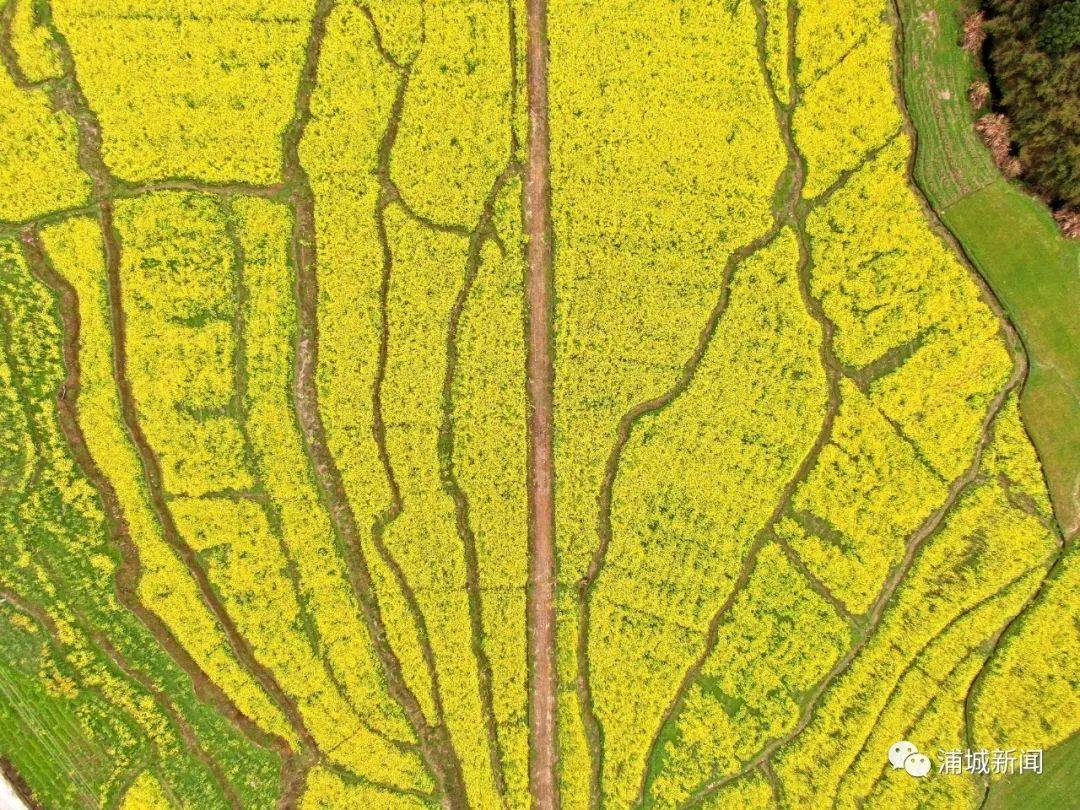Gérard带我们去森林里散步。刚走了十分钟,就听到打雷的声音,我们决定继续走,结果雨下了起来,我们快步走到一个风景点,站住观察雨是否会停。森林里起了雨雾,绿色的,空气变得更湿润起来,散发出好闻的草木气息。下雨前,森林里的空气也是好闻的,但下雨的时候,空气更加好闻,整座森林散发出梦一般的气息,这种享受是全方位的,色香味俱全,我忍不住深呼吸,想多吸收一些这样的空气。
雨变得更大,看样子短时间内不会停。我们决定撤回去。我们把随身携带的东西放进Gérard的双肩包,然后夹紧身体跟随在他后面快速前进,雨劈头盖脸打在我们脸上和身上。好久没有这么爽了,身心放松,无所依傍也无所忧虑。
我们还碰到几个同样撤出森林的人,他们也全都淋湿了,大家看到彼此都笑起来,笑我们的处境,也笑我们“有幸”遇到同样处境的人。
后来我们又去了这座森林,那天天气很好,没有下雨。我们走到一座像古希腊一般的圆柱状亭子前,正前方山下是一座宫殿,有条如今已被杂草覆盖的小路直接通向宫殿,据说这条路宫殿主人用来幽会他的情人。
外面在下雨。响起了钢琴声。是Gérard在弹琴。我躺在床上,听着断断续续传来的琴声,感动得想哭。我仿佛看到一个少年,他就坐在书房弹着琴,几十年刹那而过。
Gérard带我和朋友去了附近小镇上的一座博物馆,也是Gustave Courbet以前的故居。我的朋友说她喜欢这个画家,还说他最好的画在巴黎的奥塞博物馆,还说她第一次看到“世界的起源”时呆惊了。逛的时候,Gérard会告诉我们他喜欢哪幅画,为什么喜欢。他说GustaveCourbet用了一种很特别的白色。我特别喜欢他的画,幅幅都很温柔。逛完后,他说我们再逛一遍吧。逛小博物馆,他一般逛两次,第二次再来一遍快速浏览,锁定喜欢的几幅画细细观看。于是我们又跟着他走了一次。

(Photo by Denis Trente-Huittessan)

(Gustave Courbet 1819-1877 Photo by Denis Trente-Huittessan)
“有些博物馆的明信片还做得挺好的。”我随他进了礼品区,也挑了几张明信片,还挑了一张冰箱贴,想着可以送给对门邻居,他们帮我们看猫。
出了博物馆,又沿着河边溜达了一下,除此之外,那个小镇其实乏善可陈,没什么别的可看的。
我的朋友在第四天早晨走了,Gérard开车送她去附近的火车站。她走之前,Gérard敲门叫我起床送她,他没有说出口的意思我心里知道了,即使跟朋友吵架了,也要保持起码的礼仪,对方离开时一定要起来,一定要有一个温暖的仪式。于是我起床,和他们一起吃早饭。我和朋友拥抱了一下,对这几天偶尔发生的不快都放开了,她肯定也有同样的感觉。Gérard让我们明白,友情的可贵,不在于随时都开心,而是在发生矛盾时宽容对方,也放过自己。对待这种生活小事,法国人的态度让我佩服。
坐在院里吃午餐时,我感觉有种熟悉的感觉,像我以前读过的俄罗斯小说。那些小说里总是写到夏日假期,总是写到去乡下度假,里面当然有爱情。那些爱情大多是悲剧,被俄罗斯作家用不同的笔调和手法写出。这里也总让我想到我老家,山东农村,我在那里度过的童年时光,以及后来上初中时回老家过夏天时的种种感觉。柳树、虫鸣、风、红砖瓦房,不同的是我老家更穷,也没这么多好吃的,也不需要每天布置桌子,也没有红酒可以喝。
老家的太阳总是热辣辣,老家有许多亲戚,有许多孩子,那时候我也是孩子。


我有时候还会想到90年代。我的90年代。那时候我还上初中,那时候家里有本书,是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得奖运动员们写的文章合辑,那本书已经找不到了,但我依然记得当初看它们时的激动心情。那种拼搏、集体主义精神和明亮的90年代气息一直存在在我心里。
在法国的最后一天,晚餐时他打开另一瓶他和他姐姐一起灌的酒,是当地有名的黄酒。没坏,还能喝,而且味道还不错。我去年参加诗歌节的时候喝过这种酒。这种酒比较少见,离开当地基本上就喝不到了。
“Madame.”他用法语称呼我,然后给我倒了第一杯。
他们都看着我,我尝了一口,没坏,还能喝。
太好了!
我们四个把那一瓶黄酒都喝掉了。
饭后,我与Gérard进行了最后一次漫步。一轮新月升了起来,天上有无数星星。远山、树木、玉米地,我们不说话的时候就能听到无数的虫鸣。我又想起了许多往事,包括死在十七岁的那个男孩,我农村老家邻居家的儿子。我们通过几封信,他后来去打工,还给我寄过钱。后来他跟人打架,被捅死了。我把他写进了小说《新死》。当时发表在日本的文学杂志上,大江健三郎看了以后说:“春树可能有未来。”
他告诉了我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他谁也没告诉过,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想告诉我。
这个秘密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我也不会在笔下写出来。这是他对我的信任,一个几乎是陌生人的信任,如此珍贵。
“接下来的两年,你最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他问我。
这是个经典的问题。我给了他一个经典的回答:“我希望找回我自己。”
Gérard听了这个回答,跟我说起很久以前的事,大概是二十年前,他最好的朋友死在了他怀里,在希腊。他说那个朋友长得帅气极了,是个诗人。就在他死后几天,他的爱人也死了。真是个浪漫主义悲剧故事。我也在思考死亡,尽管我比他年轻。他六十八了。在死亡和存在之间,是爱。无法忘记和磨灭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