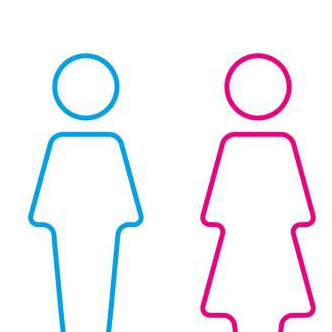和老北京一样,老济南也是有许多胡同的。
那些深巷在记忆中清晰生动。它们纵横延伸,好像巨大的舞台,上演了无数人间清欢。
每当想起故乡,脑海中总出现明星电影院和一个叫道德四里的地方,萦绕一片清雅甜蜜的槐花香。
那一大片区域被称作槐荫区,在城市中充满诗意。槐花是道旁树,夏天其香弥漫,而且槐花还可以做成美食。煮在粥里,揉进饼里,别有风味。
电影院是座中国古典建筑,在童年的记忆中,它几乎和宫殿一样伟岸。红檐琉璃顶,用时髦话讲,当年它差不多是槐荫区的地标。下面一条坡路,通向许多弄巷。影院位于高处,很有些高屋建瓴的气势。
弄巷虽宽窄不同,两边的宅院却大都是四合院,别有洞天。道德四里有条略宽的主道,两边各有住宅,走到中间向左拐,进入一条短巷,尽头是两扇黑漆大门,就是外公家。短巷没有什么用途,好像只是自家的外走廊。
进入大门迎面是照壁,向右拐,才进入祖宅四合院。院中有两棵高大梧桐树。外婆说,紫色花朵晒干后是一味中药。从新鲜的花朵尾部吮吸花蕊,有香甜的蜜汁。
雨中的梧桐花散发出奇异的幽香,落在地上,铺砌成满满的悠长的回味,美丽而落寞,脆弱而无奈,美好却无法长久,正符合少年时期莫名的清愁。
卧室的窗户很小,开得很高。因为临街,能听到各种小贩的吆喝声,卖豆腐脑,江米粽之类。最神奇的是爆米花。端一碗生大米或玉米粒出去,小贩用一个小炉子,过一会听到“嘭”一声巨响,热乎乎香喷喷的爆米花就出来了,收在一个大篓子里。和美食同样吸引小孩子的,是近乎表演一般的制作过程。记得每逢爆米花的小贩来了,左邻右舍的儿童会鱼贯而出,或捧着碗,或捂住耳朵,兴奋又害怕地等待那一声巨响。
资料图片
老宅里留下了许多欢声笑语。小姨爱美。一天举着十张崭新的两角钱钞票,喜上眉梢地说,烫发去。时值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正在改革开放。烫发还要费心用新钞票,可见心情是多么新鲜、多么欣欣向荣。
剥橘子吃的时候,我被什么逗笑了,不小心吞下一粒橘子核儿,马上不知所措,问小姨怎么办。她大笑说,没关系呀,以后会有一棵小橘树从你脑袋上长出来。为此我发了半天愁,直到被别的新鲜事吸引了注意。
当年,有间临时的学校设在一处古雅的院落里,只有一年级几间教室。院子里有高大的乔木。在秋天,落叶随风起舞。幼年不知何为古雅,只是觉得喜欢。那种景象仿佛就是诗意的种子,播撒在记忆的原野。我们玩一种游戏,拔老根儿,找一些杨树落叶,叶柄越有韧性越好。把两枚叶柄交叉反扣,各自用力拉,如同拔河比赛。谁的叶柄先断,就输。这样,残破的落叶竟然成了小孩子的宝贝,有了用武之地。
大院子后面套有小院儿,里面的房屋用作办公室。课间休息时,学生们在院中到处跑来跑去,我也闯进小院儿,惊奇地发现老师的小女儿在吃一道凉菜点心:把紫色的杨树花洗干净,开水烫过,拌上香油、酱油和醋。老师笑着说,很好吃的。
儿时如此亲近自然,真是令人回味无穷。以后才知道,串串成熟的杨树花具有抑菌和增强免疫力的药用价值。以花入味,过去吃的是朴素,现在如果有机会再吃,吃的就是情怀了,可以抵御膏腴的油腻。
人们常说,最美的风景是人。济南民风淳朴,除此之外,当然还有美人。因为住处很深,让人平添了几分向往。母亲的好友就是一个古典美人,像神仙姐姐一般,有少见的丹凤眼,眼梢细长又温柔。乌黑的发辫几乎垂至腰际。她和典型的大眼睛、鹅蛋脸不同,脖颈又长,让人以为是芭蕾舞演员;但是她又显得娇弱,没有舞者的健美。
小时候看她的黑白照片,顿时觉得翩若惊鸿。和她的照片一起压在玻璃板下的还有当红影星的黑白照,可是她们笑得太灿烂,妆也太浓。她呢?你总不会用艳这个字形容,却觉得令你过目不忘。照片中的她几乎都在微笑,微到捕捉不到。少时的我第一次领略到,朴素具有如此惊人之美。
那时候很瘦弱。胳膊细细的,据说别人一拉自己手臂,十有八九会脱臼,俗称“掉环儿”,动弹不得,大人就赶紧抱去找刘奶奶。
刘奶奶住在巷子里,青石板铺成的巷子。她抽水烟,嗓音唔噜唔噜的,却身怀绝技。有人骨折了找到她,刘奶奶只要用手指一摸,即知道裂缝在哪里,然后用手掌稍稍用力便可以接骨。这种祖传的正骨秘术使她远近闻名。
听母亲讲,一次舅舅踢球摔伤了腿。请刘奶奶来。
“用一条腿靠墙站好”,她对一瘸一拐、龇牙咧嘴的舅舅说。然后用手摸索一番,几下就把断骨接好了。刘奶奶这位名医还很仗义。说街坊邻居不收钱,只要治一桌酒席招待她就行。
当然对付小孩脱臼,刘奶奶更是手到病除。
也许就是这些民间高手启发了自己对中医的兴趣?自家姨夫学识渊博,还自学成了中医。上医治未病。每次号脉,他都能说出身体可能出现病症的隐患,真是神奇。比如,说我胃寒,我的孩子却胃热。难怪!即使是夏天,我也喜欢吃温热的食物,可是孩子却大爱冰激凌。可惜因为不是科班出身,他的本事只能在亲戚朋友间施展。虽然惠泽别人,却绝无名利可言。
济南的道路很多以经纬命名,东西为经,南北是纬,网格状分布,刚好和地球仪的经纬线相反。据专家说,百年前老济南开埠时的经纬路是从纺织机得到的灵感。手工纺机长线为经,短线为纬,对应老商埠东西长约五公里,南北不足三公里的地理区划。而把这些经路、纬路贯穿起来的就是无数的寻常巷陌。
走在深巷中,仿佛走在故事里。
资料图片 摄影/赵琪
小时候住在十一马路,附近有热闹非凡的西市场,一条极窄的巷子是去二姨家的近路。昏黄的路灯让长长的窄胡同充满了神秘。由于行人不多,还真有年轻人在那里幽会的。
大家就管这条巷子叫浪漫胡同。如果骑车经过,对面的人走过来只好侧身避让;或者单车停下,推着走过。偏偏一次姨父单车后座上驮了儿子,不方便下车。前面偏又有一位老太慢条斯理似闲庭信步,按了铃铛也不管用。他很幽默,灵机一动大喊:对不起,撞上了啊!说时迟,那时快,老太倏忽一下不见了。倒不是她施展轻功飞了起来,而是无比敏捷地闪进了旁边开着的院门。就凭这一点,我觉得住在巷子里的人个个身手不凡。
因为姨家有个小院子,自己和母亲常去串门。院子正中有棵石榴树,枝干遒劲,适合入画。夏天最适合在小院里纳凉,吃晚餐。
一天大家正在院里围着方桌吃芝麻酱、黄瓜丝凉面,来了一位客人。二姨赶紧准备碗筷,招呼一起吃。吃完饭又聊了一会儿才告辞。姨夫笑着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我当时还是小学生,以为他说那客人性子慢吞吞。速,不是快的意思吗?这个误解直到几年后才得到纠正。觉得自己真是不学无术。
上中学以后在姨夫的书柜里发现了《史记》,有种惊呆的感觉。世上还有这么好的书!还有《唐诗选》,也是如获至宝,赶紧借来,找个笔记本,手抄唐诗,看不懂的不要,不喜欢的也不要,居然囫囵吞枣抄了一小本,应该是个文学启蒙
小时候还没有什么课外班,大家只是浑浑噩噩地玩、自然生长。家弟曾按照连环画,俗称小人书上面的图样,削出梁山泊好汉的各式兵刃,相当有模有样。我在表弟的指导下学会了象棋。一次输了,他才笑眯眯说,我这招叫二车错槽。不过从那以后,就各有输赢了。现在的孩子不得了,课余有各种专业班,不到十岁就已经是围棋段位高手。可是我并没有觉得遗憾和缺失,反而觉得自己虽然已届成年,或许尚有深厚潜力,未来可期。
无论是道德四里的老宅,还是浪漫胡同,都已经从地图上消失。幸运的是,保留下来的还有百花洲、曲水亭街这样巷陌交错的地方。那里可谓老济南人心头永远的风景,是低吟浅唱的牵挂。在大明湖对面,一道清流两岸,全是延伸的小巷。“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清流和明湖一样,是道地的泉水,清澈见底。
这里有条王府池子街,以一池碧水:濯缨泉而得名。泉池属于珍珠泉群,曾经囊括在明英宗的次子德王的王府中,因此又名王府池子。德王在清代即废,王府池子重返民间。
它藏在比较隐蔽的地方,要走过像迷宫一样的街巷才能抵达,所以显得幽静,不若趵突泉久负盛名,气势也大。不过,它一泓碧水,周围一圈旧建筑,宛若绿树、蓝天和白云的梳妆台,自有柳暗花明的惊喜。曲水沿岸,人流如织,但拐过几个弯,到王府池子,就会眼前豁然一亮。若过了中午的饭点儿,进入一户大院,也许会有那种专享待遇呢。四下无人,和朋友用一个包间,点几道像荷叶酥鱼,饺子之类的私家菜,饶有趣味。
此处还是农历三月上巳节古民俗活动:曲水流觞的绝佳之地。古人把注满酒的轻质酒杯放置水上,任其漂流,酒杯停驻在谁面前,谁就要举杯吟诗,好有雅兴!
“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想也是。这些巷陌充满了独特韵味和各式有趣的人物,真的萦绕了悠远神秘的气息。无论走到哪里,这气息都常伴左右。
我从炎热的南半球回来,经常盼着下雪。在澳洲想欣赏雪景,需要在冬天专门去雪山。一辆车收五十澳元,而且要排队,轮胎要绑上防滑链。总之需要全身心动员,费心安排。哪里像回家,冬季总有一天,开门就是一片繁盛的白雪!
每逢大雪纷飞,我和表姐相约游园,已经成为近年来我们的保留节目。看雪花落于松菊之上,泉水之中,从白到白,简直梦一般的归宿。
回忆起儿时,在街巷中追来跑去打雪仗,多过瘾!现在许多年之后,学生的功课也多,离自然趣味却有些远了。大雪天,已很少看到孩子们在雪地里尽情疯玩。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采薇》里的句子甚合游子心境。
自问:百花洲上百花开,何时可缓缓归?
(作者:庄雨 简介:现居澳洲。多篇散文刊登于人民日报海外版、入选海外作家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