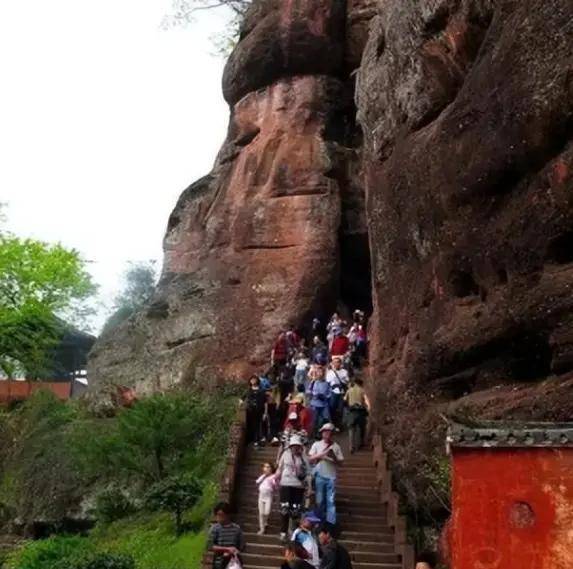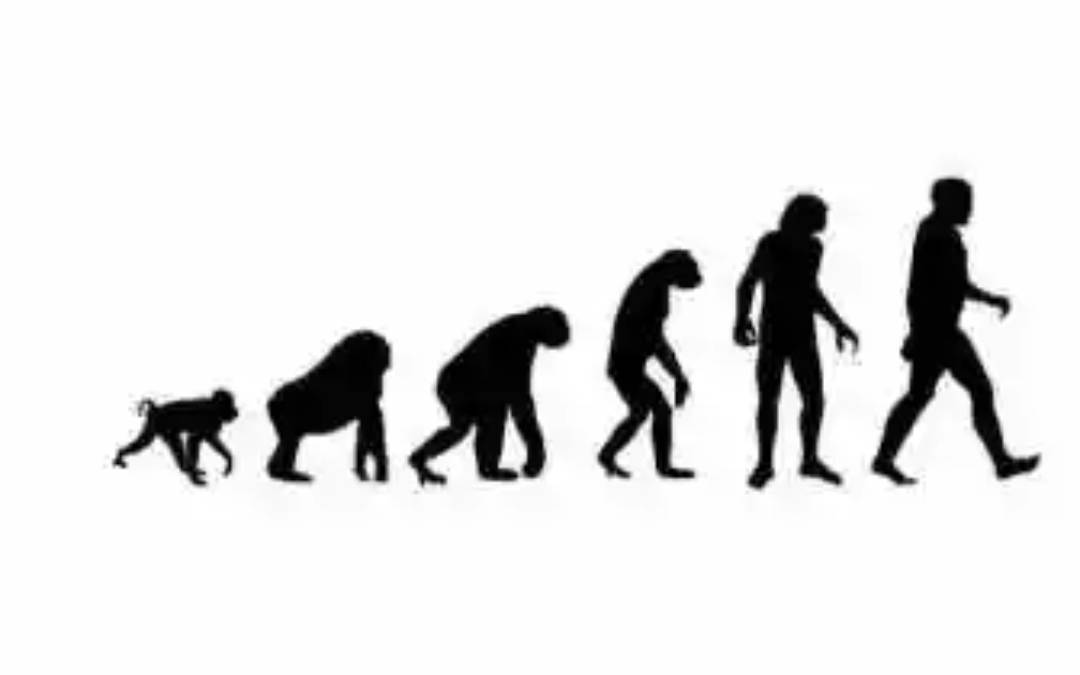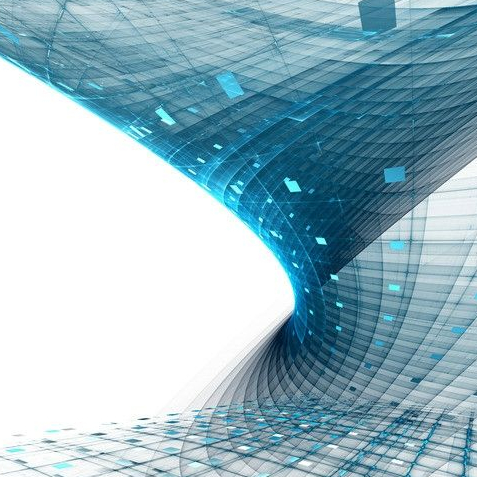漫漫人生,你会走过很多路,看过很多风景,经历很多事情,遇见很多人。有些人,有些事,平常你绝不会感觉到他们有多重要,但当你需要他们时,却发现他们已经不经意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譬如,街角修自行车补鞋的师傅。
大概是十几年前,那时我还是初中生,每次骑车上学和回家的时候,总会经过离家不远的一个修自行车补鞋的小店。
店主是一对夫妇,好像是四川人,大概三四十岁,男的修车加补鞋,女的除了负责家务外,也会做一些诸如沾鞋之类的轻活。
印象中男的留一个中分头,总爱穿一身老式的空军迷彩,女的倒没有多少印象,因为我去那里要么是修车,要么是给鞋动“大手术”,所以都是和男的打交道。
那时,无论春夏秋冬,小店门口总会支一张桌子,放几个凳子,附近的中老年男士就聚集于此,或闲聊国家大事,或用一副纸牌运筹帷幄。小店门口总会放一个蜂窝煤炉,用一个茶壶烧着开水,打牌聊天的人想喝就自取。
至于我,自然是和这些中老年同志凑不在一起的,因此每次路过也只是和其中认识的长辈打个招呼,便匆匆回家“干饭”。
前面也提到过,我会去那里修车和补鞋。十几岁的孩子,正是爱出风头的年龄,就像《辛幸和冷泠》里的辛幸一样,双手骑车不过瘾,非要单手骑或者干脆直接不握车把;宽敞平坦的大路显示不出“车技”,非要骑车上人行道、骑着下楼梯,由于我的父母也和辛幸父母一样坚持“穷养儿子”,再加上那会治安不好,我的自行车就是普通的山地车,于是,修车就成了家常便饭。
后来还是因为有一次出了交通事故,司机赔了我一辆稍微高档一点的铝合金材质的山地车,才把“动手术”变成了“输液”,最多也就是“缝合”一下“伤口”。
我提出反正这个轮胎已经被扎了好几次,干脆换个新的,他却说不用换,补补还可以用,等再扎几次再说,后来,倒没有被扎破,而是直接爆胎了,终究还是换了新的。
沾了几次以后,鞋子伤口越来越大,我也暗喜可以买新鞋了,不过为了说服父母,还是把鞋子拿去店里让店主修,就只等他说修不了。
“可恶”的是,男店主亲手破坏了我换新鞋的梦想。他告诉我可以修,用机器钉一下就行,我当然不同意,钉完外面一圈线,怎么好意思穿出去。
那还能怎么办呢?试试呗,别说,他技术还挺好,真看不出补过的痕迹。
车上,我又想起了那个修车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