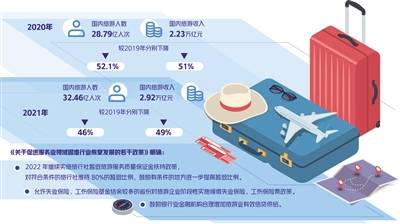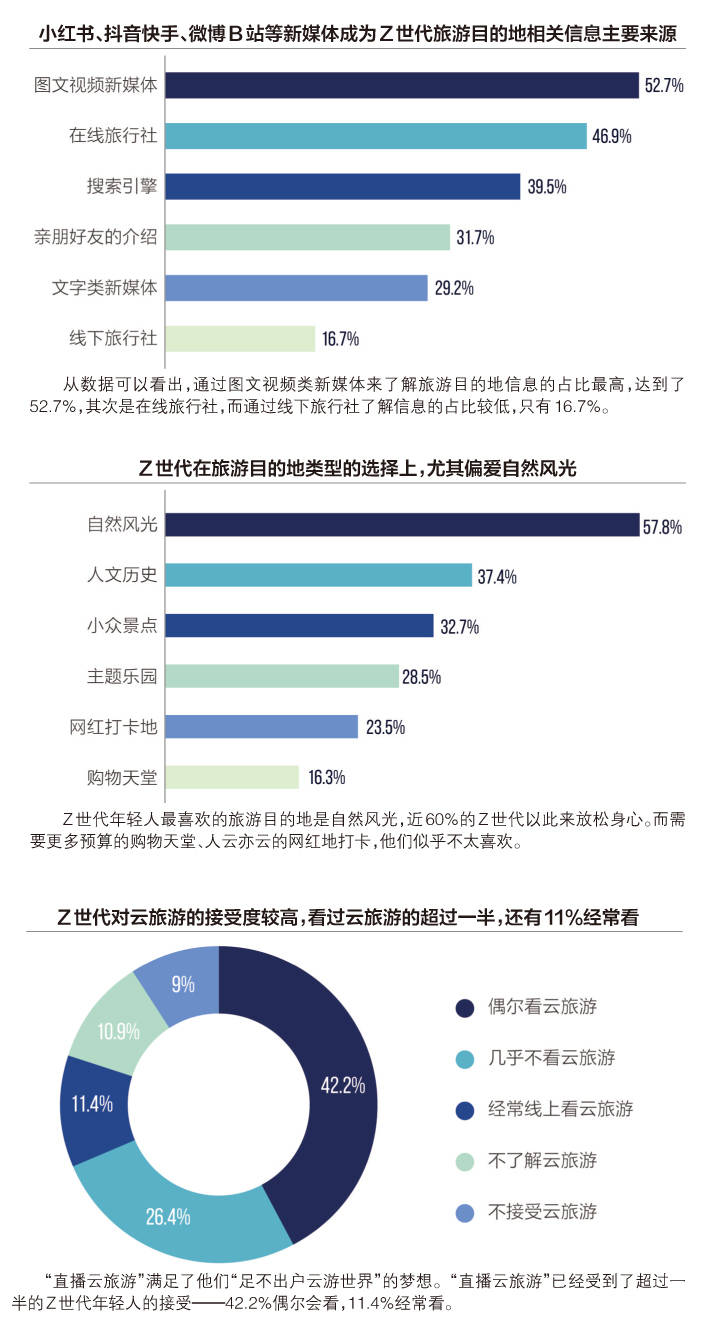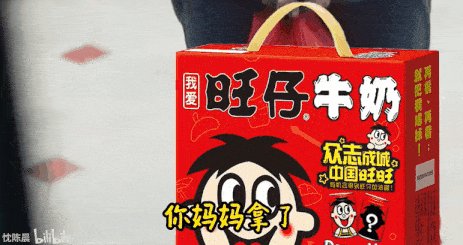三月的室外,隐约还有些冷。春天的古城总是忽冷,忽热。它让我感到,它同我一样的情绪化。连日的沙尘弥漫在空中,入室于罅隙,破窗于无形,散发着呛人的尘土味,久久不愿散去。它似乎在等待一场雨或雪,好让它们落在更为迷茫的空间和时间里。
久居在小城中的我,对于春天实在迟钝,或者说是已经很久没有见识过真正的春天了,抑或就是感官功能退化了吧。抬眼望小城的上空是一成不变的灰色,周围的树木和景色并未发生多大的变化,阳光珊珊迟来又早早褪去,灯光成为必不可少的照明工具。即便是到了三月末,虽说温度上升了几度,但那些个沾着点绿意的词,似乎依然是书里的记叙。春天什么样子,我想起了乡下,童年的我穿行其间,在充实、舒服的春天里,就像一只春日衔泥的燕子。而今离开故乡快三十年了,但我似乎一直没有从我的童年和少年的时光中走出来。也许从乡村里走出来的人,大多对乡村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

记忆里乡村的春天,最先是沿着牛羊踩出的雪坑里走出来的,深深浅浅的蹄影在春风里一行一行变的水旺旺的。厚厚的积雪覆盖的泥土,最先从那一个个小坑里重见天日。伴随那些春日时光的,是冰冻了一个漫长冬日的大地脱去了白色的皮袄,一点点的露出了春色。先是房前屋后的杨树抽出了绿芽,然后是地上枯草上冒出嫩嫩草尖,接着就是迟滞了一冬的康沿河又吹起了悦耳的哨子。而那一阵一阵的风,从遥远的大漠深处悄然而来,带着些清新的尘土,带着些水雾的粘稠,浩浩荡荡而又缓慢地融进了乡村的角角落落。

清晨,脆耳的鸟鸣从打麦场的草垛上飞过来,一声声唤醒了沉睡的人们。太阳从东大山跳了出来,露出了红彤彤的笑脸。不知谁家的老牛已在哞哞长歌,似乎想发泄积蓄了一冬的力量。田埂间,三三俩俩的乡亲们,扛着铁铣,拉着架子车,要去自家的地里修整沟渠,拉粪烘土。春种一粒黍,秋收万颗籽!农事是误不得的。
院子里,母亲正在帮哥哥整理农具和绳索。那时的她,还不到我现在的年纪。刚从高中毕业回乡的哥哥,对农具的使用多少还是有些陌生。而父亲在县城工作,偶尔回来,也帮不了多少忙。母亲一边整理,一边对哥哥说,康沿河边的那块地,去年种的是豌豆,今年换茬要种麦子,趁早要把粪土拉上,不然过几天,地湿的就拉不成了。整理好农具和绳索后,哥哥从圈里牵出骡子,把架子车套上。然后在车箱里放上圈笆、铁锹。粪堆在街门外的大院里,是积聚了一个冬日的农家肥。哥哥用厥头在刨土,母亲在帮着装车。母亲边装粪土边说着哪块地种什么,这块地种什么。那是我家种地种的最多的几年,共种六大块二十五亩地。母亲和哥哥每天早上拉粪,下午地化了,车子进不去,就在家干其它的农活,拉粪一直要持续上十多天才能运完。

遇到周末,我和弟弟也会加入到拉粪的行列。粪装满了,我和哥哥往地里运,哥哥驾着骡车,我坐在高高的圈笆上,在场院南的高坡上往回看,感觉到村庄一下变的很矮很矮,就像用手指捏成的一个小面饼,很小,但很集聚。天上软软的云、地上暖洋洋的风,向我们扑来。从粪车上远远的望去,炊烟、柴垛、畜粪、旱烟和新鲜的泥土味混合着浓烈的阳光,在平地上起伏。村西头那一大片被雪埋过的麦岔地,已经有人在撒粪,油黑油黑的地里,拢着淡白的雾气。日头照在雾气上,返出一道道光晕。田埂上坐着几个抽烟的老人在聊天,几个小孩围着追逐打闹。河沟旁边有几块撂荒晒茬的沙土地,泥土酥软,青绿色的地衣植物隐隐地生长。当然还有农家人最爱吃的野苣苣菜,常常有村里的老人和孩子去挖,她们挎着蓝子,拿着铲子,起伏之间充满了动感,像一只跳舞的猴子。天是抬头看见的,很高,很远,也很蓝。而那些云彩也是清晰的,朦胧的,现实的,梦幻的,幽蓝的,乳白的,浅灰的,都交织在一起,拥挤在一起,形成堆积。再远点,是隐约的祁连雪山,以及离我的视线稍稍近些的东大山都拥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美感。也许这样的场景毫无创意,这种描述和镜头已无法引人发笑,太习以为常的方式,每个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早已默许了它存在的合理性。

当春天已过去半个,节气过了雨水和惊蛰,挨到春分时。牛哞声便从地里传过来,最早起来犁地的常常是小叔。天不亮他就出去了,等到太阳冒出一丈多高时,母亲就让我去给小叔送早饭。拉着犁铧的牛走的很辛苦,扭来扭去,但由于小叔叔手中的鞭子时常会轮起来,它也也不敢声张。小叔犁地一直会到黄昏,才扛着犁,牵着牛,驮着一轮夕阳回来,爷爷接过缰绳,然后用慈爱的目光抚看着牛。从地里到村庄,要经过康沿河,从祁连山流下来的雪水夹着冰块互相拥挤着在康沿河狭窄的河道上趔趄而行,那流水与冰块碰撞的声音吸引着我们的脚步,牵绊着我们的成长。整个春天乃至夏天的康沿河,就成了我和伙伴们玩耍的天堂。当然还有河边的沙石,歪斜的杨树,被冲刷得凸凹不齐的田堰,以及黄土墙掩着的村庄,村庄里的石磨,牲口,拐弯的土路,坐在自家街门闲聊的老人,以及蜷缩在门口的黄狗……

春雨贵如油,有雨下过,地里的青苗便发疯似地长开。爷爷来穿雨靴,说要去地里看看,怕雨把埂子都冲坏了。我便也跟着去,田地绿油油的,像铺上了绿色的毯子。有时,爷爷也会拎着一只粪筐,拿一杆粪叉,去拾牛粪驴粪,倒进自家的田里。偶尔爷爷会挖出一种叫厥玛和辣辣的植物,用水冼净让我吃,那种青涩的、微苦和辛辣的味道让我至今记忆尤新。

春天的村子,被雪水和发芽的青草洗涤出一股纯净的气息,像土,又像牛粪,我的身体和思维,也一点点地被这气息所熏染,渐成一件洁净的、轻盈的物件。场院里的石墩子,小英的妈坐在上面纳鞋底。那时,她是我们村庄最漂亮的女人。她从来不干活,时常在她家的门口和场院里的石墩上闲坐。冬天也是,她不怕冷,脸红扑扑的,穿了那时彼为时尚的衣服。像极了画册上的女明星,质朴而实在。后来,我常听大人们议论说她和村子里一位在外地当包工头的堂哥来往,而且经常有青海的司机开着车来她家,卸下一些货和蔬菜之类的东西,住上一晚,然后第二天便开车离开。村里的一些女人常对对她指指点点,但她也不在乎,也有村里的女人和她对骂,骂她是婊子,然后厮打在一起。那时她在村里的情形,颇尴尬。终于有一天她失踪了,后来听说她跟那位堂哥在西安生活,可谁也没有见过。只当是新的传说罢了。

通往康沿河的路口,有一户人家。他们家三男一女,母亲是寡妇,很矮小。也是春天的一个早上,正在地里干活的老大不知何因与他老婆争吵几句,突然回家吃老鼠药就死掉了。我们放学回来时,尸体已放在路边,上面盖着草席,一双脚露在外面,他的母亲和老婆爬在席子上放声大哭。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面对死人,为此,好长时间我都不敢一个人去村西头。春末的时候,他的母亲也死了,他的妹妹跟着一个陕北的石匠跑了,再也没有回来过。短时间内似乎所有的不幸都落在了他家。听人说是他家的房子没选好风水,西边来的的阴气沿河沟全进了他家。
所以这些记忆,都如我的梦寐,像是一幅永不退色的照片,悬挂在我记忆的屏幕上,至今都还沉湎于不舍的回味。有人说:人间的春,只在童年,可惜,当我们懂得,这样的春日,已远去。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