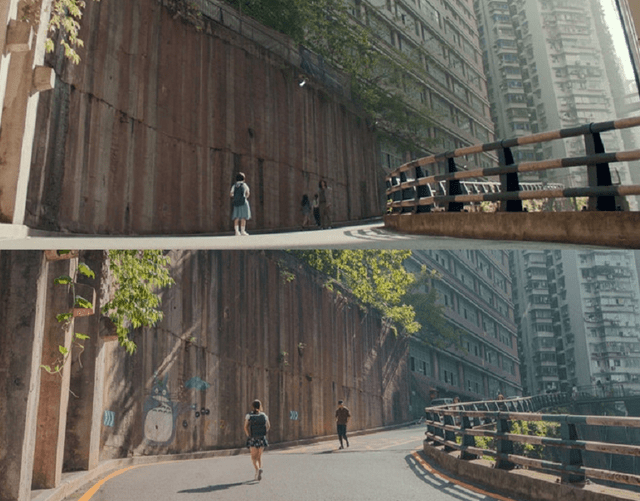深秋,是京寨一年最美的季节。满山的树叶变黄、变红,清风徐来,树上早已熟透的栗子从炸裂的带刺的壳子中滚落,掉到树下,立即被山里勤劳的松鼠搬进树洞的窝里贮存,作为它们过冬的口粮。山下蜿蜒的铁道线上,鸣着汽笛开过的火车,一点也不影响松鼠们的劳动,它们仿佛在说: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谁没见过火车呀。
那年秋天,从学校毕业参加铁路工作的我,成了一名新工。坐着绿皮火车在都匀市与独山县交界处的京寨站下车后,大胡子工长牵着一匹白马来接我,马背上驮着我的行李,我跟在大胡子工长身后,踩着山路上厚厚的松针叶,来到山下的京寨工区。来之前,我不止一次地想象过,京寨,是一个如金似银、让人无限遐想充满诗歌的远方。在外人看来,这里仿佛世外桃源,美不胜收。
其实,再漂亮的风景,也需要一种心态。若是以游客的身份来京寨时,你会感到新奇、惊艳;但当你作为主人、长期在这里扎根生活时,眼睛里就不再只有美景。我所在的工区,坐落在群山之中,前不巴村,后不着店,除了铁道线上偶尔鸣着汽笛奔驰而过的火车,这里仿佛就是被人遗忘的角落。
新进工区,新工一般是要由一位师傅带着干活的。新人往往一头雾水,弄不清铁路上繁多的安全规章,没有师傅带是容易出事的。带我的是大胡子工长。在工区,工长的养路技术水平当然是最冒尖的,是工地上唯一有资格掌握道尺的人,不然怎么当得了大伙的头儿。嘿,工务段的活,并不是外行人想象的有一身蛮力气,把八斤半重的捣镐头舞得带风就能干好,没有金刚钻,做不了瓷器活。大胡子工长对精确到毫米的线路起、拔、改,道岔曲线养护,样样都精通。
据说,之前有的班长为了维护自己在工区的技术霸主地位,在使用道尺测量轨道几何尺寸时,袖口都要把道尺水平泡遮挡得严严实实的,生怕别人偷偷把本事学了去。大胡子工长倒是没有这样的作派,我上工地的第一天,他就教我认道尺,量轨距,讲解一些捣固的要领。比如捣镐柄的两只手,要握得前手松、后手紧,手才不容易起水泡……看着我满身油污、满头大汗的样子,大胡子工长说:你呀,真不该来。
大胡子工长把工区当成了家,很少回到县城里去。每个月底,他在县城一所小学当教师的妻子就会来看他。大胡子工长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工区就像过节。工长的妻子很漂亮,她不仅带来了县城里的流行风气息,还带来了很多好吃的。大胡子工长就会把工友们招呼在一起,大伙热热闹闹吃了一顿团圆饭。有懂事的小年轻,饭桌上殷勤地给工长的妻子夹菜,左一个“嫂子”右一个“嫂子”甜甜的叫着,央求工长的妻子帮忙介绍女朋友。大胡子工长的妻子笑着连连点头,答应着帮忙牵线。年轻人兴奋地举起拳头当话筒,扯起嗓子唱起了跑调的“卡啦”不OK,开启了工区一个月最热闹的时候。
说起来,大胡子工长还救过我的命。记得一次,我正在线路上作业,心里盛着心事,这时,火车开过来了,我还在铁道中间发呆。火车一路鸣着急促的汽笛,一边撩下了死闸,工友们急得朝我大叫。说时迟,那时快,大胡子工长冲了上来,拽着我滚下铁道。火车带着刺耳的制动声,呼啸着从我们身边驰过。看着惊魂不定的我,大胡子工长当时没有批评,也没发火,只是关切地问了一句:没事吧?但是,这件事的教训却让我终身难忘。
次年的夏天,京寨满山苍翠,傍晚,树上数以万计的知了鸣叫声如歌如潮。我被调到段上助勤。离开那天,大胡子工长又从老乡那里借来白马,驮着我装满书籍的箱子行李,把我送到了车站。相处大半年,大胡子工长和我已亲如兄长。临别,他说:你不应该走。
在工务段机关助勤的一个月后,我走过单位的光荣榜时,突然看到光荣榜里一个人的照片分外眼熟,确切地说是他那兜腮的大胡子,让我一眼就认出了老工长。他身着白色铁路短袖衬衣,胸前戴着的一枚党徽格外显眼。
瞧,这就是我看过的最帅、最精神的大胡子工长。
文/黎玉松
文字编辑/向秋樾
视觉/实习生 惠仕维
编审/李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