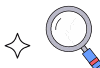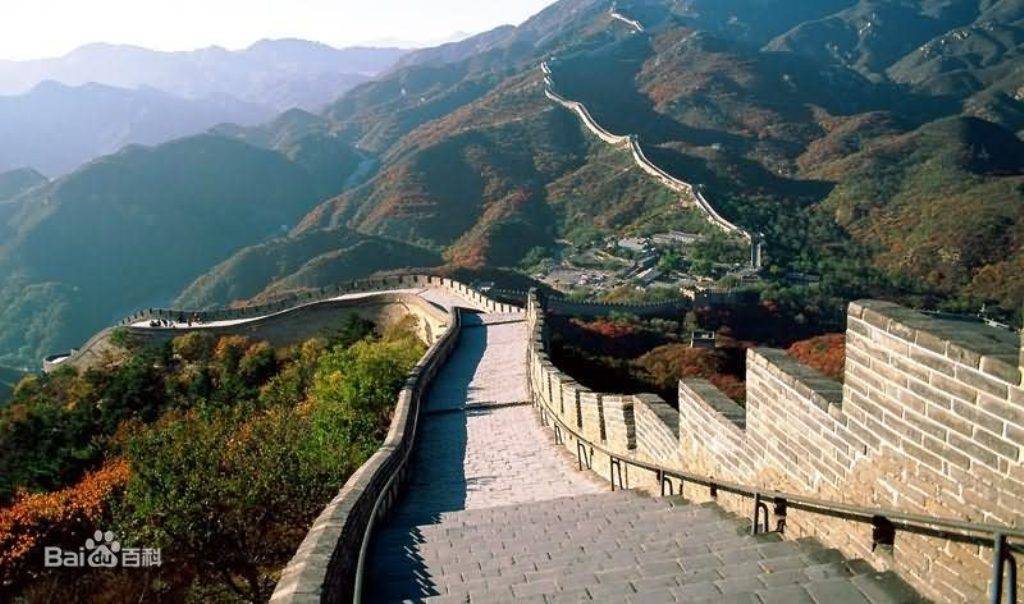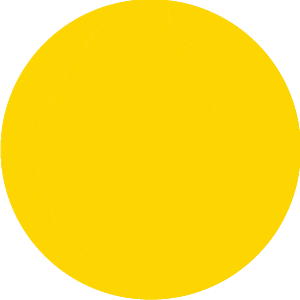黄昏以后,暑气随着夕阳的西下而稍微有些减退,偶尔有一股轻风吹进苏北村弯弯曲曲的棚户区内。人们在矮屋子里蹲不住,先后拎着小凳,寻个空地方坐下。条件好些的,放开一张用旧水管弯成的躺椅,往上一躺,脚后跟垫上一只小木凳,那滋味并不比在冷热空气调节的宾馆里差。要是哪对年轻的恋人散步拐进苏北村,那么,就得表演踏高翘般的东绕西转,没准,还会撞进死胡洞。
这会儿,只有杨傻子那幢小平房门前有块空地,称它为“幢”,实在是因为它比旁边的屋子高出一截。因此,它搭的阁楼也有一公尺半的高度。虽说一旁是二十来户人家的公用水池,可是这辰光也清静了。这儿成为左邻右舍欲抢占的地盘。往常,放上一张小桌,从杨家阁楼窗洞挑出一根电线,这儿就是牌迷们的市面。今夜,附近的沪东工人文化宫溜冰场露天电影是新片《阿凡提》,经冶炼厂做工的柳保子一宣传,说是他们厂子里放过了,是如何的扎劲,逗得人们恨不得立即瞧上一番才解馋。这样子,就吸引走了不少牌迷。剩下的皮匠老三与他媳妇三娘子、伍大妈乘虚而入,享受着这块地盘。
随着一阵木拖板的“踢沓”声,五大三粗的杨傻子走出小屋,右手指缝夹一支烟,大大咧咧地倚在椅子上,翘起二郎腿,悠哉游哉地喷着烟圈。
七岁的女儿跑过来,粗声大气地问:“阿爸,台子上的西瓜是留给我吃的吧?”
“拿去吃吧。”
“只有一块,妈有得吃吗?”
“你管你吃,啰嗦什么?”
女儿进屋去,捧出一片西瓜,坐在父亲身边,咂咂嘴,不时伸长舌头舔去上嘴唇沾上的甜汁。当她站起身,欲将瓜皮扔进垃圾箱的时候,忽然眼光往弄堂口一转,快活地叫道:“妈,你回家了。我吃西瓜,奶奶留给我的。”
做母亲的没有好脸色,气鼓鼓地走进屋子。一会儿“蹬蹬蹬”地跑出来,对着悠闲的丈夫叫道:“菜怎么一点多没得啦?”
“碗橱里大概还有一点油炒罗卜干,你吃是了。”
“早上我买来的两根大肠呢?”
“家里这么多人吃,你这么晏家来,留着不要馊气?你将就点就是了。”
“将就点?我再将就,你们越发要爬到我的头上撒尿呢。”这回,做妻子的火气像是压不住了,喉咙一下子粗起来。
做丈夫的小眼睛往四周一瞥,妻子的大嗓门惹来左邻右舍耍笑的目光,马上低声然而严厉地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不要逼人太甚!”
“我逼你什么啦?没用的家伙,只会在女人面前凶。有本事把六角钱讨家来。”
“你还提六角钱?我恨不得揍死你。”做丈夫的咬着牙齿说。
确实,杨傻子也烦恼一整天了。上午,里弄大组长老霍来收自来水费。大热的天,水费是一年中最贵的。傻女人说某人家少付了。老霍将了她一军:“你家女儿长到七岁了,也不付水费呀。想说人家的话,自己先要过得硬。”
杨傻子可不买帐,是个堂堂正正的红脸汉子,一下子掏出六角钱交给老霍。
老霍笑咪咪地走了。傻女人像被人剜去一块心头肉,唠唠叨叨了一整天。可杨傻子无论如何也拉不下这个脸面去讨回六角钱。所以听任女人的责备。可现在,反击的机会来了。于是,他摆出一付大丈夫的威势,呵斥道:“扎呼什么,不要脸的。阿是西瓜没吃到,嘴巴馋得熬不住了?”
“你才不要脸。大傻子。苏北村谁个不晓得?找上你真倒祖宗十八代霉。”女人毫不示弱。
“你,你再不识相,要吃老虎酱!”做丈夫的攥紧了拳头。
“你敢?摆什么臭豆腐架子……。”女人的气焰越发嚣张。但她的话音未落,脸上就挨了一记脆响的巴掌。女人嚎叫一声,上前在丈夫光溜溜的前胸后背上抡巴掌。丈夫也似酒醉了一样,抡着拳头与女人干了起来。霎时间,凳走砖飞,杀气腾腾。
七岁的女儿穿着短裤衩,赤着膊,哭喊着:“不要打呀,不要打呀。”但丝毫没有起到阻止的作用。
所谓苏北村,地处杨树浦工业区,早在四十年代,大批的淮北人流浪到此定居,自成一个村落。这里的居民,到了今天,大多数从拣破烂、刮鱼鳞,转为到大工厂里做工了。这儿,也可以说是职工住宅区了。只是棚户还没多大变化。这儿,历来有习惯,谁家婆媳之间、夫妻之间、母女之间有些微小的事情,甚至年轻的谁谁有了对象,对象的长相怎样,工资如何,都会成为新闻而传播三两天的。现在,有了一幕活话剧在开演,自然是非看不可的了,并没有人上前劝架。老三娘子嘴里嗑着西瓜籽,离开小凳,站到一旁,那对眼珠在路灯下,反射出贪婪的光。她的男人皮匠老三,长就一副芦柴棒似的骨架,抡把大蒲扇,往自己光光的大腿上扇着风,嘴里助威似地喊着:“别打了呀,打伤了总是自己的老婆,手下留情呀……。”他那节奏感很强的声音,倒招揽来更多的围观者。以至于前弄后街的人们都涌来了,把一条带鱼似的小弄堂给挤得水泄不通。尽管这样,在杨傻子所到之处,人们还是极自然地退出一块足够他们周旋的地盘。
天已漆黑一团。只有几颗星星眨巴着不解的窥眼。昏黄的路灯下,人群中有位长相俊美、梳着云髻的女人用手肘抵一下旁边的老三娘子:“老三娘子,他们怎么这个样子?”
“你一直住在厂子里,不晓得。这一对活宝,从结婚到现在,孩子都七岁了,可夫妻俩一年打到头,好一阵孬一阵,就像家常便饭。”老三娘子说着瞧一下听的对象,见对方露出惊讶,以为找到了一个听她摆龙门阵的人,很是兴奋,话也滔滔不绝了。“这个女的自家不好,还在做姑娘时,就赖在杨傻子家,三天两头不走,弄得杨四妈一家门都看不起她。结婚时讲排场,请了二十多桌酒,又办了全套的捷克式家具,背了一身的债。婚后没几个月,大橱五斗橱陆陆续续卖掉。每个月关饷这一天,准要打上一顿,把个婆婆杨四妈气伤心了,把他们两夫妻全部赶到阁楼上去睡,下面房间让给二儿子作新房间……。”
“这家子真没说的,去年腊月里,杨傻子一前一后背着两条被子,女人抱个孩子,像逃难一样去小菜场,在菜场卖菜的台子上宿夜,被值勤民兵当流飞抓住……。”伍大妈不知从那里钻出来补充这个细节。
老三娘子见自己的话被人打断,心里不满地蹩一眼伍大妈。随后又说了下去:“他们呀,打架是打疲掉了。什么刚打完架,马上手拉手去看电影了。有时候买来一只西瓜,分得不匀就吵闹,最后解决问题的手段就是拳头。女人左眼被傻子打伤后,视力减退,傻子好像突然明白过来,心疼得不得了,一下子买来三块冰砖,非要她一口气全吃光。就是这样子的人,没脑子……。”老三娘子动情地摇摇头。
“我要不活了,你们也没得太平。你家儿子闺女全部打过我,我要杀光你一家门才解恨……。”女人尖利的叫声从人丛中传出。人们有点儿惧退了。女人拣起砖块当武器。傻子真是勇敢,毫不畏惧地冲上前去,抓住女人瘦弱的身体用力一掇,女人跌倒在地。刚爬起来,还没站稳,又是一个狗吃屎。女人歇斯底里地吼叫着,进出一下灶间,手上多了把菜刀。但是,丈夫那有力的手臂神奇地捏住菜刀并夺下,转手交给一旁的杨四爷。
杨四爷拎着菜刀,踱步到柳保子家门口,拣只小凳坐下,重重在叹口气:“讨这么个媳妇真是倒霉。”
那边,杨傻子又将女人往墙壁上碰几个响头,似乎解了恨,决定休战。女人不服气,仍前前后后地撕打着男人。杨傻子可全不顾这些,他提高声音说:“左邻右舍全看见的,我是看在孩子的面上才不打你的,你……。”
这时候,人们似乎才注意坐在杨家门槛上,哭作一团的女孩。她嘶哑着嗓音在喊叫:“不要打了呀,不要打了呀……。”可能是这喊声撼动了做母亲的心,傻女人也歇下了疲惫的手。
这会儿,柳保子捏亮手电筒,挤进了人群,一束光线射在傻女人的脸上,只见左半边血迹模糊,人们七嘴八舌地惊呼起来:“血,血,眼毛这块缺掉一块,快去看,去医院检查要紧,弄不好,眼睛要出毛病……。”
傻女人本能地手往脸上一抹,稠粘粘的,借着手电光一看,神色大变:“哎哟,我的眼睛疼死掉了,要瞎掉了呀……。”
女儿闻声挤进来,着急地推着父亲粗壮的大腿:“阿爸,快送妈去看看眼睛呀,快去呀!”
在人们的一再催促下,杨傻子那大手掌在胸前撸一把汗水,踌躇着说:“去看,去看!”
女人一听这话,越发大声嚎叫起来:“你这个狗心狗肺的大傻子呀,你就这样的往死里打我,哪块还有夫妻情分,我要跟你上法院去……。”
“好啊,你有种啊?我们各奔前程,离婚!”杨傻子硬梆梆地表态。
这时候,杨四妈插进来,话外有音地训斥儿子:“傻不溜秋,死嘴硬,活世宝,现人眼。”说完,在众目睽睽之下,坐到杨四爷一边去。
做媳妇的愈加不买帐了:“你一家门算计我来对付我,我天不怕来地不怕。我要和你们同归于尽。”
杨傻子的火气又冒上来了,刚地开口,突然手电光又亮了,光柱再次从女人的脸上亮起,慢慢地往下移,那件像泥潭里浸过的碎花黄衬衫已经是七零八落,显眼地展示在人们面前。光柱颤抖一下熄灭了。柳保子又开腔了:“杨傻子,还不快给你媳妇换件衣衫,去医院把眼睛看看,要真是瞎掉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男的没响,女的触动了心思,伤心地又推搡起丈夫来:“你再打嘛,打死我你就开心啦,我也不要活了。”
“我让你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看得到……。”杨傻子继续做着舆论工作。
女人又一个人打了十几下,感到无聊,自觉地歇了手,往先前杨傻子享用的椅子上一倒,闭目养起神来。傻子坐在先前女儿坐的凳子上,挨在妻子的旁边。女儿泪一把鼻涕一把地坐在门槛上,独自抽泣着,嘴里还不住地喃喃着:“阿爸,你不要打妈,你陪妈去看眼睛……。”
戏闭幕了。人们带着不满足的心态陆续走散了。一边交头接耳地发表着各自的见解。杨四妈与杨四爷在向柳保子诉说着不急气儿子与讨债媳妇给一家人带来的烦恼与羞耻。
大约又过了一个多钟头,天越发黑了。周围有的乘凉的人已发出轻微的鼾声,进入了梦乡。四周显得静悄悄的。杨傻子小心翼翼地对一旁昏昏欲睡的女人轻声说:“你把脸上的血洗一洗,换件衣衫,我陪你去街道医院看一看……。”
女人没有吱声,只是把头轻轻地摆动了一下。
1981.7.24.20:45时-22时草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