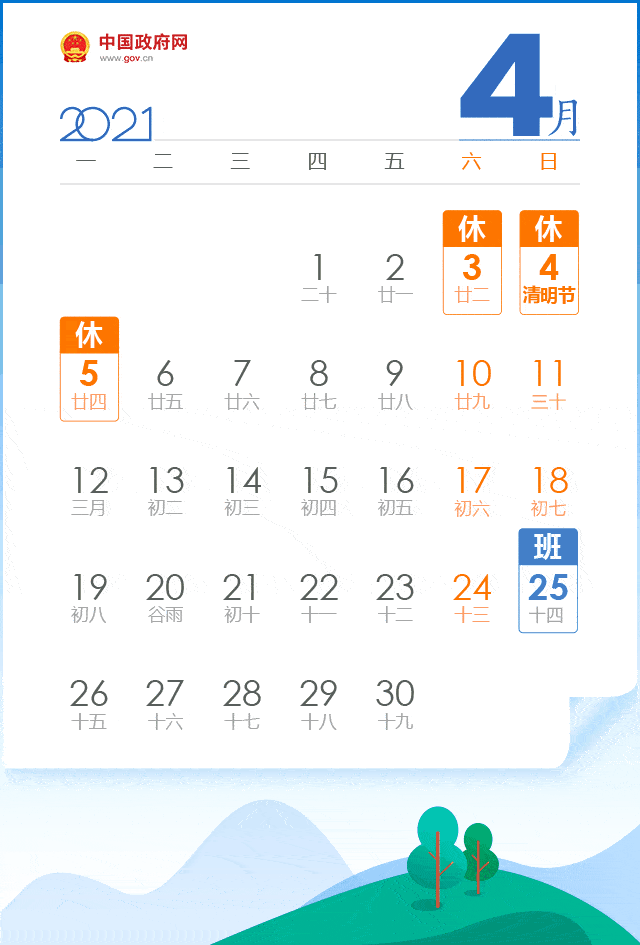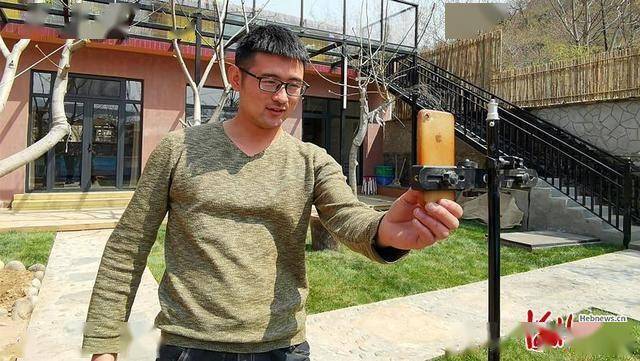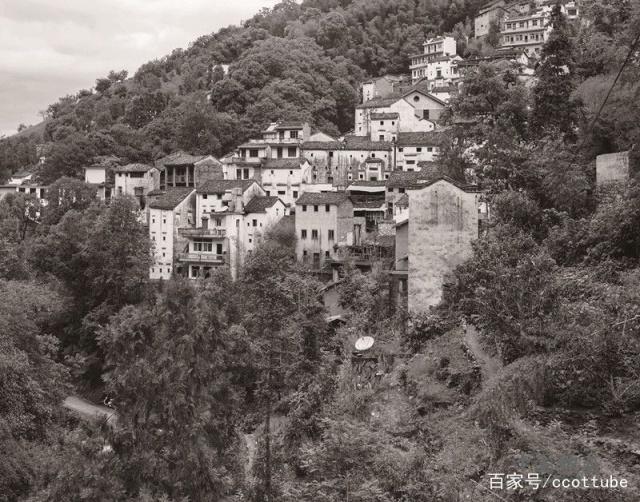新华社香港4月11日电题:浅水湾畔读萧红
新华社记者 王一娟
4月初的浅水湾,海蓝云淡,浪静风平。
无数纷沓的脚步走过香港这一著名的观海游水之地,却少有人注意到沙滩上的一座雕塑。
这座名为“飞鸟三十一”的雕塑,是为纪念埋骨于香港浅水湾的女作家萧红而立的。
她的生命旅程终结于香港
“鲁迅先生从《生死场》中,最早看到了萧红的才华,他称赞萧红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潘耀明说。
1934年,23岁的萧红创作了小说《生死场》。鲁迅亲笔写了序言:“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的经典评价,奠定了萧红在文学史上抗日作家的地位。
超世的才华若不能遇到好的时代,便注定要承受更多的苦难。
1940年1月,萧红和端木蕻良一起来到了香港。萧红做过多次关于抗战、妇女问题和文艺问题的演讲。香港的碧海蓝天和鸟语花香暂时抚慰了她漂泊的心。一年间,她完成了小说《呼兰河传》以及《马伯乐》《小城三月》等重要作品。
和当时的许多文人一样,萧红的生活穷困潦倒,写小说挣的钱有时连果腹也难做到。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曾到萧红位于尖沙咀乐道的住处拜访,惊讶于萧红居住条件的简陋和生活的寒酸。得了肺病的萧红,由于史沫特莱等友人协助,才住进了玛丽医院。
日本侵略者将战火烧到了香港,1941年,香港沦陷。连天的战火中,萧红拖着病体被人抬着从九龙逃到港岛,又在港岛西躲东藏、山上山下地逃命。战时医药紧缺,食物匮乏,这对萧红都是致命的打击。
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临时救护站含恨离世。31岁的年轻生命就此凋零。
香港成为萧红漂泊生涯的最后停泊地。她的骨灰一半埋在浅水湾(1957年移葬广州银河公墓),另一半埋在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一棵大树下。
“她曾活过冬季/最艰难的事物/也不过枯与枯萎/开与盛开。”香港诗人萍儿以这样的诗句表达后辈诗者对这位充满悲剧色彩的传奇女作家的致敬。
潘耀明说:“如果能给她一个安静的环境,萧红会写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她的文字细腻鲜活,表达方式趋于西化,如在《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中都有大段的环境描写。鲁迅先生已看到了她的潜力,认为假以时日,她会超过当时已经成名的许多女作家。”
潘耀明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多有研究,和端木蕻良、萧军等都有交往。他说,萧红本打算写《呼兰河传》第二部,可惜天不假年,只完成了“半部红楼”。
战火重创香港,也摧毁了萧红
萧红在香港居无定所。记者试图寻找当年萧红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却一无所获。
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3号,这处地方如今是一条夹在高楼中间的酒吧街。下午5时许,肤色各异的人坐在桌前浅酌,灯红酒绿,服务生来往穿梭。萧红居住过的另一处——尖沙咀乐道8号时代书店二楼,也已找不到一点昔日的痕迹。
祖国山河破碎,游子痛彻心扉。困守孤岛、奔波流离的生活,更令萧红思念北方的家园。在《呼兰河传》里,她写童年的后花园和祖父,写家乡的故事和传奇,写呼兰河的四季,写那些底层小人物。她的笔下,有欢喜,也有悲伤。
茅盾评价《呼兰河传》有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战火重创了香港,也摧毁了萧红。
离世前的最后一个秋天里,在《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中,萧红写道,我们应该献身给祖国作前卫工作,就如我们应该把失地收复一样。这是我们的命运。东北流亡同胞们,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大豆、高粱,努力吧!
潘耀明说,包括萧红在内的老一辈作家都有很浓厚的家国情怀,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强烈的认同感,因而他们的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国家是根,没有根,失去了生长的基础,就不会有未来。
生于乱世,萧红短暂的一生虽悲苦却又精彩。“人生激越之处,在于永不停息地向前,背负悲凉,仍有勇气迎接朝阳。”诗人萍儿对记者说,萧红的这段话表明了她在艰难中依然心向光明的勇气,她对家国的无尽思念和诗意的语言超越时代,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感怀和启迪。
“浅水湾头思祖国,年年香岛掩诗魂”
浅水湾沙滩上,2016年设立了“飞鸟三十一”雕塑。萧红常自比飞鸟,设计者以31只鸟代表萧红短暂的一生,从北到南,从萧红的家乡呼兰开始,每一年都有一只鸟落到她漂泊过的地方;鸟的颜色由白渐变为红,代表她生命色彩的沉淀和积累。
“浅水湾头思祖国,年年香岛掩诗魂。”广东诗人芦荻的诗句表达了人们对华年早逝的萧红的追思。“飞鸟三十一”雕塑前,偶有海内外的游人在此追忆萧红短暂而凄美的一生,感念这位对故乡和国家、民族充满深情与眷恋的女作家。
潘耀明说,萧红的作品在海外影响很大。几年前,日本一位汉学家找到他,请他一起到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祭拜萧红。但物换星移,70多年前萧红的骨灰究竟埋在哪棵大树下,虽多方寻找,仍难以确定。
记者来到位于香港半山列堤顿道的圣士提反女子中学,隔着围栏,探寻当年萧红度过生命最后时光的地方,只看见校园内一棵棵郁郁葱葱的高大树木。
有“文学洛神”美称的萧红,一生漂泊流离,却在困顿中盛开出灿烂的文学之花。
诗人萍儿说,作为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萧红挣脱了家庭的羁绊,却终究不能摆脱动荡的时代加给她的命运。这是萧红的不幸,也是时代的不幸。
萧红一生都没能摆脱战争的阴影。日本侵略者从她的老家东北开始,似乎一路追着她。她不停地漂泊,不停地书写,如杜鹃啼血,用手中的笔控诉侵略者的恶。
萧红匆匆地来了,给香港播下了文学的种子;她又匆匆离去,留给人们无限的怅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