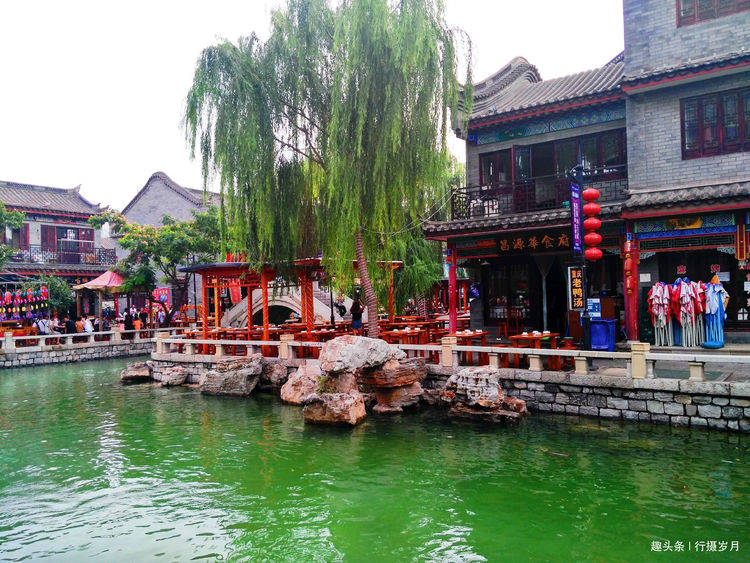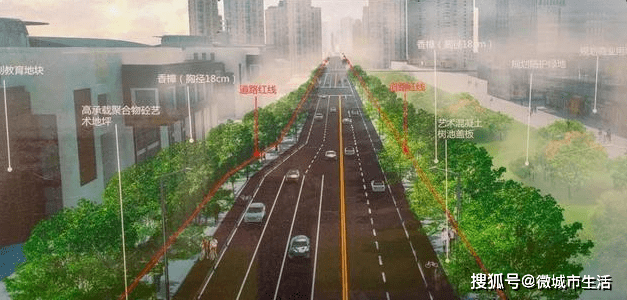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行万里路虽然早已不是什么难事,但有时难以抽身,只能作一些“诗与远方”的遐想。那么不如在书中登临高山,俯瞰湖光,饱览那无人之处的月色与雪景,来一次穿越时空的逍遥游。
登山观日出,在壮丽的大自然中辞旧迎新,颇具庄严的仪式感。在孔子曾登临而小天下的泰山上看日出,会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跟随桐城派散文大家姚鼐的《登泰山记》,去看看两百多年前的泰山日出:“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以日之正红为主色调,衬以云之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东海之红光摇曳,山峰之绛皓驳色,颜色丰富又不失纯正,流淌变化,如一幅晕染扩散的动态画卷。大自然崇高壮阔的美,足可消除鄙俗之气,使人在人格上有所提升。
姚鼐在文中自述,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二月,与好友朱孝纯由南麓登山。第二天正值除夕,五更时分,他与朱孝纯坐日观亭待日出。此前,姚鼐称病辞去四库全书馆纂修官一职,从京城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抵达泰安。辞官的原因,有人说是学术观点与同僚不合,也有人认为是因官场险恶,志向难酬而心生退意。某种意义上,《登泰山记》也可以看作一篇“归去来兮辞”。因此,我们在文中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日观以西峰“皆若偻”,似乎都在向最高峰日观峰鞠躬致敬,令人联想起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西山:“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土娄(小土丘)为类。”写山,实均为写人,凸显特立独行之高峻人格。“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圆)。少杂树,多松”一段,除了体现姚鼐作为桐城派之集大成者对雅洁文风的刻意追求与“融考据于辞章”的古文主张外,实则也别有怀抱:石之方正,松之高洁,都象征着耿介不阿、难容于世的君子之风,可看作“夫子自道”。
时值冬日,泰山正逢大雪,文中有几处文字与雪有关:苍山负雪,明烛天南;大风扬积雪击面;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白茫茫的大雪中,并无其他游人;虽有友人相伴,但文字所传达出的孤高清冷,颇近于柳宗元之“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大抵是难容于世的高士共同的心境,因此姚鼐的老师刘大櫆说姚鼐登泰山而“慨然想见隐君子之高风”,其中自有幽怀远韵。
我这样的俗世中人,除了仰慕高士之幽怀远韵外,颇为好奇的是,在这样的“雪与人膝齐”的天气里,姚鼐是以什么样的装备登山的?同样是写十二月清冷雪景的名篇,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也为我们描述了一个超凡脱俗的世界,只是这世界在水上而非山巅,时间也要更早,在明崇祯五年(1632):“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上下一白的大天地中,万物皆小,成一痕、一点、一芥,人也以“粒”计之,不过是“渺沧海之一粟”而已。与柳宗元、姚鼐相似,张岱向往的也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孤绝之境,因此选择了这样的时间独往:“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舟中除他之外只有船夫,连朱孝纯那样的知交也无。与姚鼐不同的是,张岱略略交代了一下出行与御寒的装备:小舟、毳衣、炉火。毳衣是鸟兽细毛编织的衣服,不知保暖程度与今日之羽绒服相比如何。
张岱还曾描述过西湖七月半时的盛况,感慨一无所见,只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须等到游人散尽,方可呼客纵饮,共赏月如镜新磨。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也散去,此时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