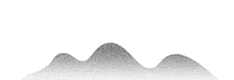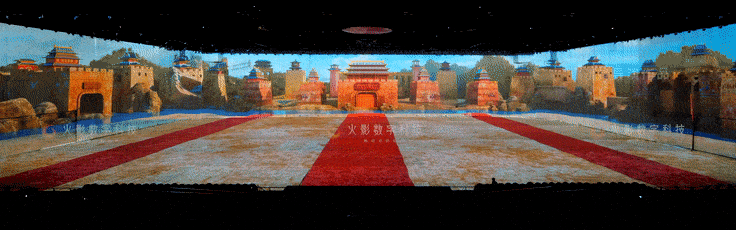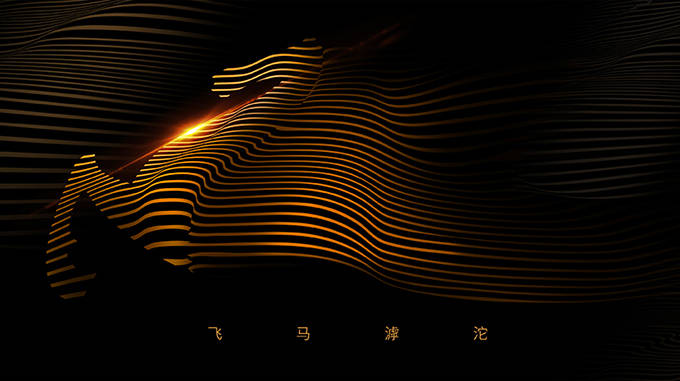除此之外,梭罗还相信小精灵和占星术,认为满月可以使他经历灵魂出窍。他和爱默生都是超验主义者(Transcendentalists),介于寡淡无味而富有教养的美国启蒙时代新教与辛辣浓郁的泛灵论神秘主义大杂烩之间,带有些许亚洲风味——我初次读《瓦尔登湖》时就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站在空旷的土地上,”爱默生在梭罗出版《瓦尔登湖》前不久向公众说,“我的头脑浸没在愉快的空气中,飞升至空无之境,所有卑劣的自负都消失殆尽。我成了一只透明的眼球。我什么也不是,我却看到一切。宇宙本体的环流从我体内穿过。我既是上帝微小的粒子,也是上帝的一部分。”

人性本善。所有的造物都存在于一个宏大的关系网之中。自然即上帝,上帝即自然。这有什么不好呢? 就在那个时候,时年32岁的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给他的朋友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写了一封信,描述了这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浪漫主义风潮。梅尔维尔欣赏同辈人描述的超验狂喜所散发的美妙、诱人的力量,但他也认识到,超验主义者站在一个危险的陡坡上,随时有可能陷入一种典型的美式唯我主义。
梅尔维尔向霍桑写道: “在万物合一中感受生命”,真是胡说八道!…… 这种“万物合一”的感觉……也有一定的道理。你应该也经常能感受得到,比如在温暖夏日躺在草地上时。你的双腿好像是伸入大地中的根茎。你的头发好像是飘在脑袋上的树叶。这是一种万物合一的感觉。但当人们把这种转瞬即逝的感觉或见解强行推广到世间的一切,事实真相便遭了殃。 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人们拒绝承认极乐的顿悟是模糊而短暂的,就麻烦了。

这种亲历田园幻想的美国式冲动,就像利奥·马克思所写,也“体现在各式乌托邦设计规划中,它们试图把美国变成西方社会的新起点”。历史又一次押了韵。正像持宗教异见的贵格会和震颤派在17至18世纪的时候从主流教会中分裂出去,建立自己幻想中的社群,19世纪怀有特殊理想——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营养方面的、性方面的皆有——的公民们来到乡下,在这个新兴的国家里建立更良好、更完美的微型国家。第一次大妄想期间,100多个乌托邦式的社群在全美的乡村地区落成。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果园公社(Fruitlands)和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组织者是波士顿郊外富裕的超验主义者。
其他定居点的规模从十几人到几百人不等,编织着疯狂、迷人、可爱的美式幻想曲。除了崇尚自由性爱的奥奈达社区(Oneida Community)——它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在美国东北部建立了多个分部,最终演变成了知名的厨具和餐具公司——很多社群都存活时间不长。但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这个现代美国梦幻之地诞生的年代,它们转世再生成为公社,卷土重来。 在19世纪初期,94%的美国人居住在乡村地区。到了1900年,将近一半人居住在小镇和城市里。

美国的人口增长为原来的14倍,经济总额是以前的70倍。但要想真正实现美国梦,人们需要住在大草原上的小房子里,住在大森林里、河岸边或湖水旁。或者更确切地说——伴随着20世纪的进程——是住在这种地方的仿制品里。这是一种完美的混合物,既有对拓荒者生活的怀旧,又有对精神纯净的追求。
因此,在梭罗扮演隐居山林者两个世纪之后,大多数美国人现在都居住在郊区或仿田园生活区,有些甚至真的叫“瓦尔登湖”(印第安纳波利斯、克利夫兰附近、底特律附近、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都有叫这个名字的地方,从大海的这一边到那一边),还有些叫“枫树湾”、“威瑟斯彭草原”、“橡树流”、“鹰之谷”、“榆树湖”、“巴林顿溪”或“海龟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