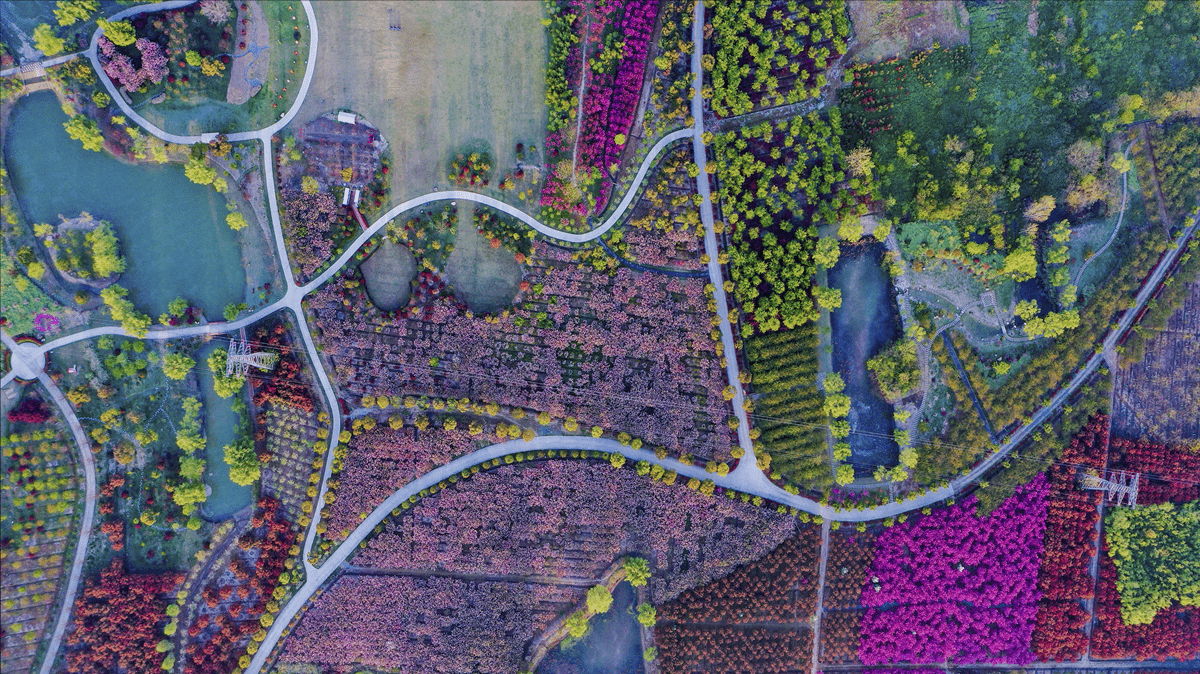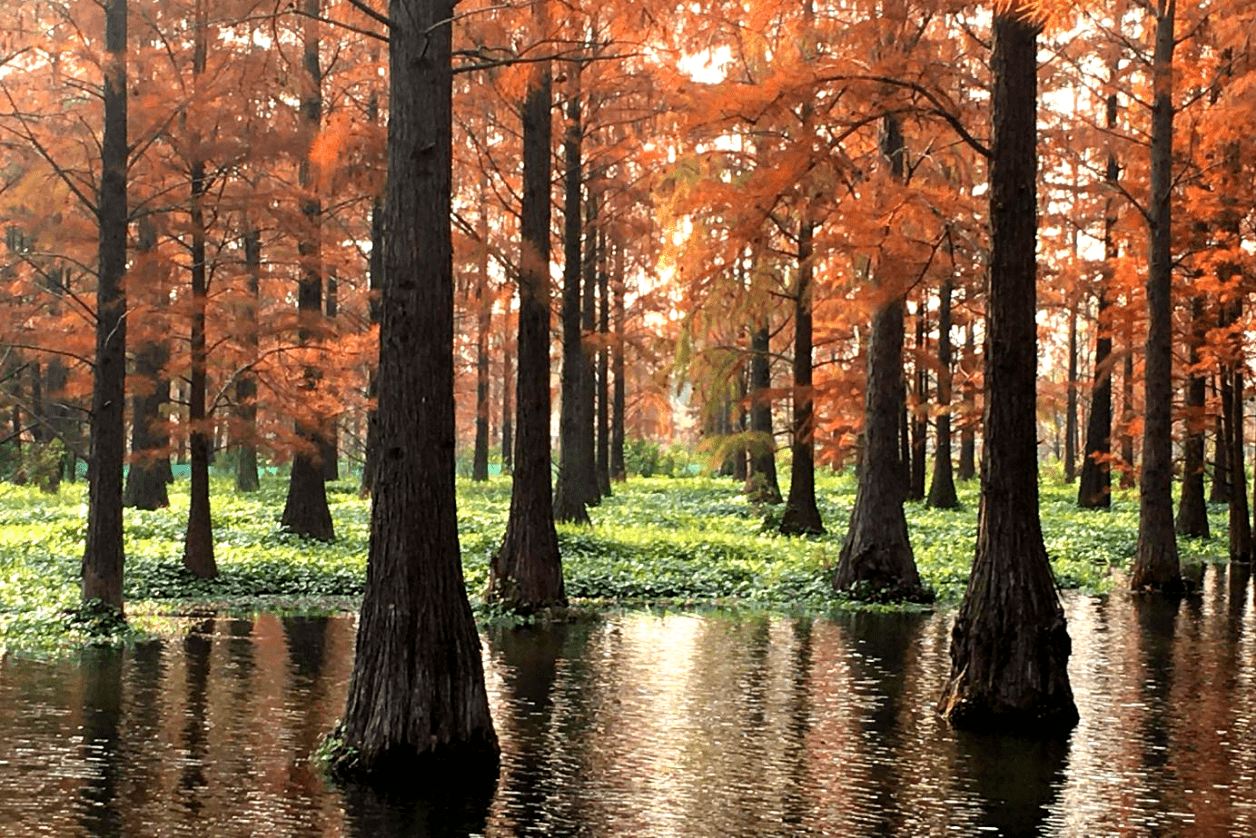汽笛声声
晓柳
元旦刚过,因家事乘动车一路北上,回到了我那阔别多日的家乡----豫南小城。由于一天前这里刚降下了国内开年第一场大雪,袖珍般的园林城市嫣然变成了雪雕城,处处银装素裹,春寒料峭。
雪后的道路光滑无比,从高铁车站出来,行走在人们刚刚从厚厚积雪中清理出的通道,步履虽然不如晴好天气那么自如,但总能看到路人伴随脚下“咯─吱、咯─吱”的踏雪声而透出的愉悦、惬意之情。朋友事先知道我到达时间,在站外见面寒暄几句后,帮我完成了高铁站外的“最后一公里”。
到家后不久,夜色降临,雪后傍晚的小城,老城区内行人稀少,空气透凉,光线暗淡,路旁电线杆上发出的灯光,昏黄、朦胧、无力,阵阵寒风不时撩起地面上一撮撮白纱糖似的雪子,这就是隆冬夜幕下真实的家乡。
子夜过后,睡梦中忽然听到了两声汽笛声,是城内火车站里发出的,而且是旅客列车启动前的笛声。这是再也熟悉不过的汽笛声了,万籁俱静的漆黑雪夜中,汽笛声穿透夜幕,虽然显得格外突出,但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尖利、刺耳,它似乎怕吵醒了熟睡的人们,音频力度适中,很轻很轻,时间长度也恰到好处,响过即收,绝不是高亢激昂,像是仅仅是给旅客一种提醒示意,显得很温柔、很温柔……,听到久违、亲切的汽笛声,我的睡意全无,不停地仔细品味着,它唤起了我的许多记忆。
早年家乡的汽笛声,伴随着全城人的生活,按照不同的功能,我将它分为三种。
先说第一种,是上班提示声,“呜──”直来直去的一段平声,它是从铁路地区一个单位发出的汽笛声(当地人平日里习惯把它称呼为“拉尾子”),主要是提示工人们上下班,相当于“闹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铁路机务段利用一台退役的蒸汽机车,为工厂生产、加工、办公以及职工食堂和浴池提供热能,工人们拆下机车顶部的汽笛,架设到厂内一个烟囱上,充当提示职工上下班的报时器,这个烟囱足有三十多层楼高,在遍地都是平房的年代,它显然是鹤立鸡群,高高耸立,格外显摆,汽笛一响,声音响彻整座城市每个角落。这个汽笛除周日休息外(那时周末只休息一天),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段响6次,早晨7点30分、下午13点30分为上班预备声,8点、14点为上班声,中午12点和傍晚18点为下班声。由于小城处于一盆地内,每当早晨7点30分第一声汽笛响过之后,全城人几乎在同时动起来了,市民们陆陆续续从各自家门走出,工人们拎着铝制饭盒,学生们背着书包,主妇们拉扯着孩童,各自向自己的目的地出发,就连政府部门的干部(那时还不称公务员)、社会上的市民们也以汽笛声为参考,不慌不忙地出门了。此时的汽笛声是平缓的,温馨的,更是家常的,在很长很长时间里,人们依托它,伴随它,它已经成为这个整个城市所有人生活中一个重要内容了。
有意思的是,这类笛声在不同的季节里,人们的感受也居然不同,春秋天的早晨,当第一声汽笛响起时,人们都会条件反射般地、自然地、慢慢的终止自己手中的活计,按照自己的节奏早餐、打点物品后,心旷神怡地在晨曦的映衬下走向自己的单位;而冬季早晨响起的笛声,相当一部分人感觉是“无奈”的,特别是那些恋床的人,对预备的第一声有种莫名的“厌烦感”,此时,他们倦意未消,而被窝暖意浓浓,由于大多数工人们居家离单位不远,往往不屑一顾,宁可省去早餐,也要多睡10、20分钟,直至距第二次上班笛声还只剩为数不多的时间,才慌不择路的向单位冲去;而夏季里的汽笛声,几乎是让所有市民们颇有感触的:盛夏三伏天的午后时分,炙热的太阳烘烤着大地,建筑物不停的扩散着热气,各种植物筋疲力尽地耷拉着脑袋,窗外树上的知了不知疲倦的鸣叫,所有的人们在勉强应付了午餐后,各自在自家平房的凉席上午休,13时30分,“呜…”,人们最不愿意听到的汽笛声又准时响了起来,惺忪中的人们感觉此时的汽笛声,就像大地上的万物一样,是乏力的、干涸的、甚至是嘶哑的,但不管是无奈,还是慢条斯理,守时、有纪律的铁路职工仍然会准点上班。
进入八十年代后期,出于设备的更新,机车换代升级以及环境保护需求等因素,这个多年影响全城几代人生活的汽笛光荣“下岗”了。
第二种就是事故信号声,“呜…呜…呜…”连续的叫着,它是救援时紧急呼叫的汽笛声,那时,凡是发生影响行车的各种事故,诸如机车脱轨、火车相撞(内部称为“追尾”)、甚至洪水断道时,都要通过这个汽笛发出“有事故了!”的信号,这类汽笛声,一般情况下呼叫三轮,每轮响三声,每声时长5秒,汽笛声响过之后,有两个群体立马动作起来,一个是所有单位的头头脑脑们,即刻他们中断各种事务,急速向自己的单位奔去了解情况,尔后,或是赶往事故发生地担当救援、协调和辅助工作,大家都是一个心思,尽快处理事故,恢复通车。另一个群体就是铁路职工家属了,主要是火车司机家里的主妇们,那些有出乘在外未归司机家庭的妻子们,不知事故的级别有多高?事故的性质有多重?是不是他们家男人开车出的事故?听到那急促、凄厉、刺耳甚至是撕心裂肺的汽笛声,心里倍受煎熬,要么相互间打听消息,要么自己跑到单位了解实情,直至弄个水落石出,悬着的心才放下。
相对而言,这类汽笛声在漫长的生活中还是极少出现,当然,也是铁路部门和家属不愿听到的。
第三种是火车启动前或是在进站时发出的示意声, “呜……”长长的声音,家乡小城属于丘陵地貌,车站处于小城偏北,东西走向,因此京广铁路在城内呈“S”形穿城而过,出城向北是个弯道,且又是上坡地段,因此,每列向北发出的火车出站后必定要鸣笛,旅客列车更多的是一声长鸣伴随着车轮与铁轨摩擦“咔嚓、咔嚓”声,而牵引货物的列车通过这个地段时,由于负重爬坡,则是一声长吼中夹杂着火车头排气筒那“哄─哄─哄”的喘气声,儿时的家,在火车站北端尽头,每逢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的心跳和呼吸的节奏,总会与火车那喘气声合拍的,久而久之,我能轻易从汽笛声中迅速判别,是旅客列车还是货物列车。每台机车的传出的笛声音质是不一样的,有的脆亮、有的憨厚、有的文气、有的粗放。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铁路家属区距火车进城的铁路一步之遥,尤其是火车头库与职工住宅一墙之隔,火车头返回车库是都要鸣笛示意的,天长地久,大车司机的老婆媳妇们都记住了自己男人驾驶机车发出的汽笛声,便掌握了一个规律,只要在白天听到熟悉的汽笛声,便清楚的知道当家的车回来了,紧接着就开始忙乎打点回来后的午餐或者晚餐,司机们有时也下意识地多摁几声汽笛,意在向家人报平安:“我回来了”,就连刚刚从汽笛声判别不是自家男人车的邻居也免不了昂上一句“他王嫂,赶紧烧菜吧(当地口语把“做饭”称为“烧菜”),你老头子回来了!”前后洋溢着邻里间大家庭似的关系,充满着随意、安逸和家常气氛,由此可见,这时的汽笛声就是一种对话,一种暗示,更是一种默契。
车轮滚滚,时代在前进。家乡的汽笛声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挥之不去的,它给了我无穷的回味,现实生活中的汽笛声,又给了我无尽的遐想。现在,无论是公差外出,还是往返故里,几乎都是乘坐动车组,每当乘坐时我特别留意动车组发出的汽笛声:在快速通过车站时,总感觉动车组发出的笛声有气贯长虹、一往无前的磅礴气势,无不震撼,如果说以往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发出的声音是单一的,是吼出来的、是憋出来的,那动车组的笛声是从车头那多管里迸发出来的,似乎含有和铉音,更有韵律,它在进站时发出那短促的声响并不刺耳,尤其是它起步前的音调与其他类型的机车的确不同,响亮而不燥人,显得果断与自信,这个笛声不再那么单调纤细,也不再那么沉闷仓促,这个声音已经融汇着现代社会的新元素,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听到动车缓缓起步前的笛声,从那流线型车身缓缓起步中,仿佛看到它在挥手与站台上的旅客告别,从那奔驰的时速中似乎看到已它迫不及待地要冲向前方与新时代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