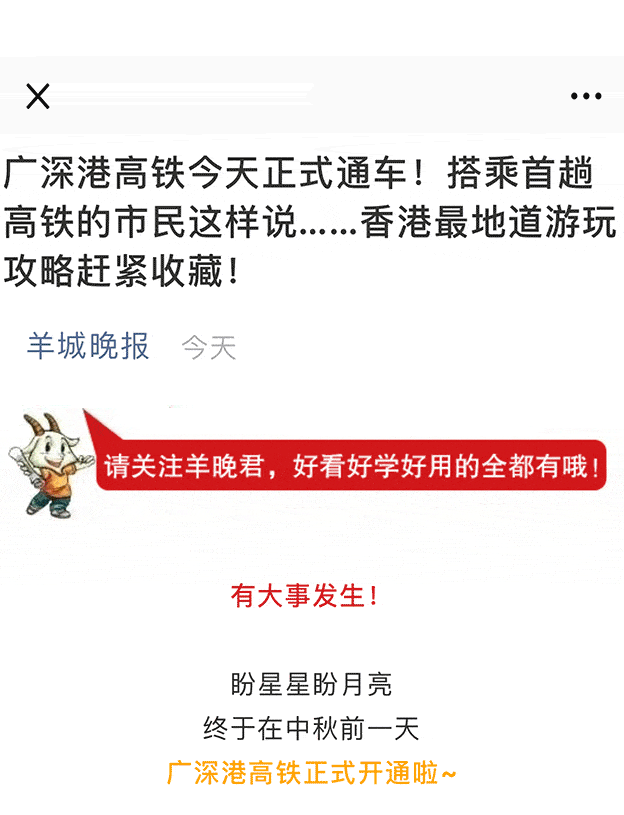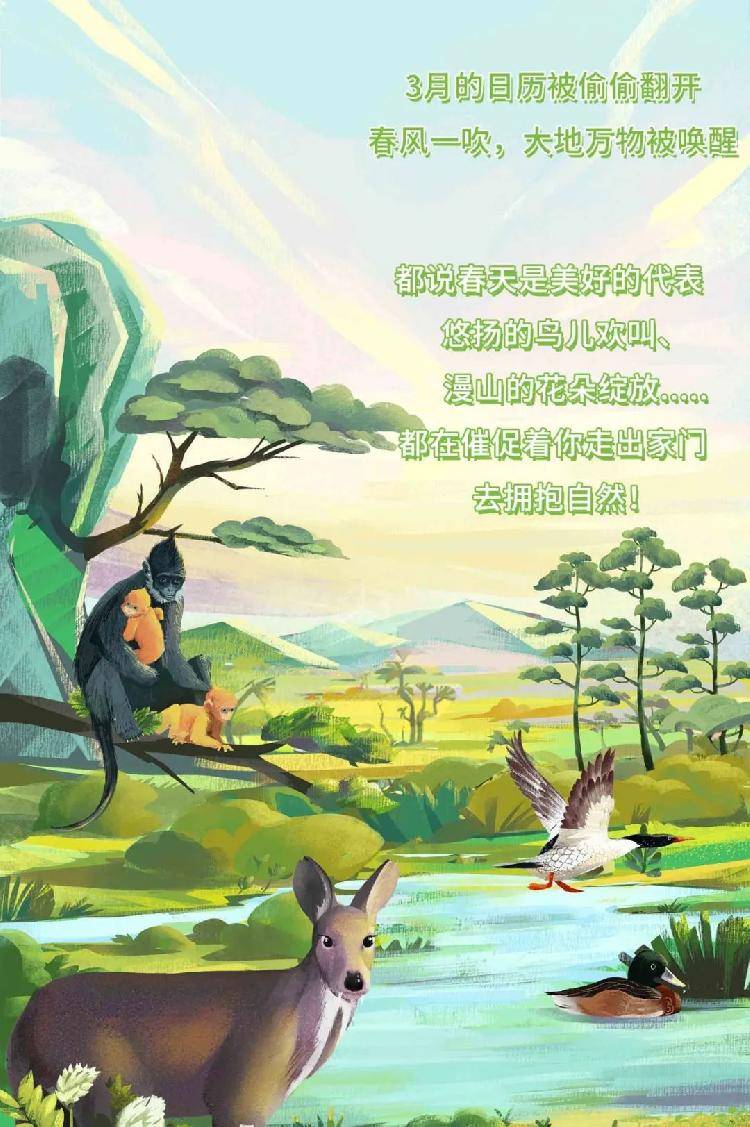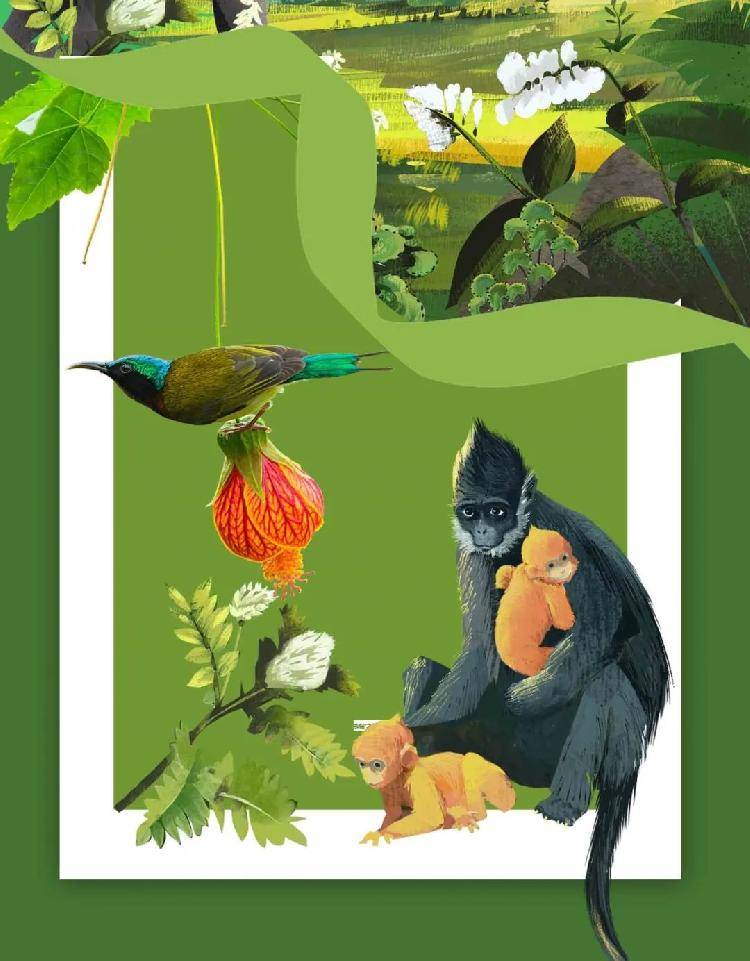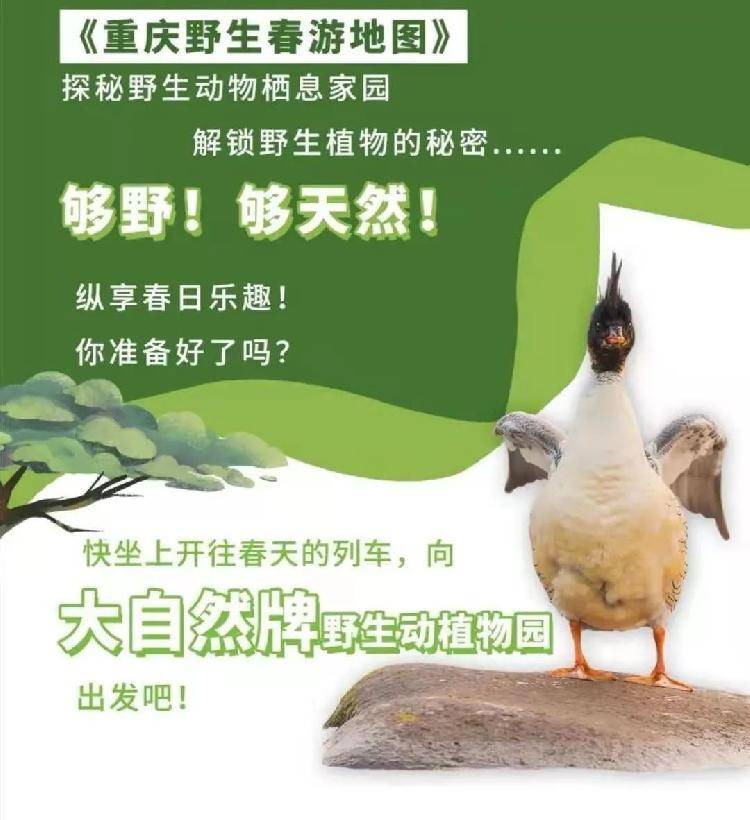风景旧曾谙,放到北方天空下是恰当的。而风景永远新鲜,更适合拿来见证南方流动的时间。在北方,十月的景物已开始萧瑟,几乎所有的绿都已成枯。而在南方,一年四季绿遥遥和路迢迢融为一体的写照,常常让看风景的人,进入奇幻的想象。
酱紫FM出品

值班主播 |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惠天骄
在北方,一马平川的北方,人坐在车里,同样的车速,窗外日光下一排苍黄的速生杨,焦褐的大叶子,看上去有种被烧灼的味道,它们在许巍的歌声里如长驻的少年,仿佛要让初来乍到的我一次看个够。辽阔的玉米地,远远出现白头巾的影子,开拖拉机的农民,载着堆积成山的玉米秆,摇摇摆摆从田间驶向村庄。
这样的画面从窗外慢镜头一样后移。

资料图/视觉中国
我以为我们已经走了很远,在一条坦直的高速公路上,并排行驶超车的概率极低,来往车辆比视野中很久闪现的房舍和商店更稀疏。那些后移的玉米田和路边的速生杨,像穿着笨重的北方农民,并未移步太远。在北方,车窗外的风景,不适宜用“消失”这个词语代替速度,因为车里看风景的人,几次回头,那些原风景还在歌声里踯躅。
若是在南方,我来时的南方,窗外的丘陵、河流与花草树木,早已一晃而过。小卖部、路人、屋基、庄稼、猫和狗随处可见,防护栏之外的零散风景,距离公路如同胶水粘贴紧密。它们在车窗外,就像俄裔美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句——波浪在波浪式的窗帘后面跌落。南方风景的丰富构成,是单调北方没法抗衡的。
原以为这是南北行驶的速度之差,究其原因,是窗外的参照物发生了微妙变化。因为视线的苍凉和空旷无限拉远,近处障眼的植物、建筑和人皆不多。还有一种可能,透明的阳光也在发生作用,感觉上的缓慢便成了思绪的一种迟疑。在南方,车窗外绿色的屏障从不稀缺,随时把人的视野填得满满当当,来往的车辆交汇密集,惊心动魄的是蚯蚓般的地理路线,在云雾重重的视线干扰下,导致风景在车窗外闪得比下落不明的云朵更快。
风景旧曾谙,放到北方天空下是恰当的。当然,我不是指曾经去过的北方,风景有多么熟悉和美好,仅是车窗外扫描的印象。而风景永远新鲜,更适合拿来见证南方流动的时间。在北方,十月的景物已开始萧瑟,几乎所有的绿都已成枯。而在南方,一年四季绿遥遥和路迢迢融为一体的写照,常常让看风景的人,进入奇幻的想象。
几年前,我曾跟着一群跳广场舞的大妈,去一个名叫米亚罗的地方,看山上的彩林。层峦叠嶂的彩林,车窗外游走的五光十色,在西康怀抱的一座高原上,呈现出童话般的世界。当我透过车窗,望着这片梦境般的林子越来越近的时候,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李可染的名作《万山红遍》,心灵的窗户顿时涌进多元的矿物岩彩,像是产生了人在画中游的体验。
回过头,大妈们早已开始了她们的手舞足蹈,仿佛一件件时光遗忘的往事,从她们的手上飘动的纱巾红里失而复得。其中有一位是我的姑姑,她关闭已久的心窗由此打开。大妈们脸上绽放的灿烂和青春之光,完全可以同山中的彩林比美。当我把悄悄抓拍的照片递到姑姑眼前时,顿时,她紧张得双手捂住了嘴巴——天啦,这是我吗?怎么会有这样的笑容?
那一瞬间,多少心动的画面倒回她飘满落叶的小径,也许只有她眼中闪亮的泪光记得。大妈们过去起早贪黑的光阴,多交给了工作和家庭,姑姑的心窗关闭太久太久。
我常受邀去一些地方采风。许多跨省的邀约,先要乘坐飞机,再坐列车或汽车。异乡最初的风景,透过车窗一步步抵达眼底,慢慢形成一种辨识。车辆行进速度,决定着人的体味深浅。但有一帧车窗外的风景,只是因为不经意遇见,从此再也无法忘记。
那是中印边境线上的西藏。
太阳的光斑打在茫茫雪线,我们的车在雪山湖泊的倒影中,笨重如蜗牛缓慢独行。远远的,突然一个或多个站在路边朝我们行军礼的小男孩,顿时撞击眼球。寒风吹彻,他们天真的眼神,俨然刻进了冷霜,他们举起右手的肃穆表情,绝不逊于一个饱经沧桑洗礼的军人。
来源 | 羊城晚报2020年12月23日A15版
文字 | 凌仕江
编辑 | 木言
校对 | 周勇
审核 | 艾渝
签发 | 孙朝方
猜你喜欢
按以下步骤
把羊晚君设为“星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