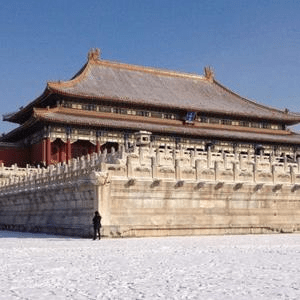为节日期间作精神漫游的朋友提供阅读选项
——小编
文丨包临轩
大剧院
郊外的空旷,是另一种声音,仔细倾听,发觉至少有风声隐含其中,且不论其它。风声何尝不是起伏变幻的音乐呢?甚至,那风声有时也是激越的,尤其当季节转换的当口,风成为季节代言的时候。
然而,对于渴望洪钟大吕或者笙歌管弦的耳朵来说,仅有大自然的风声,也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大剧院应运而生。
A
大剧院落成,即成为哈尔滨的新地标。
在大剧院诞生之前,这座城市的地标建筑可谓不一而足,最出名的,相继有霁虹桥、尼古拉大教堂、防洪纪念塔、松花江公路大桥、索菲亚教堂等等,这些地标性建筑,出现在媒体无以计数的报道中,出现在影视和网剧的镜头里,出现在摄影家和画家的作品中,出现在新年和旅游明信片上,它们声名远播,令人耳熟能详。
一部城市地标史,就是对一个城市发展史的有力勾勒,大剧院的出场,标志着城市品味又跃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哈尔滨的现代性增加了一个可被强烈感知的新维度。文化建筑特色风格鲜明,一流的剧院专业技术标准,形式感与专业内涵的完美融合,让大剧院迅速成为后来居上的都市新地标。
张澍/制
虽然松花江一如既往地宽阔,江水一如从前那样由西向东,时时刻刻响应着远方蓝色的召唤,但大剧院的出现,似乎第一次从视觉上拉近了两岸的距离,直觉中,两岸彼此间不再是以往的遥遥相望,似乎是近在咫尺了。
平地崛起雪山一样熠熠生辉的银色和流畅的造型,极为醒目地扑入人们的视野。
当驾车从桥上驶过,或者步行于滨洲铁路桥人行道上,那银色的矫健身影会映入眼帘。
与海对江水的召唤不同,那银色,分明是另一种调性的召唤,是冰清玉洁、晶莹剔透在召唤,那是对着站在南岸驻足的人,或者是对江上眺望的人发出的。
是召唤,也是诱惑。
B
夏季的一个午后,我从太阳岛绿道一直北行,直至登上北岸。
引导我一直向前的,是大剧院。
起初沿着中东铁路公园的核心景区滨洲桥步道,从南岸一路漫步走到太阳岛的,我的本意是想走走太阳岛上的长长绿道,因为这条绿道已经铺设了很长时间,一直不曾走过。
从滨洲桥走到太阳岛,是一条不可多得的陆路直线,虽然距离最短,但却很少有人这样子徒步过来,这是一条还不太广为人知的崭新捷径。
果然,我很快就顺风顺水地抵达了太阳岛。
走完绿道之后,本来想折返江南,但是无意间抬头北望,大剧院一下子跳入了我的视野。
张澍/制
太阳岛和大剧院原来相邻,从这个点位上看,两者距离这么近,这可是个意外发现。
那就继续前行,顺便去大剧院那儿看看吧。当时心中也有几分踌躇,老话说望山跑死马,大剧院会不会像一匹马似的,看着很近,实际上挺远呢?但是,它很真切很分明地就在眼前嘛,但愿我没产生错觉。
下了决心,走!
又沿着滨洲线继续前行,甚至无需拐弯,很快,这座艺术宫殿逐渐在视野里全面真实地裸露出来。
坐北朝南,临水而居,大剧院像一个王者居高临下,太阳岛和松花江一并尽收眼底。
纳入大剧院视野里的,自是松花江沿岸又一处绝好景致。
大剧院所处的滨水湿地,本来就是松花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太阳岛,又不过是松花江主道与江岔子之间形成的一片面积较大的沙洲,假如没有江北大堤的阻断,太阳岛与北岸滨江湿地实际上是可以一体化的。
所以,太阳岛和坐落于湿地之中的大剧院,原本就同处一个水域,不过是一南一北,方位不同而已。
近些年来,滨江湿地纳入了城市的认知范围,这大大拓展了松花江北岸的宽度,北岸景观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松花江连同它的湿地资源,一体两景,相互映衬,展开了大哈尔滨的新地理画卷,北岸从此不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扇面了。
这也因此带动了太阳岛的新生,随着哈尔滨沿江湿地的蓬勃扩展,太阳岛本身也随之更新了内涵,原来老哈尔滨人心目中的太阳岛,事实上已经变“小”了。
在此意义上,大剧院正是处在太阳岛延展了的外围,成了一对彼此呼应的伙伴。
只不过,目前湿地、太阳岛,加上大剧院这些崭新故事,尚未经过时光的足够沉淀,但人们对此种格局的普遍认知,正在加速形成。
张澍/制
大剧院靠近松花江岸边,且不论其周边整体环境,仅仅感受其南侧的水面,就已足够迷人。
那与浅浅沙滩相接的水面上,点缀着若干袖珍岛屿,也就是小小的沙洲。沙洲上面生长着一簇簇榆树、杨树和柳树,以及灌木丛,树丛中有木船和钓鱼者的身影不时地闪现。
由于水量的变化和年份、季节的不同,这些沙洲也是动态地改变着,时大时小,时隐时现,但是那上面的草木,却一直未曾被真正淹没,乔木伸展着身姿,灌木和蒿草们抱团儿,生生不息,成为人们流连的好风光。
在这些星星点点的沙洲的南侧,也就是这水面的最南端,正好就是太阳岛北端,一片茂密的沙洲森林,以浓淡不一的各种绿色,墨绿、黄绿、浅绿,向着太阳岛的纵深之处绵延不已。
正是因为有了大剧院的兴建和落成,太阳岛北侧的这一脉从前无缘得见的风景,其画轴般的另类风情,才得以徐徐展开,得以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对于大剧院本身来说,这自然只是一个副产品,但是对于渴望野外休闲、露营和垂钓的本地人来说,对于热爱着太阳岛的市民和游客来说,这副产品可能反倒是他们心目中的主产品呢,他们在大剧院欣赏音乐会和演出节目之余,在江堤上小坐,或款步而行,太阳岛北侧的独异风景,和太阳岛老区那些经年习惯了的熟悉景象,当然有着不同的新奇之处。
C
大剧院当然属于都市,是大都市强有力的音符,是都市的奏鸣,但它所处的位置,却是一片旷野。
这似乎完全符合建造者心目中的定位,音乐这只自由自在的看不见翅膀的精灵,从来都渴求着无拘无束的翱翔空间,而江北恰好如此天高地阔,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适合安放一个音乐时而敛翅时而振翅起飞的栖息地了。
大剧院自身并不是高层建筑,湿地的自然地势趋于低缓,也使得建筑并未获得什么天然的制高点,然而,大剧院却极具雄伟宏大的气度。这气度,大概就是得益于它所处地理空间的开放性吧?
大剧院是松花江的儿子,是松花江畔的水、冰和雪的化身与象征。只要来到江边,即使在南岸,你也能够以目光和它相遇。等到你跨江而行,无论是在船上、在江中游泳,在无数个点位,只要你抬头,你就更可以看到它,在大桥上,你会更加无比清晰地看到它,并强烈地感受到它发出的光芒。
无需刻意寻找,你会很轻易地发现!
大剧院,你无法忽略它的存在,它会自动闯入你的视野,它似乎有着艺术家式的顽强表现力和表达欲,未闻音乐之声,先见音乐之形貌!从诞生那一刻起,似乎注定了它将摄人魂魄。
丁毅/绘
然而,它并非以挺胸昂首、高调宣示的方式,也并未铺陈和渲染,它甚至取着卧姿,但却坦荡地敞开着自己。可是,它到底以怎样匪夷所思的魔术,如此强烈地占据了你的视野呢?
只要你北望松花江,只要你接近了松花江北岸,似乎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大剧院都会进入你的视野。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罗兰•巴特笔下的埃菲尔铁塔,人们在巴黎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到这一尊竖起来的钢铁,它是巴黎人和巴黎游客无法回避的存在,除非你躲进铁塔内部,你才会很短暂地看不见它,否则,铁塔就始终无处不在,并且是高耸着的,针刺一般尖锐地,不容分说地。
大剧院之于哈尔滨,似乎与此类似,只要你在松花江附近出现,你总会在不经意间看到那团银色的光辉,闪耀在天空下。
但是在气质上,大剧院与埃菲尔铁塔迥然不同,它不像埃菲尔铁塔那样呆板,那样死硬,那样灰黑,那铁塔是冰冷孤立地站在那里,含义不明,却给人以拒绝感。
大剧院则不同,作为音乐艺术的载体,作为文化建筑,它的银白色,它的三维曲面,它的流线型,都始终洋溢着都市生活流畅的气韵,它虽然饱含着超越的冲动,却不是要摆脱人间。
D
大剧院坐落在湿地之中,而湿地不过是原野的一种形态,浅浅的流水或静水穿插其间,但草木葳蕤。
这是一座原野上的剧院。
从西往东,是看大剧院一个很别致的角度。
徒步中,需要时时透过大地上纷繁树木的参差和掩映,才看得见大剧院的上半部分,它构成了旷野画框的远景,在这一片微微起伏的大地景观的远处,大剧院亮出了它的银色。
随着对它的趋近,大剧院很快占领了视距中心,于是成就了乡野和人文的一种不间断的对比,这是蓬勃的自然和冷冽的钢铁的一种对比,随着远近距离的动态变化,大剧院和周边环境的比例也是在变动中,就有了移步即换景,步步景不同的惊奇不断的效果。
丁毅/绘
那从地面上冒出来的奇异模块,像天外抛入的一块陨石,起初给人以突兀之感,似乎有一份硬生生的意外,打破郊外大地原初的环境氛围,以异质侵入的方式发生了。
然而我们的内心知道,正是因为大剧院的诞生,松北这片被自然野性主宰的粗糙肌体,从此被注入了现代和时尚的血液,新的基因得以植入,这片区域将因此而变得激情澎湃,一个生态与人文共生的全新时代到来了,两者融合起来的新景观正在全新地生成。
还记得诗人斯蒂文斯吧?他把想象中的坛子,置于田纳西的山顶,坛子使凌乱的荒野,围着山峰排列,于是荒野向坛子涌起,匍匐在四周,再不荒莽,坛子在地上矗立,君临四面八方,仿佛成了田纳西的桂冠。
谁能想到,在遥远的东方,在数十年后的哈尔滨的大地,比诗人想象中的坛子大出数万倍的大剧院,横空出世了!
这座大剧院吸纳了荒野和大地的精华,草木与溪流和羊肠小道,纷纷向着它奔涌、汇聚,这大体量的现代容器,成功酿就了艺术与生活、与自然完美融合的玉液琼浆,从此让人饮之不竭。
张澍/制
大剧院的建筑师说过,他的团队,是取松花江的风和水的形态气韵,来用心雕琢这座艺术宫殿的造型和每一个细节,从都市的梦幻和内心里孵化出一座雪峰。
这雪峰,这银色殿堂,聚集起松北无边旷野和两岸人们漫游飘荡的神思,凝成强劲超拔的灵魂,以旋律、歌声和戏剧的方式,让音乐的神奇力量,从一大一小拥有最高艺术标准的两个剧场中间,从多岛式看台的观众席上,一场接一场地不断生发,浸润人心并冉冉升腾,向着剧场和它的公共广场扩散,向着观光廊道和可供露天演出的观景露台扩散。
向着松花江两岸水天一色的辽阔空间,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