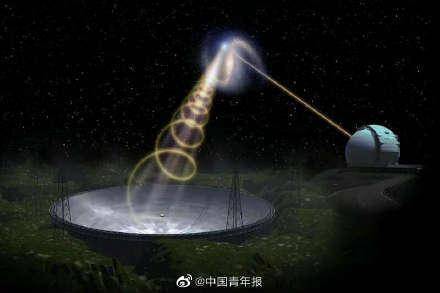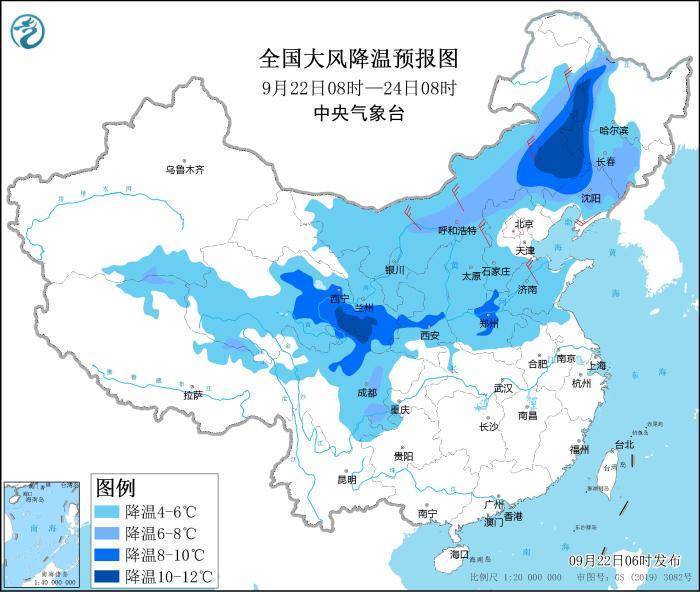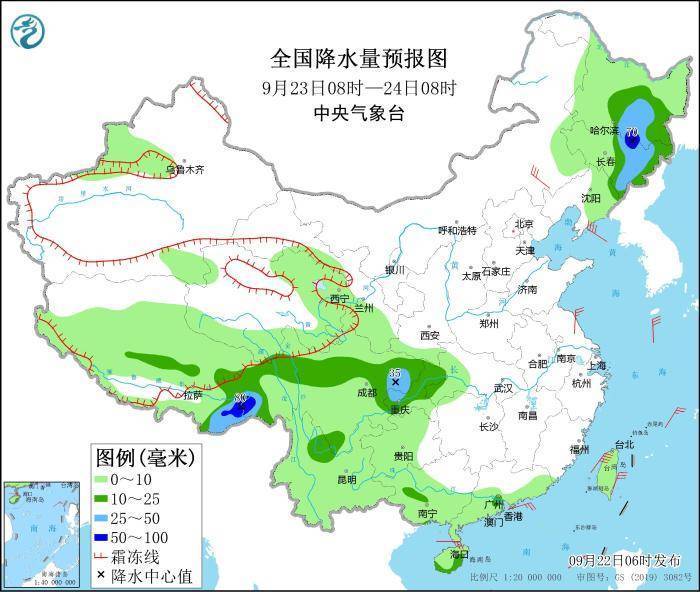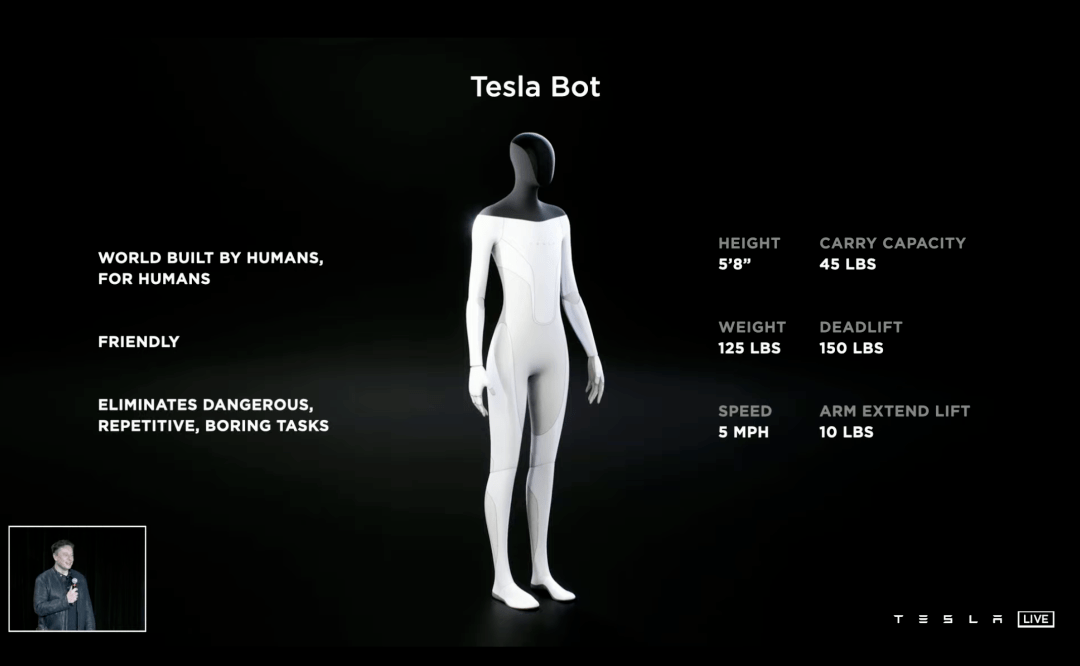她是一位十足的学霸,一位衣食无忧的娇小姐,却在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里,选择了敦煌这一“苦寒之地”,一待就是半个世纪;
她放弃了与丈夫儿子团聚的机会,将自己的大半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敦煌莫高窟,致力于敦煌莫高窟的永续利用和永久保存这一“逆天”之举。
她就是樊锦诗,敦煌研究院的名誉院长,也是我国“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的获得者。
与莫高窟的不解之缘
樊锦诗第一次了解到莫高窟,是在中学历史课本上,那时的她看到历史书上的描述就被深深的吸引,刚巧,从北大毕业分配实习的时候,就被分配到了敦煌,那时的她满心欢喜,想要一睹莫高窟的美。
但是,在抵达敦煌之后,眼前的景象也着实吓到了她,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没有卫生设施,宿舍就在莫高窟旁的一座破庙里,天花板是用芦苇杆搭起来的,晚上睡觉时还会掉下来老鼠。
有次起夜,樊锦诗刚推开屋门就看到两只闪着绿光的“狼”的眼睛,吓得赶紧跑回屋里,一整晚都没再睡好,第二天出门,才发现那原来是一头驴。
作为一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娇小姐,樊锦诗本就体弱多病,再加上敦煌这恶劣的环境,她很快就水土不服晕倒,只能提前结束实习。当时的樊锦诗觉得,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然而,造化弄人,实习期结束正式分配工作的时候,她又一次被分配到了敦煌。
父亲舍不得自己的女儿去那么远的地方受苦,于是就写了一封长信给校领导,但是这封信还是被樊锦诗给截了下来。她说: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就这样,樊锦诗又一次回到了那个让她喜忧参半的地方,也开始了自己与当时的男友,也就是后来的爱人彭金章的“牛郎织女”一般的生活。
分隔两地的爱人
樊锦诗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的彭金章约定,自己只在敦煌“玩”三年,看够了莫高窟的美就申请调到武汉去。结果三年期满之后刚巧赶上特殊时期,樊锦诗因此没能兑现诺言,不过二人还是在1967年成婚,并且在婚后第二年生下了第一个儿子。
樊锦诗临盆时,就在敦煌的一间破旧的病房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丈夫彭金章也直到儿子降生近一周之后才赶到敦煌与妻儿团聚,但是,作为武汉大学的骨干,彭金章不得不在十天之后就匆忙赶回了武汉,留下樊锦诗独自一人照看孩子。
莫高窟的研究任务十分繁重,樊锦诗并不能像其他妈妈们一样倾心照顾自己的孩子,只能将孩子锁在屋里,每天抽出一点点时间来给孩子喂一些吃的,甚至有次回家时,孩子已经掉在了地上,脸上都是煤渣,心痛之余,樊锦诗只能做“蜡烛包”,将孩子用被子裹着捆起来。然而这并非是长久之计,无奈之下,樊锦诗只能将孩子送到了河北,让丈夫的姐姐抚养。
1973年二儿子出生之后,又将大儿子送到武汉,二儿子再送到河北。
在这段日子里,樊锦诗也曾努力争取调到武汉工作,但是一直未果,直到1986年领导终于松了口,樊锦诗却发现自己离不开敦煌了,于是,丈夫彭金章甘愿放弃了自己在武汉大学的工作,跟随樊锦诗一同去了敦煌,至此才结束了二人长达19年的“牛郎织女”一般的生活。
“不近人情”的院长
面对家人的樊锦诗总是柔情似水,而对待工作的她严厉认真,“不近人情”。
初到敦煌的那几年里,樊锦诗只要有空就会进莫高窟,仔细研究洞窟内的壁画和彩塑,每日的工作安排都满满当当,当时作为樊锦诗秘书的魏丹就曾说樊锦诗“太可怕了”,自己刚工作的第一年常因为跟不上工作进度而被“骂哭”。
莫高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古典文化艺术宝库,然而它现在正以非常缓慢的、不可逆转的速度在消逝,七十多年前法国人伯希所拍摄的莫高窟中,一些彩塑和壁画的一部分已经消失不见,风沙侵袭和各种病害使得莫高窟不再完整,抢救莫高窟的工作已刻不容缓。
为了使莫高窟能够永久保存,樊锦诗在朋友的启发下想到了建立数字化档案,然而以当时的科技手段根本无法实现,在尝试多年无果之后,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达成合作,一起为莫高窟建立数字化档案。
在合作期间,樊锦诗面对当时强大的美国也一样“不近人情”,初次见面就直言“你们只是一群富有的美国人”。
功德无量的保卫工作
在敦煌这半个多世纪的日子里,樊锦诗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进去。为了方便工作,她剪了一头极短的头发,几十年都没再留长,每天日思夜想的都是莫高窟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守卫莫高窟已经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最初的北朝、隋和唐早期的分期断代研究,到后来提出的建立科学的数字化档案,无一不对后来人们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和参考。
樊锦诗这一生,无愧于敦煌,有愧于家庭,也怠慢了自己,作为一个亲眼见证了抗战和新中国成立的女性,她的骨子里都铭刻着强烈的建设国家的主人翁意识,甘愿在敦煌过着“苦行僧”生活,也要守卫我们的宝贵遗产。也正是因为有着像樊锦诗这样的无私奉献的人们,才有了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莫高窟的珍贵档案。
如今,敦煌研究院树立着一座以樊锦诗为原型的雕像——《青春》,樊锦诗也被亲切地称为“敦煌的女儿”。
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樊锦诗守护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宝,使得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得以永久性保存,实现了保护和利用的双赢。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这件事功德无量”。
文/扒拉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