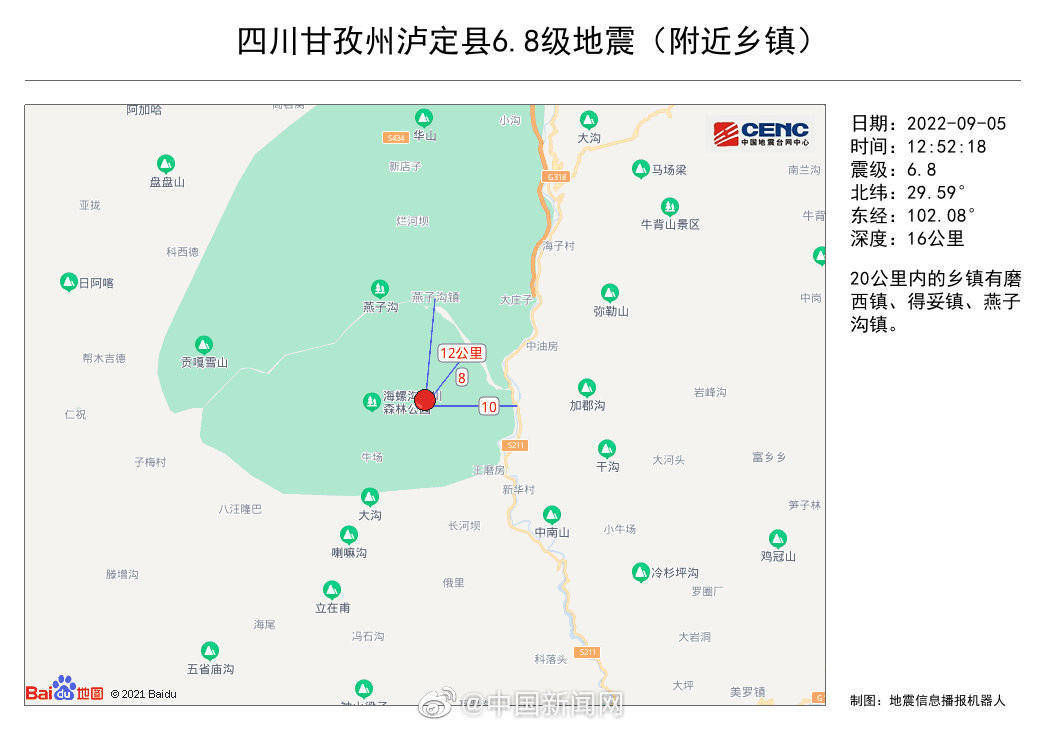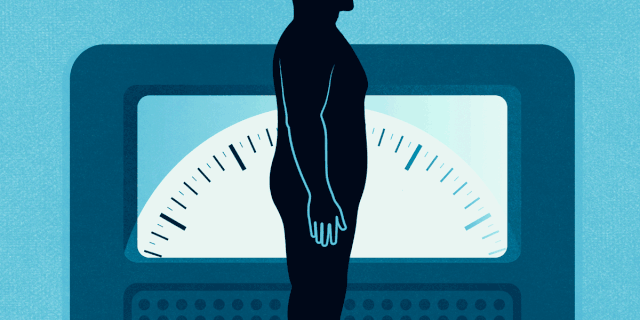去年深秋,在北京。
那一天原是想到香山。挤在公共汽车里,距香山还有一站路的地方,车停了,也是一个站点,好像叫卧佛寺站。售票员喊:“卧佛寺到了,有看大卧佛、曹雪芹故居的,在这儿下车。”心中一动,再看身周挤满了的人没有一个下车,就挤出去,下车了。
下车后,眺望不远处的香山,红叶灿灿,有点惆怅。是惆怅,不是后悔。其实我在这个地方下车,并不是为了卧佛寺和曹雪芹,我是中华禅学会会员,但只是对佛教的部分理论有兴趣,对佛像佛画佛门胜地者流并无太大兴趣;我喜欢读书,却不是特别喜欢读那部伟大的《红楼梦》,对这部小说颇有不恭,并写成文字,在《山西日报》、《福建日报》等地方发过,引来部分“红楼迷”的批评。简短截说一句话,我之所以未到香山就下车,只是因为小客车里人太多。当时正是赏红叶的最好季节,我想香山也许就是个放大了的客车。我很向往心目中红叶漫卷的香山,却不想挤到生满红叶的客车上去,这是我在卧佛寺站下车的惟一理由。
直到走到四顾无人的曹雪芹故居——黄叶村前,站住,长长一段时间心境茫然,然后恢复过来,心中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也许我下车是冥冥中的安排,让我在30岁之前,得机会与雪芹一晤。其时天晴,天朗,云淡,云轻。远远近近的山,青自青,红自红,树色苍茫。黄叶村村周,木制篱笆蜿蜒环绕,与远处的树色合为一体。门亦木制,门上有檐,檐覆黄草,院内树木无一青翠,黄叶纵横。其时秋风横吹,偶有黄叶被刮出院来,自我脚边飒飒滑过。
无人。我独自站在黄叶村前,久久不能移动。
《红楼梦》的大悲剧力量,就在此时准确地、深刻地击中了我,让我在黄叶村的门檐下,进入了一种天高地阔的大悲凉中,以至于当我约半个小时后走入曹雪芹纪念馆的展室时,面对林林总总有关曹雪芹、《红楼梦》的资料,心中再也难以出现比此时更强烈的冲动。
在曹雪芹纪念馆那几间普普通通的平房外,小院中,黄叶被秋风吹着,从我脚面上慢慢地、簌簌地滚动过去。满墙的挂藤,也都落了,瘦瘦地交错在衰败的墙上。远远有歌的旋律传来:“真的好想你……”突然有泪急涌,我伏在极灰旧的木板房门上,泪水渐渐浸湿衣袖。
再也无人打扰我落泪,再也无人看我落泪。低矮陈旧的平房展厅内,曹雪芹的画像一片模糊。时光已过去几百年了,寂寞的曹雪芹在寂寞的光线下,寂寞地看我寂寞地落泪。只微微听到秋风吹过院前高树的声音,以及落叶擦过院墙的声音。(也许,此时的香山正是人流如织。茂盛的游客正在如锦如霞的香山红叶中兴高采烈。)
谢草池边晓露香,怀人不见泪成行。
北风图冷魂难返,白雪歌残梦正长。
琴裹坏囊声漠漠,剑横破匣影茫茫。
多情再问藏传地,翠叠空山晚照凉。
四个小小的、矮矮的、暗暗的展厅,不多;四个萧条的院子,极小。慢慢走过去,也用不了太多时间。从侧门离开,回头,突然有返回重走一遍的冲动。一片黄叶落到我眼镜上。叶柄被镜架别住,伸手取下,看看,心中的冲动慢慢平息,就回过头来,慢慢再在黄叶村中独行。
独行的感觉彻骨铭心,因为这儿是黄叶村,因为在几百年前,我的那位号雪芹居士的好兄弟,他也曾在这里独行过。那时的天那时的山那时的树木那时的风,不知与今日可有不同?
村北闪出一处篱笆小院,院内隐隐有一匾额:黄叶村酒家。心中热起来:雪芹好兄弟,我来陪你喝酒。
正是中午时分。酒家有一个老板和两个服务员,没有顾客,这正合了我的心意。看着菜谱,要价都比较高,老板解释说这儿的房租很高。我没说什么,点了两个最便宜的菜:麻婆豆腐,炸花生米。要了一瓶二锅头,就一个人到院子里去,坐在石凳上,等他们上菜。
一会儿服务员端着菜提着酒过来,关切地说外面有点冷,到屋里喝吧。我摇摇头,要一瓶开水,与白酒掺在茶杯里喝。二锅头质量很差,与白开水兑在一起,喝起来更不舒服。一茶杯下肚后,诗情画意都远远去了,就想这酒是不是假的,曹雪芹当年不知可曾喝到过假酒?
然而雪芹不见,无人应答。
慢慢地酒意上来,身上不热,更冷。黄叶村酒家的篱笆墙外,是一湾池塘,池水寒碧,偶尔有落叶吹入,有微微的漪纹。池边是几株垂柳,萧索地垂着长条,很苍茫、很古老的样子。
曹雪芹也只是一个很苍茫、很古老的梦罢!
掖一掖衣襟,还是冷,石桌上的菜也渐渐凉了。看看空寂的黄叶村,依然只有黄叶在寂寞地翻卷。酒还剩半杯,却怎么也喝不下去。曾经与我非常遥远的《红楼梦》,在之前半个上午的时光里,与我居然会如此逼近。而此际,与我曾经如此接近的《红楼梦》,又隔的那么遥远,遥不可及,遥不可思。
我回头:“服务员,算账。”
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