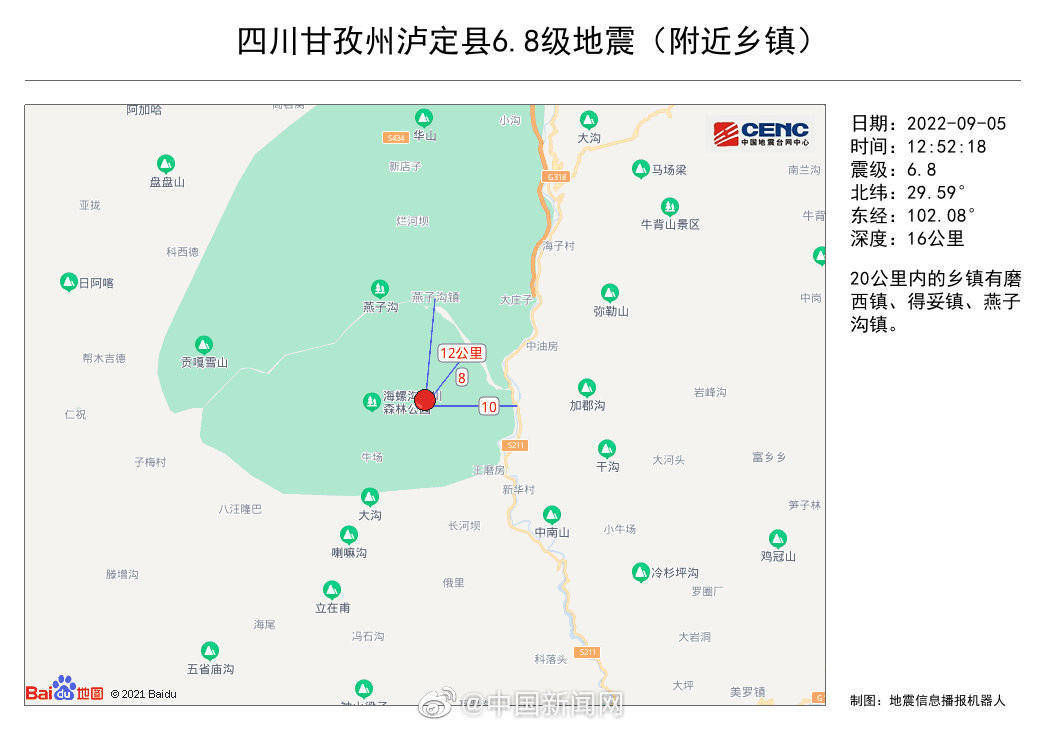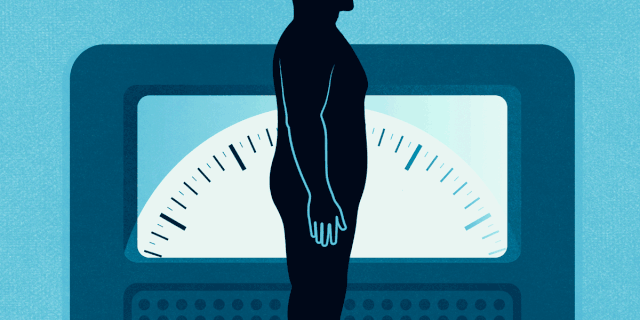今年特别热,老邓邀我去消暑。
我住在老邓非常有特色的民宿院子里,老邓忙完手里的活,来院子里陪我说话。
月光下,黛黑起伏的山峦上,明月静谧,天空清朗,整个夜就是偌大的一幅水墨。我们闲聊着,夜就深了,老邓没有睡意,还在对我说:“我就想用我这双手,将山里这些水竹,都划成篾片。”
我知道,老邓是要用这些篾片来编织山里的每一段光阴,每一处景致——它们或许是大雪封山时房屋上升起的炊烟;开春后叮咚的溪流和满山的新芽野花;入夏后被鸟叫得空灵的山;秋天夜里被山风吹净的明月……总之,这山里的一切,他都要把它们编进他的竹席里,让买他竹席的人看一眼就稀奇上这里。
老邓与我是20世纪90年代末在滚子坪山里认识的。
滚子坪在娄山山脉的末端,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很多年前这里是非常贫困的地方。这些年通过人们不懈的努力,滚子坪被打造成了重庆市江津区塘河镇的一处避暑胜地。
认识老邓,是因为我到滚子坪工作。
那年夏天,我把从家里带来的竹席拿出来铺到床上以备消暑用,却发现竹席已经破旧,需要换新竹席了。山里人告诉我,在山里,编竹席手艺过硬的,唯老邓。老邓身材矮小,黧黑,岁数并不大,只因相貌显得老成,因此山里人叫他老邓。
我向老邓买竹席的时候,老邓对我说:“我这里只卖水竹席,其他竹席没有。”我对竹席并没什么概念,只要是竹子编的竹席,我都认可。但听了老邓的话,我有些好奇:“还有别的竹子编的席子?”老邓并不搭我的话,自顾自地编织手里的竹席。
我有些尴尬,想找话说,见老邓并没有搭理我的意思,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开口。
好半天,老邓好像突然想起我是来买竹席的,才又抬头问我:“你买不买?”我赶紧搭话,说:“买。”他继续问我:“好宽好长?”
我一时不知道他问的宽长是指的什么,就没有回答。见我不回答,他就又不说话了,继续编他的席子。见老邓不再理我,我莫名有些不快,转身走了。
回去的路上,碰到叫我去老邓家买竹席的山民,他见我空手而回,忙问道:“怎么没买?是瞧不上他编的席子么?”
我把在老邓那里的遭遇说了。他一听,居然脸上堆起了笑意,仿佛路边怒开的野山茶。他一边笑,一边对我说:“这个老邓,老毛病又犯了。他生性腼腆,生人面前是不多话的。走,我陪你去买。”受不住他的热情,我与他重新踏上了买竹席的路。
路上,他告诉我,这山里的人家都穷,但老邓更穷。他早到结婚的年纪了,因为穷,所以还单身着。老邓在家排行老四,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前些年两个哥哥激烈要求分家,就把老邓分出来了。老邓吃身材矮小的亏,对打理庄稼的事,很是吃力。幸亏他以前跟了个师傅,学了编竹席的活,才凭着这点小手艺艰难地养活着自己。山里人知道他的状况,皆帮衬他,有买席子的,都介绍给他。
我很好奇:“为什么老邓说只卖水竹席?”他说:“用来编席子的竹子有很多,有慈竹、风竹、斑竹等。但是这些竹子的韧性都差,用它们编的竹席,不吸汗不耐用,没几年就坏了。水竹席就不一样,不但韧性好而且更吸汗,就是用篾刀把篾片划得比纸薄,它也耐用得很。一床好的水竹席,可以传几代人呢。”
为了印证说的是事实,他接着说:“我床上铺的那床席子,就是水竹编的。那是我曾祖留下来的,油浸浸的色,一看就是老古董。夏天铺在床上,人粘着就津津的凉,酷暑给人的燥,躺进竹席里就没了。”
他说完顺手一指路边的竹子说:“这水竹贱得很,有土的地方它就能活。砍了生,生了砍,砍不绝。用做柴烧都嫌它不熬灶,但打竹席却是最好的东西。”
我在老邓那里买了一床水竹席,果然睡起凉爽得很。后来,我也经常介绍人去买,和老邓就慢慢熟络了。再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离开了滚子坪。这一去就是很多年。
再上滚子坪的时候,当年介绍我买老邓竹席的那个人已经是山里脱贫攻坚小组的成员。我在他开的农家乐里小住,问起老邓的时候,他说:“晚上我叫老邓过来陪你喝几杯。”
我还没有回答,他就继续说:“这些年的政策好,老邓已经是这山里的能人了。我们村组织就近会编竹席的、日子过得艰难的山民组成了一个竹器社,由老邓任社长。山民编的竹席由老邓把关质量,镇上负责给他们宣传找销路。他们现在手工编织的竹席,俏得很。”
末了,他还很兴奋地说:“老邓这些年好运也来得快得很,他在网上教了一个女徒弟,教着教着,人家被他的手艺折服了,把自己嫁给了他,现在孩子都两岁了。”
再后来,大约在两年前,我得知老邓建起了特色民宿。他推倒了原有的破旧的土房,用山里的竹木修建了别具一格的民宿院落。
民宿里的墙面是用各式各色的竹席装饰而成,屋顶则是用编竹席用不上的竹黄吊的顶。民宿里的家具一应皆是竹子制作的,甚至连客人用的餐具,皆是他用竹子编的。最神奇的是他用竹编的汤盆,居然不会渗出一丁点儿汤水。
夜很深了,我躺在老邓铺着竹席的床上,屋外的山风把月光从窗口吹进了我的房间,在微风里散散碎碎的。我枕着竹枕,躺着竹席,津津凉凉的感觉让人心特别的安宁。
想着刚才我和老邓在院子里的絮絮叨叨,我明白,这就是我们普通人的日子,也是我们静好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