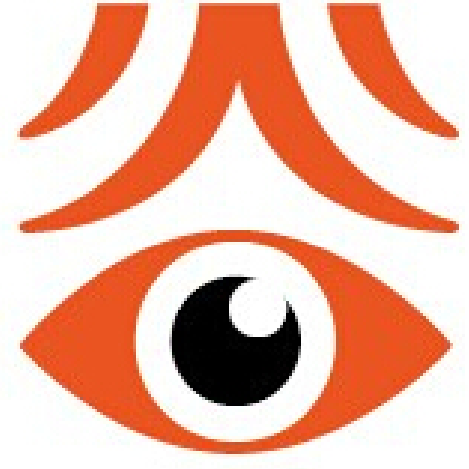人是旅行的动物。“旅行文学”在给我们讲故事的同时,也让读者在诗与远方的召唤下,去追寻更多可能的世界。
这个夏日,红星文化邀请莫言、阿来、迟子建、李娟、罗伟章、龚学敏、胡成等作家,用他们笔下的文学,经由途经的地理,构成我们的一次读行。
在这场意犹未尽的夏日读行之旅将尽之时,我们特邀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西湖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德明先生,一同探讨“当代旅行文学”。
旅行和文学,是一对天然的孪生子。我们很难相信一个足不出户的人能讲出什么故事,也很难相信一个走南闯北的人说不出点儿奇闻逸事,哪怕他人再笨,口再拙。其实许多情况下,我们是先读书,再上路的。先知道有孔乙己,再去绍兴咸亨酒店喝酒,吃茴香豆。先读了莫言,才来到秋天的山东,去高密看满村的红高粱。硬件必须配合软件,空间必须注入历史,通过文学的讲述,才能成为人类活动的镜像,吸引游客前来膜拜、怀旧和消费。纯粹的自然风光固然也吸引人,但缺乏本雅明所说的那种经历史打磨后的“光晕”。
我曾在不同的时间点,分别在美加两国观赏过尼亚加拉大瀑布,但当时只有激动,没有感动,更没有写诗的冲动。因为再壮美的风景,缺乏人类活动的痕迹,只是一堆光影和色彩的颤动。相机能记录的,只是瞬间的物理之光,而缺乏人的目光和思想的穿透力。黑格尔说过,人之所以为人,一定要在自然中打下自己的烙印,看到自己“精神的对象化”,心理才会满足。而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做到的,正是这一点。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字面意义上的“阅”历和“履”历同样重要,同样值得珍视。
2016年,53岁的北大历史学家罗新,一位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的专家,做了一件他惦记了15年的事——从大都走到上都。他自北京健德门启程,沿着古代辇路北行,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用了15天的时间,一步一步用脚丈量了450公里的河山,抵达上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归来后用一年时间写成并出版了《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全书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虽会比较累,但读完后的愉悦感是实在的,收获是良多的。书中既有细密的考据,旁征博引的趣闻,又有途中生动的观感和对当下的反思,使我想起了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那本著名的南美游记《忧郁的热带》。
另一位旅行作家刘子超,在2020年,前往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归来后写出一本22万字的游记《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很快收获学界的一片赞叹。许知远称他是“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游记作家”,罗新则评价这本书“为今后的旅行写作树立起标杆”。
旅行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充电器”和“安全阀”,其功能之一便是帮助都市居民舒缓日益加剧的生存焦虑,治愈因疏离感和孤独感带来的精神抑郁。
在当代中国文学家/诗人中,我发现了一位将自己的旅行生活“完全诗化”的诗人——黄怒波(骆英)。这位集企业家、登山家和诗人三种身份于一身的作家,在2011年出版了一部诗集《7+2,登山日记》。在这部作品中,他以诗的方式逐日记录了他6年间登上世界七大峰和南北两个极点期间所经历的情感和思绪。诗人抛弃纷纭的俗虑,摆脱了各种眩目的社会角色,毫不避讳地记下自己在面临生与死的抉择、滑下冰峰或跌入深渊的考验时,所经历的恐惧与战栗,放弃与坚持,也忠实地记录了跋涉的痛苦与疲累,登顶的兴奋和欣喜,下山的感悟与思考等。诗人将每一个登山的日子都变成了诗,将极端的生存体验“完全诗化”了。
宫崎骏说,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酷暑即将到头,秋光将更灿烂,让我们读起,走起,来一场从文本、身体到心灵的漫游,让自己的生命变得前所未有的充实,丰满和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