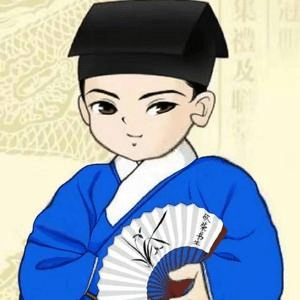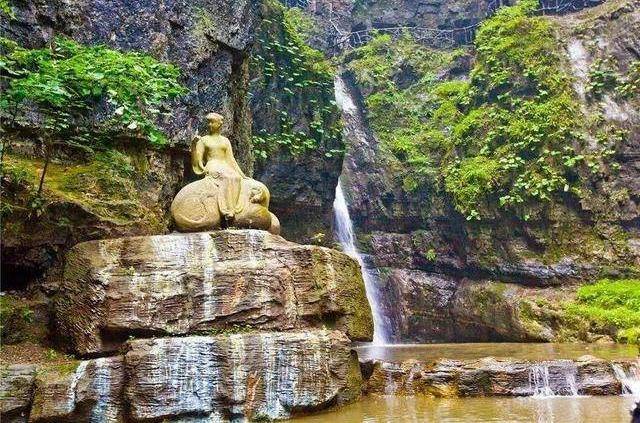热情洋溢的西班牙人很善于交谈,也十分乐意将时间挥洒在广场上无穷无尽的话题和美食美酒上。但对我们而言,和他们的沟通只能完全依赖智商。在小城镇里,无论是住店、问路还是点餐,大多数当地人都不说英文,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愿意表示友好。若是听懂了你的意思,他们便开始叽里呱啦噼里啪啦地说上一大串西语,语速快得像机关枪迸出一整梭子的子弹,或者再配上点儿手势表情什么的,似乎觉得你总应该能听明白点儿什么。
葡萄牙人中会说英文的人数就多了许多,尤其是年轻人。后来在塞维利亚和房东聊天时,谈到语言这事儿。他说“:我的英文也很差,但我想学。我身边的很多人,就像带你去的那家小食店里年轻小伙,他真的一句都不会说,连一到十,都不会说。”可是葡萄牙的年轻人为什么大都会说英语呢?房东说或许是西班牙人看电影都是配音的译制片,而葡萄牙则是看原文的。看来虽然全球都受英美文化的影响和同化,但西班牙在语言上,却是和法国一样大执着和小任性的。
西班牙语的发音听着就觉得热情夸张,带劲儿。葡萄牙语则似乎稍委婉细腻一些,或许只是我单从听觉上的直感,也很可能是从法朵(Fado)和弗拉明戈(Flamenco)之间感受到的不同影响了我的判断。语言的尽头,音乐响起。音乐是代替语言最好的、最诗意的方式。某种程度上,一个民族的音乐表达方式和他们习惯的语言表达方式是一致的。法朵与弗拉明戈分别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音乐之魂。弗拉明戈一词原意是逃亡的农民,法朵是命运悲歌的意思。
法朵里的Saudade和弗拉明戈里的Duende都是指歌者最深沉的灵魂,这是音乐里怀旧的,唤起某种情思的能量与精髓。同样是多民族复杂融合的起源,同样旨在表达流浪的悲情,同样是诗性的气质,但两种音乐在形式和味道上,以及民间艺术家们赋予的创造性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西班牙是个民谣和民间音乐最丰饶的国家,雅俗不分,所以才会诞生弗拉明戈这种糅合了弹、唱、跳的综合形式,吉普赛人和摩尔人的加入,是西班牙诗歌至关重要的元素,而这些诗歌便成了歌词,歌者用更接近阿拉伯人吟诵的唱腔,像血液在胸膛里奔腾一般唱出这一首首深歌,如同古老的叙事曲。吉他明亮而有力,配合着唱和舞步展开丰富的节奏变化,时而哀鸣,时而热烈,时而带着挑衅和欲望,时而孤独绝望。吉普赛男人女人们脚下踏出的舞步,双手的击掌、弹指声,每一个发出的动静,每一个瞬间都是靠着一股内在的浓郁的“气息”连贯而迸发出来的,仿佛我们呼吸的空气都要被他们凝结住了。
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在塞维利亚的小舞台上观看弗拉明戈,差点被感动得流出泪来,视觉与听觉的冲击下,我感觉到除了那些伟大的建筑和发明之外,这也是人类作为流浪者的后裔,通过一代代鲜活生命的繁衍和融合,集体创造与传承出的结晶,它是我们真正存在过的证据。如果弗拉明戈的标志是女人的扇子、服饰,那么法朵最具特点的标志则是葡萄牙的吉他,长得像鲁特琴的十二弦吉他。法朵通常只有吉他伴奏和演唱,它旋律性更强,优美,悲而不伤,甚至在不断地演变中加入其他乐器,比如手风琴,小提琴等等乐器伴奏,也更多了一丝现代元素和小情调。
这两个国度里,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流浪艺人,他们只要一个好天气,一把乐器,就可以开始他们新的生活。行动缓慢的老人、外表邋遢的嬉皮士、朝气蓬勃的乐队、一人多能的唱作者、售卖自己CD的人,和那些带着狗狗出来练琴的人们,各自在自己的角落里等待着人群的驻足和硬币的降临,无论上帝赏赐他们的是音乐本身,还是技巧与才华,还是今天的硬币换来的一杯咖啡或一顿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