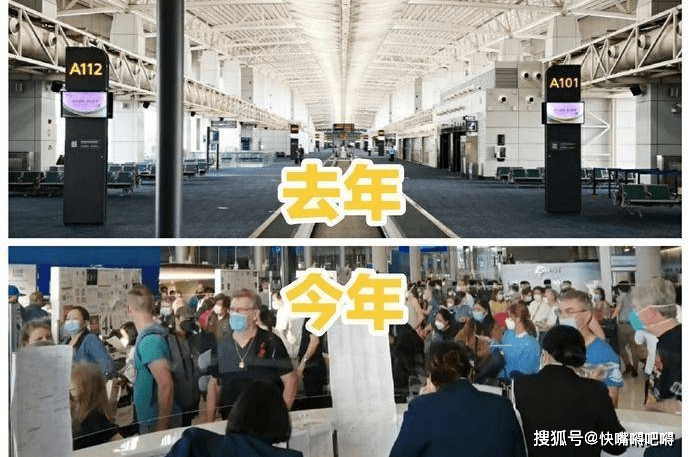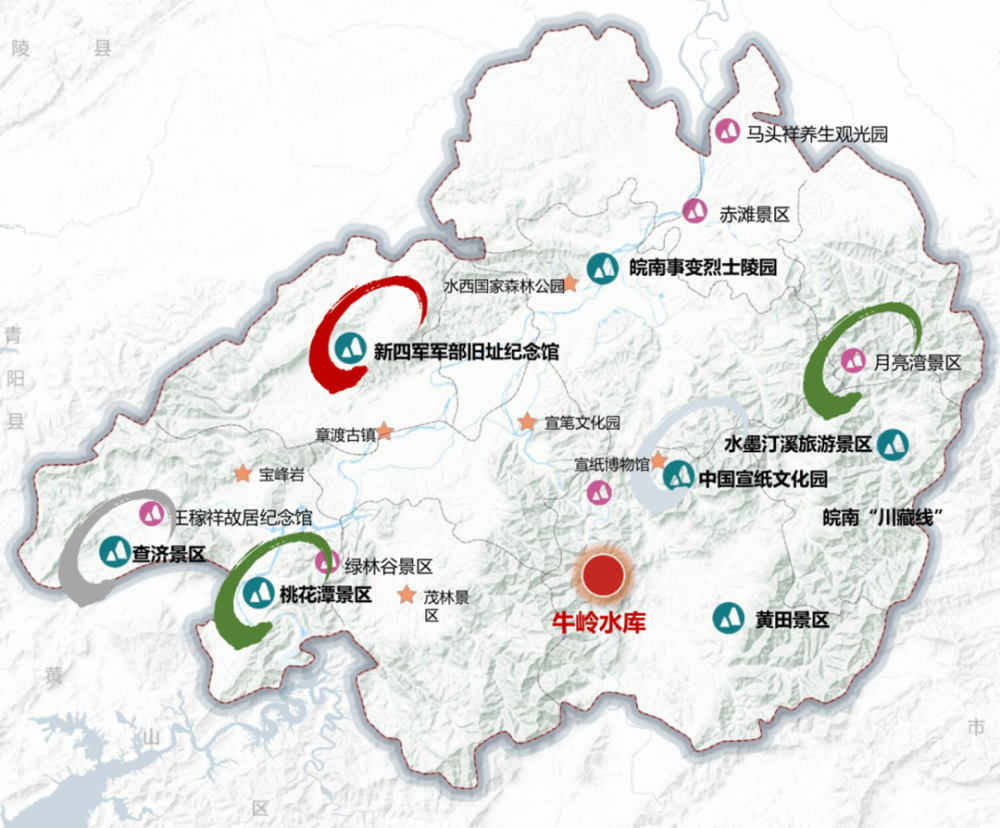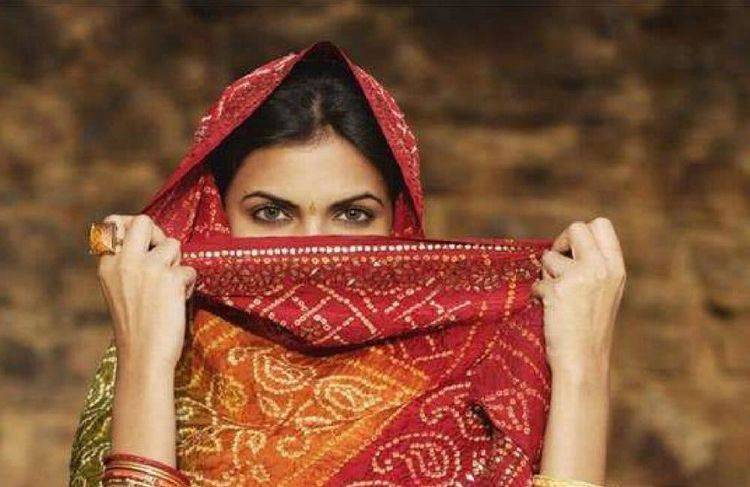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18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拟建立拐卖妇女等侵权行为强制报告排查制度。
草案二审稿进一步突出对妇女人身权、人格权的保护;拟建立拐卖妇女等侵权行为强制报告排查制度,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乡镇人民政府等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妇女疑似被拐卖、绑架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处理;要求学校建立入职查询制度,预防学校发生对未成年女性的性骚扰、性侵害;保障孕产期女职工合法权益,禁止因婚育等原因限制女职工晋职。(完)
【相关报道】
北师大教授王志祥谈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应延长追诉时效,减少无罪化处理(红星新闻)
4月6日晚,陕西榆林发布关于佳县“小雨”事件调查结果。据榆林市联合调查组表示,经调查,网络上出现的陕西佳县“小雨”的有关贴文,其户籍登记名为陶某侠,患有精神疾病。在第二次走丢后,于2010年9月被吴某娃与吴某霞带回自己家中,随后以8000元价格出卖给李某民。2022年3月10日,公安机关对吴某娃、吴某霞等涉嫌拐卖妇女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侦办中。李某民涉嫌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已过追诉时效。
拐卖妇女这一话题再度受到关注。除了对是否应变更拐卖妇女儿童罪罪名、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的刑罚,一直争议不断,红星新闻记者还注意到,在司法实践中,少有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方被追究法定责任。为此,红星新闻记者专访北京师范大学外国刑法与比较刑法研究所所长王志祥,解读拐卖妇女儿童罪名设定的初衷与变革,以及这背后不可忽视的社会背景。
对收买方未追究法定责任的情况,王志祥表示,涉及到追诉时效的问题,因为法律对3年有期徒刑的最高追诉期只有5年。“在司法实践当中,一旦收买儿童后,往往好多人收买了一二十年,甚至已经抚养成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志祥认为,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是有必要的,“这样一来便可以延长追诉时效,强化对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追究力度,减少无罪化处理的现象。”
▲王志祥
1
立法演变
从拐卖人口罪到拐卖妇女儿童罪
红星新闻:拐卖妇女儿童罪发端于拐卖人口罪,最初出台拐卖人口罪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的呢?
王志祥:1979年制定的《刑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而是规定了拐卖人口罪。1979年《刑法》第141条规定:“拐卖人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从我们国家情况来看,拐卖人口罪是在1979年刑法当中建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对人口流动的管控比较严格,再加上经济的发展水平有限,所以拐卖人口犯罪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就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人口流动的频繁,拐卖人口犯罪相对而言就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红星新闻:1983年,将拐卖人口罪最高法定刑提高到死刑,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志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犯罪总量处在一个增长的状态。所以在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决定当中就对包括拐卖人口罪在内的7类犯罪,把法定最高刑上升为死刑。很明显立法意图是为了强化对这7类犯罪的严厉打击。应该来说在短期内还是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拐卖人口犯罪在总量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红星新闻: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犯罪分子的决定》增设拐卖妇女儿童罪。刑法中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拐卖人口罪并存的局面开始形成。这在司法实践中有什么变化?
王志祥:这个立法是考虑到在司法实践当中,就拐卖人口犯罪而言,拐卖的主要对象是妇女儿童,为了强调对拐卖妇女儿童行为的打击,所以说通过单行刑法这个方式,向拐卖妇女儿童行为予以犯罪化,确实形成了拐卖人口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并存的一个格局,导致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拐卖妇女儿童行为,要按照单行刑法的规定,认定为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对于拐卖妇女儿童以外的其他人口行为,就要认定为拐卖人口罪。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刑法当中的拐卖人口罪起到了一个堵漏的作用。
▲图据视觉中国
2
立法漏洞
遗漏对已满14周岁男性人格尊严的保护
红星新闻:在1997年《刑法》中将已满14周岁的男子排除在拐卖犯罪的对象范围之外,已满14周岁男子的人格尊严和妇女儿童的人格尊严是不可同等对待吗?
王志祥:1997年《刑法》在设立拐卖犯罪时,实际上采取了简单一致的做法,具体来说就是把刚才我所提到的《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决定》当中,所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移植到了1997年《刑法》中,这样一来实际上就遗漏了对于妇女儿童以外的已满14周岁男性人格尊严的保护。
但是从刑法理论这个角度来看,人格尊严为所有人口都共同所享有。所以1997年《刑法》在设立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同时,将拐卖已满14周岁男子这个行为予以非犯罪化处理,这个在道理上显然是说不通的,这实际上属于一种立法上的漏洞。比如山西的黑砖窑案件,他们拐卖智障男子到黑砖窑里去做苦力,就只能按照强迫劳动罪来对这样的行为加以惩治。
红星新闻:在你的专著中建议将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表述调整为贩卖妇女儿童罪,为何提倡用“贩卖”而不是“拐卖”?
王志祥:在这里实际上就涉及到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这六种行为方式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如果说把这个罪名表述为拐卖妇女儿童罪,一方面就容易让人引起一个误解,认为在司法实践当中,只有先拐后卖才可以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然而在大量的案件当中,根本不存在“拐”这个行为。譬如说父母出卖亲生子女的行为。另外一点,可能会让人们误认为拐卖妇女儿童罪成立,应该是以违背妇女儿童的意志作为前提的,但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妇女儿童即便是自愿同意被卖,也不影响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成立。
在这里就涉及到拐卖妇女儿童罪究竟保护的是什么,好多人说保护的是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但是人身自由是可以承诺出让的,一旦从人身自由角度来认识这个罪会非常麻烦。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其实就是不把人当成人,把人给物化,把人给商品化了,它构成了对人的尊严的侵犯,应该提高到这样的高度来加以认识。
▲“严打拐卖妇女儿童,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大屏公益广告。图据视觉中国
3
立法特点
收买行为大多过了追诉时效而无法定罪
红星新闻: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你在专著中提到,这项罪名呈现出轻刑化的制刑政策,立法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志祥:对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而言,采取轻刑化的刑事政策总体上与该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相吻合的。尽管买和卖一般而言是相互对应的,但从拐卖犯罪产生的诱因来看,拐卖行为的发生和收买行为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关系,拐卖类犯罪预防和惩治的重点仍应放在消除犯罪原因即打击拐卖犯罪分子上,而且,与出卖行为的多样性相比,收买行为从形式上要单纯得多。这些均决定了收买行为的刑罚配置不可能与出卖行为等量齐观,对之只能处以相对较为轻缓的刑罚。
红星新闻:近年来很多寻亲家庭都找到了孩子,但在司法实践中,少有收买被拐卖儿童的家庭被追究法定责任,这是为什么呢?
王志祥:这涉及到追诉时效的问题,因为法律对3年有期徒刑的最高追诉期只有5年,在司法实践当中,一旦收买儿童后,往往是收买了一二十年,甚至已经抚养成人,已经没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也是有必要的,因为一旦过了5年后,国家在原则上就没有追诉权了。
如果说适当的提高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法定刑,譬如说把法定最高刑的3年有期徒刑提高到7年甚至10年有期徒刑,这样就可以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追诉时效,从5年上升到10年甚至15年,这样一来大大强化对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追究力度,减少司法实践当中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行为无罪化处理的现象。
红星新闻:在你的研究中,被拐卖妇女自愿留下来和收买人继续维系家庭关系的比例高吗?
王志祥:这个比例不算很低,尤其是当妇女已经在当地结婚并有了孩子,她想要脱离被收买家庭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她甚至自己也会认同被收买这个行为,这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如果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行为得不到及时打击的话,它往往会制造非常大的一个社会难题。
因此婚姻登记的工作人员可能需要有一定的报告义务,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治理来讲,它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发力。刑法第四百一十六条(规定) ,针对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专门规定了两个渎职性的犯罪,一个是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另外一个就是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当然从司法实践角度来看,这两个罪适用的面比较窄。从立法规定这个角度来看,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它规定得含糊,在司法实践当中,哪些人究竟属于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范围不是特别明确,由此就造成在司法实践当中,在适用两个条文的时候操作起来难度比较大的一个现象。
▲图据视觉中国
4
法定刑之争
“买卖同罪”在刑法中很难实现
红星新闻:前段时间有许多的法律专家和人大代表,都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量刑问题进行了探讨,你注意到了哪些观点?
王志祥:罗翔教授提出了“买卖同罚”,我认为在刑法中是很难实现的,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所发生的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发生的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处于剥削的目的,比如说买卖为奴或者说买卖强暴,但是中国刑法当中所规定的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从司法实践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都是为了建立家庭为目的,与被拐卖的妇女建立婚姻关系,与被拐卖的儿童建立子女关系。两者的危害性还是应该予以区别对待,两者的法定刑不可能保持在一个水平上,否则的话实践上无法突出打击的重点。
此外,罗翔教授将此罪与非法收购野生动物相比的说法,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当然有些人也指出来,把个人和动物简单地进行对比恐怕也不是特别合适,对人和动物立法出发点还是存在较大不同,但是罗翔教授这个观点也不得不让我们正视一个问题,中国刑法规定本身会导致人们得出一个结论,人不如动物,我觉得这个现象确实值得引起重视。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法定刑应该予以维持,认为收买妇女儿童的行为,发生之后接续会发生一些重罪的行为。比如说非法拘禁行为、强奸行为等等,像强奸这样的犯罪,一个妇女被收买以后,她所发生这个性行为怎么可能是自愿,但是这仅仅是观念上的一种推定,司法实践当中认定构成强奸罪,还需要证据来加以支撑,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一般来说都是单独定罪。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有必要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法定刑,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后续重罪发生的可能性。
红星新闻:你认为拐卖妇女儿童罪在立法上还有哪些地方有待完善的吗?
王志祥:我认为从立法角度来看,可以总结为一升一降。具体来说就是对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应法定刑升高至6、7年,甚至10年。这是考虑到其本身有一定正当性,也就是说适婚人口这一块,男女性别差别比例太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甚至认为越南新娘、缅甸新娘是没什么问题的。实际上这一犯罪问题背后,带有非常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原因,不能只让犯罪人本人来承担。
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认为对于拐卖妇女儿童这个行为,法定最低刑规定为5年有期徒刑较高,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亲生父母贩卖亲生子女的行为,这种行为往往事出有因,譬如说生活过不下去了,无法把子女给养活,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就提到,这类情形或许就应该在刑法当中规定5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法定刑幅度,从而对这类行为予以恰当的刑法评价。(中新网北京4月18日电 / 记者 梁晓辉 黄钰钦)
来源: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