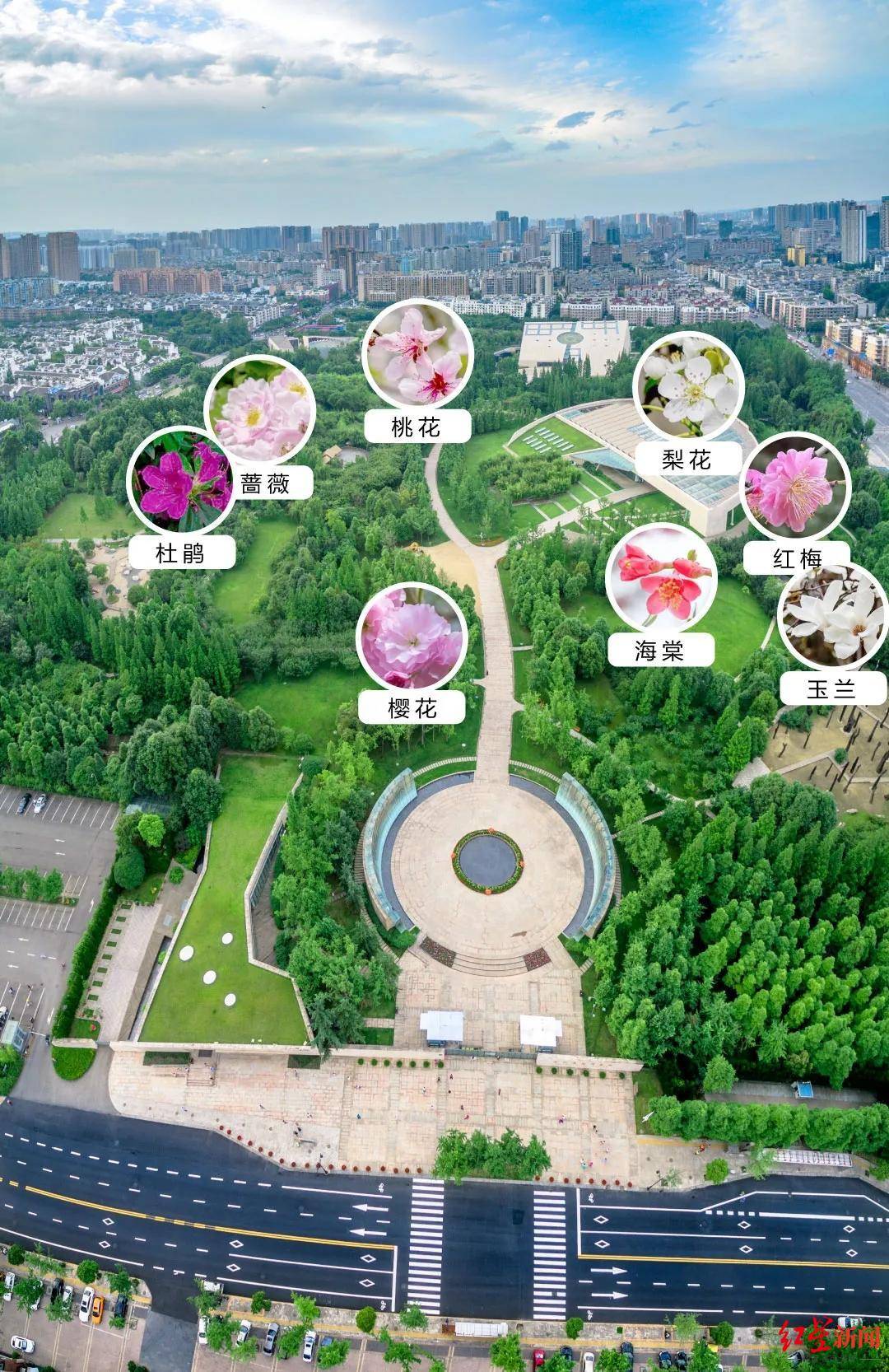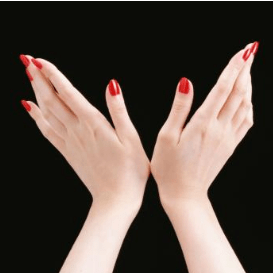仇日风气的蔓延,让人开始丧失同理心,“小”字作为前缀的形容,自以为是的雪耻前辱,电视台一遍又一遍播放着红歌,正义与邪恶势不两立,正义与邪恶也清浊分明。
日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去过日本的朋友说,那里温泉多,而且便宜,就是新干线太贵了。文章里看到令人惊讶的事实,原来富士山是私人所拥有的,这么一座有名的大山,这样一个地标性的景点,居然属于个人?
接触过几个日本人,说朋友也算不上,但模棱两可之外的印象,是事实印象。

第一个是在越南会安遇到,是个日本男生,胡子拉碴的,我以为他是四十好几的大叔,没想到人家说他才20来岁。
当时大家在讨论自己的旅行故事,他去过多少地方我已经忘了,只隐约记得那些国家的名字从我熟悉的到不熟悉的,后面更是像听天书一样听他在列数。
那是我旅行的第一年,在会安古城从下午绕到晚上,才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青年旅舍,没想人家还不承认我的YHA卡。

一年四季都是热带的会安,不出一会儿就能大汗淋漓。我在古镇的街上沿着河两边走,路过一个拐角时看到有家小店,两姐妹搬着小板凳坐在门口,笑着嗑着瓜子。
那个时候我问自己,走那么远出来旅行,到底为了什么?
也因此,面对旅行经验的背包客前辈,我只是打量他如今的憔悴,不明白为何一个人能走这么远,不明白他出行的前因到底何在。
不过,那都与己无关,所以,我听,他讲,我听过就行,也不在意是否能记住,因为萍水相逢,本就不在意料之中。
旅行多的是这样的故事。

在那之后,我在蓝毗尼又遇到一个日本的女孩,其实在国外,要分辨你是哪一国人,大多数靠猜。比较常见的黄皮肤人有韩国人、日本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当然中国人也是,只不过这一个往往被放到最后猜。
我与那个女孩住在同一间房,那是二楼的最后一间房,却靠着楼下火热的凤凰树,门口有什么人经过也看得一清二楚,就连对面师傅们的房间也能看到,明黄色的僧袍晾晒在走廊,有时候眼神碰撞,对面的师傅会哈哈笑挥手打个招呼,一点也不避讳。

那是韩国寺的二楼,最后一间房。房间里的来客,去了又来,来了又去,所以当我又一次从外面回来时,看到房间里多了一个陌生人,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就连看到她是黄皮肤,也失去了打招呼的热情。韩国寺嘛,来的黄皮肤能不多嘛?
但是人与人的气质是不一样的,可能国家与国家的气质也不同。打招呼时,她自报家门,说从日本来,是环球旅行者,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中国的。简单的寒暄,有礼有节,也点到即止。
那时候我想要静静,每天附庸风雅在房间里练用水写的毛笔字,有时候点开空白word文档,吭哧吭哧了好半天,最后全删掉,索性去外面凉快,一个板正躺在了门口木椅上,闭着眼大白天装睡。
脚步声和细索的声音总是会入耳,眼睛闭上了,听力便特别敏感。我从声音里分辨对方在干嘛,完全靠猜,竟也对了大半。有时候她跟我说话,我不想答就随口应付几句,反正都是过客。

房间里有第三个人时,就有了欢呼和惊羡。我没有参与对话,却站在她们旁边,看上去好像也是融入的一个。
日本女孩说:她出来旅行3年多了,30多岁的日本女人,没有选择结婚生子,对她家人来说已经是不孝,但她不想要那样盲从的生活,所以出来旅行,想要看一看更广阔的世界,换一种跟她前半生完全不同的活法。
另一个女孩子说,她这样的活法太酷了。又问,是不是日本女孩子都这么勇敢?我见过好多长途旅行的人都是日本的女孩!

“可能是压抑太久了吧”,这个回答我记忆至今。因为她看上去那样平常,像一汪水一样没有波澜,平静,性格也温吞,不太像藏了心事的人,更不会有激烈的心理,都不如我性格别扭,可她却做出这么多“不同寻常”的选择。
离家,去乡,流浪,远方,四海,漂泊,都是她的故事。
那时我年轻,在我认为30岁还很遥远的年代,在我以为30岁就该定性而不是漂泊流浪的时候,我旁听了故事被触动,却觉得那又与我何关。
旅行路上的旅人太多了。
我是第二次回去蓝毗尼,师傅可能看出我的不对劲,所以要我第二天在楼下等他,我不知道要干嘛,只说好的。看起来乖顺无比,不过不在乎。毕竟,我多的是时间。

第二天约定的时间到达前,我就去楼下等。因为是上午,大门口一直有人进来,许多参观的游客,也有住在寺里的人,走廊里经过的,从外面回来的,有些我有印象,有些我不认识。
我在那里站得久,渐渐地像个导航,路人过来问我这是哪个寺院,又有人问我殿里可以进去看吗,一波波人走过又路过,一上午竟也忙得不亦乐乎。
有人从我面前走过又回头,看到是我很惊讶,问我怎么在这里。我说师傅让我站这的。她说她刚刚去外面转了一圈,又说了些什么,大多是很细碎的事情,我早就忘掉了,但那一天,我们聊了许久,那是我第一次不觉得聊天是被人打扰,她说,我听着,她问,我也回答。
聊天与聊天是不同的,有时候是为了结束话题,有时候是为了探讨观点,还有的时候东扯西拉,就纯粹打发时间。但那一天,我们的话题与上述所有都无关,就只是看到了,聊了聊,好像他乡遇故知,一个熟悉的人,是会让你我打开心门的。
而在寺院的一楼,我是她熟悉的人。在大门口人来人往标致惹人拍照的凤凰树对面,多的陌生人和游客,因此她也是我熟悉的人。
熟悉这词本身需要时间作介质,便也被时光发酵。

后来,在云南建水古城,我在青旅的大厅坐着,对面过来一个老头,坐在我对面,拿出一个本子划来划去,问我会不会玩这个,我看看上面的日语,这样的填字游戏如果是文字,我一定不会,但要是数字,瞎填也能蒙对啊,至少是有这个可能的。不过没有胜算,我不丢脸,我摇摇头说不会。
老爷爷把本子往我边上靠,一题一题地写,一个空一个空的补上,然后又问我会不会——其实他说的日语,我听不懂,不过这个老爷爷,我见过好几回了。
他孤身一个人来这么偏的小城旅行,那时候建水还没有出名,游客本就不多,我住的青年旅舍偌大床位间,就我一个人。整个旅舍像是聊斋里发生灵异故事的宅院,古色古香也变成阴恻恻让人背冷。

虽然语言要学习,但交流有时候只需心领神会,所以我猜到了他的意思,他把笔给我,诠释了我的猜对。我犹豫了许久,老爷爷在旁边说着什么,手舞足蹈的,我大致明白他是让我随便写。可我不想错,想了半天干脆放弃,一抬头看到老爷爷期待的眼神,瞎填了一个。毕竟我是第二天要走的人。
可我的答案还是错了,老爷爷笑着拿过去,在纸上写写画画,把数字排列到一起,好像是解题的过程,这个时候我已经没耐性,心想我才不管你那什么答案,我根本不想玩。老爷爷蹦出简单的中文词汇,我起了好奇心,问他为什么一个人出来旅游?
我也在纸上涂涂画画,就这样鸡同鸭讲,反正是互相明白了彼此的意思,但那段故事我已忘记。后面的记忆是大段空白,好像不曾发生过。

建水我也去过两回,记忆里心心念念的大碗米线,再次吃到时依然分量很足,我却想不起来这是不是我从前吃过的那一家。
多年前住过的老院子,也已经被翻新重修,我住进了多年前的旅舍,试图找到记忆里的味道。朋友说那附近就这一家老店,你几年前吃过的就是这一家没错了。可我仍然怀疑。
时间把许多东西冲走,找不回记忆里的模样,这是“是”还是“不是”,只能靠一个自圆其说。

在从前以为这个世界与我无关,到后来所有见过我的人都说我爱笑,我一直以为那是面具是盔甲是自我的防备,后来发现水到了温度会开,我不过是与自己和解,也没再有置身事外的冷淡。
世界是整体,阳光空气雨露人人都享得。钱权富贵名利地位能让人趋之若鹜,但抵不住过眼云烟时光如梭。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才是那亘古的写照。
人本就渺小了,说伟大的是自己,说渺小的是天地,为何总要去扯仇恨,当你记住了仇恨,便只剩下仇恨。
历史是真不假,人心诡诈亦有真,但大多数人,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与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家长里短。失去的生命以数字丈量,那不过是一个总结。戛然而止的一生,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