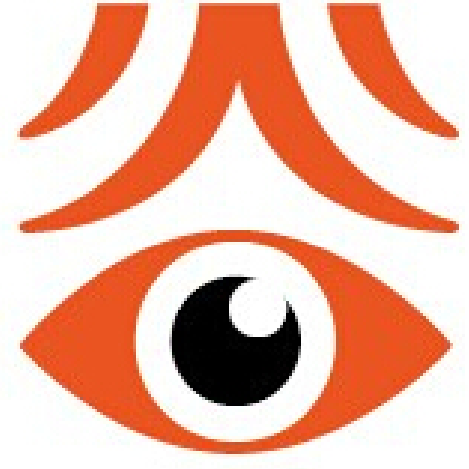骏瑜,自由写作者
由衡水进入北大附中的学生周宇(化名),“在衡水经历过极端的应试教育,在北大附中,又体验了最先锋的素质教育改革”,然而, “我可能做了个错误的决定,我不应该离开衡水,我考不上我原定的大学了。”2021年高考,周宇考了560多分,最终进入一所军校。(详见3月15日“正面连接”相关内容)
追求个性、平等、多元、包容,指向人格塑造而不是应试系统中的高分,是包括北大附中这种“素质化教育改革”中很多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与此同时,衡水作为传统教育的代名词,是维度的另一端,学生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刷题、测试,为了在考试中取得高分,被认为见识狭窄、不自信,被讥为“小镇做题家”。
周宇在两个极端间的切换,让我们看到一种“壁垒森严”的隔绝,而若想尝试突破这种隔绝的后果,可能,比在各自系统中独立运行更为糟糕。
▌不同的起跑线
3月14日,就在这篇文章发布的前一天,因为疫情防控的要求,北京东城、西城两个区通知,凡是周末上过线下课外班的小学生,都不能进入教室上课。
紧接着,网上出现了这么一张令人感慨万千的照片:一间教室里,稀稀拉拉坐了四五个孩子,其他都是空空的桌椅。据传确诊阳性的孩子所在班级,全班学生一周一共上了23个不同的课外班,包括篮球、书法、钢琴、绘画、滑冰、舞蹈、跆拳道……
这是“双减”之后的北京。
而在距北京约480公里的邢台市信都区浆水镇,“孩子们很多都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在市区或大城市打工,日常生活则由祖辈负责。在这种普遍的家庭模式下,由于祖辈精力有限、文化程度较低,孩子们往往回到家写完作业后只剩下两样活动——看电视和睡觉,周末里则会三五一群溜到街上闲逛玩耍(2020-12:《乡村阅读观察:太行山脚下的探索》)。”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一些投生在大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从小疲于奔命上各种课外班,通过重重竞争成为“尖儿”,进入像北大附中、华师大二附中、南京外国语这样的学校,接受人格培养型的素质教育,毕业后很大一部分申请到国外留学(某种程度也可能是不得已,因为这样的素质教育,不一定保证让他们通过传统教育式的高考),再以“海归”的身份回国工作。
而那些出生在村庄、小城镇的孩子,有不少是从小当留守儿童的(或小学随父母进城,在简陋的打工学校念书,小升初时被赶回 “老家”),再经历衡中、毛坦厂中学式的魔鬼训练刷题后进入高考,其中的佼佼者可以考上好的大学,进城工作,“奋斗了二十年,我终于可以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两条路,最终到这里才有了交集。
▌流水线
如果把两种教育模式,比做流水线式的装配——到一定年龄装配一定的零件,那么,在当下高考这种选拔机制面前,北大附中的“素质化教育改革”,相较衡中模式,一定会败下阵来。
衡中式的魔鬼训练,是严守流程的极端,高一需要刷多少题、高二需要刷多少卷子、到了哪个年级学什么课程、读什么书,以及禁止恋爱、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吃饭卡多少时间、入厕卡多少时间……正如对周宇的访谈中提到,已经被机器化,当没有人告知他应该做什么时,是会迷茫的。
而像北大附中、华师二附中这种“素质化教育改革”,也被一些家长“想入非非”了,或被一些留学中介“包装”成了 “出国预备班”线路。比如,小学时,被家长带着在课外班之间转场,到了中学,所谓PBL(Project Based Lesson)同样有它的“套路”,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特质——课程对学生是有预期的,并不见得能“发挥个性”。对要申请国外学校的,很多留学中介有成套的申请学校流程咨询,顾问会告诉他们,8年级时需要参加学生社团活动了,9年级时需要参加公益志愿工作了(以至于接收准留学生,帮他们“刷简历”成为一些小公益机构的生存来源之一),什么时候该考雅思了,什么时候该交申请了……
两条互相独立的“生产线”,其中一条线的“半成品”,若被臆想者换到另一条线上继续“加工”,结果可想而知。
人不是产品。产品不合格,可以报废,但教育的结果是人,无论是在传统教育的激烈竞争中高考失败,还是因为在精英学校接受素质教育后,难以考到原有的高考分数,他的人生,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一切,很多时候都不是学子自己的决定。
▌教育折叠,与其他折叠
科幻作品《北京折叠》获雨果奖时,在整个社会荡起了巨大的冲击波,它将社会中的阶层割裂具象化为空间实体存在,不同阶层的人生活在彼此隔绝的空间,环境、生活条件和方式截然不同、互不沟通。这部作品所反映的人群割裂,三年后,又一次在一部从未被正式引进的韩国电影《寄生虫》里呈现。
1月19日,北京公布的一例疫情流调让很多人惊诧,当事人“18天辗转28地打工”,从深夜到凌晨,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干活,直到行程轨迹被所有人看见。实际上,这是很多底层劳动者的常态。一些营销号,甚至拉出同一时间逛奢侈品商场的流调来对比——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不需要同情,也不应当受到攻击。
社会学上公认的,能够促进阶层流动弥合阶层裂缝的,正是——教育。
然而,当教育也被强烈折叠,各个阶层有自己的教育路径,只有金字塔尖的幸运者才能彼此看见(并彼此鄙视)时,社会又如何融合?
那些被迫回乡留守、考不上高中、只能深夜去建筑工地搬砖的人,那些上了无数课外班却进不了精英学校,或无法出国,必须和“刷题家”一起在高考中竞争并失利的人,那些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不知道应该如何度过这一生、随大流考公寻求“上岸”的人,他们,难道只能在流调中被看见、被短暂地同情、被迅速地遗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