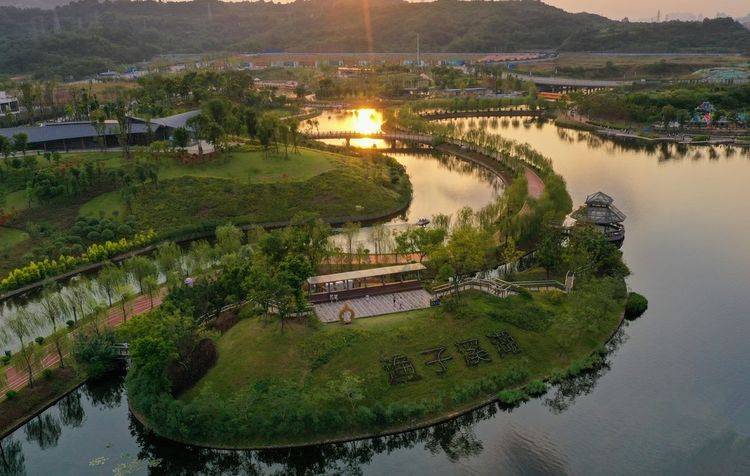美国《大西洋月刊》3月16日文章,原题:为人父母最令人难忘的真相我们真的了解父母吗?孩童时代当然不会。倘若幸运,稍大些我们才开始了解他们。比如,也许我们有些人会意识到,他们背负着我们看不见的重担。最近几年,当我懂得养育孩子最令人抓狂、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事实,才意识到父母肯定一直都知道:让孩子永远安全这件父母最想要的事,是何等之难。
“想把孩子吸回身体”
几年前的一天,我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当时,我在厨房里为自己、丈夫和两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孩子做午饭。孩子们开始长大成人,他们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忙碌,我看到他们的机会越来越少,他们离我的羽翼也越来越远。我为他们感到骄傲,同时也有了一种原始冲动,想把他们整个“吞下去,吸回我的身体”。就在我准备挂电话时,父亲问我是否听说过加勒特·格拉夫的新书——《乌鸦岩地堡》。
我确实听说过一些关于这本书的消息,它讲的是美国从20世纪开始维持了数十年的秘密地堡的真实故事。这些掩体用于核攻击发生时,保护政府高层官员。当他问我是否可以为他订购这本书时,我说,“当然可以,老爸。听起来合你的口味”。“它让我想起我在那里工作的日子。”他回答说。
这让我感到惊讶,他从来没跟我提起过那个秘密地堡。我追问了一些细节。关于工作感受,他说,“起初着迷,然后有点无聊。谢天谢地,我们从来没有派上用场”。我问他,在乌鸦岩地堡工作对他是否有影响。母亲接过电话说:“他时不时会到地堡里去,而我们会坐在家里。我不觉得真的有遭受核攻击的危险——这只是演练。”
我不知道父亲是否曾认为整个演练毫无意义。如果人类已经用核武器毁灭了自己,再也没有安全的世界可以返回,那么躲在人造堡垒里并不比躲在桌子下面更有效。当他们打开地堡时,死亡仍在等待着他们。为原子弹落下做准备并不能预测或影响原子弹是否会落下。都是假装的,只是在瞎忙,不是吗?
一种奇怪的快乐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父亲曾经寄过非常奇怪的爱心包裹。其他孩子收到的是装满自制巧克力糕点的盒子,如果运气好,可能是一副手套或一信封现金。但父亲寄来的包裹里几乎没有现金,而总是装着罐头食品。这是一种奇怪的快乐,也成了室友和我之间的一个玩笑。父亲接下来会送什么?维也纳香肠、菠萝罐头吗?他以为我在学校吃不到食物吗?我和室友可能在进行某种生存储备?每次有包裹寄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咯咯地笑起来。我当时想,真是奇怪,但也是那么的甜蜜。
我现在比父亲在地堡工作时大20岁。儿子去年秋天去上大学了,两年后,女儿也会离开家。我现在意识到,他们的离开不代表我为人父母的结束,至少在我心里是这样的。我永远不会停止牵挂他们。我感觉自己好像穿着一件隐形的爆炸背心在大街上走了几十年。活得越久,我爱得越多,这爆炸背心就越大,我就越敬畏我的好运,同时也意识到它可能在一瞬间爆炸,把我炸到空中,一切灰飞烟灭。有时这种感激和恐惧的结合几乎把我扳倒。我经常觉得老天赐予我的东西比我所能保护的要多得多。当年在大学里打开那些爱心包裹时,我并不理解,现在我理解了。
不能阻止时间流动,怎么办
无论在假想的核攻击中,还是在目前残酷的战争现实中,事实都是:我们救不了任何人。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我们设立的保护措施都将失效。最好的情况是,孩子在我们的监护下健康茁壮地成长,然后离开家独立生活。最糟糕的情况是,我们保护所爱的人的一切努力都将失败,他们被我们无法阻止的东西击倒。那么,如果不能阻止时间流动或阻止每一次损失,我们该怎么办?就像我父母那样,像我现在这样。
我们继续做着日常照护这样普通的事情。我无法永远保护我爱的人,但我今天可以给他们做顿午餐,我可以教孩子开车,带家里人去看医生,修补天花板上开始漏水的裂缝,晚上给每个人盖好被子……直到我干不动了。我可以做一些抚育的小事,代替那些提供长久保护的难事、大事,因为我们可以为彼此提供的最接近持久的庇护就是爱。尽力爱得深沉、博大、形式多样。(作者玛丽·劳拉·菲尔波特,传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