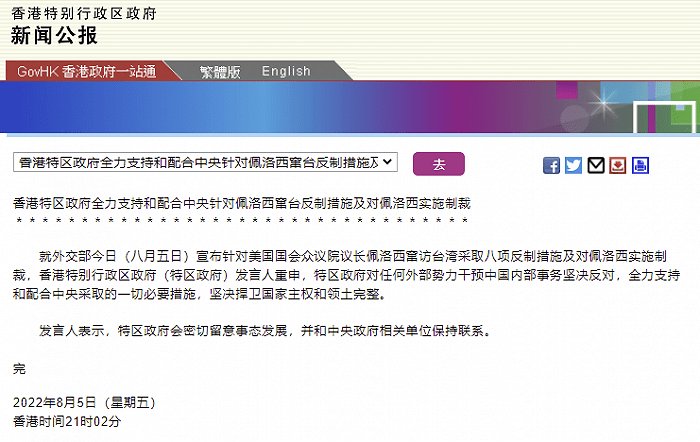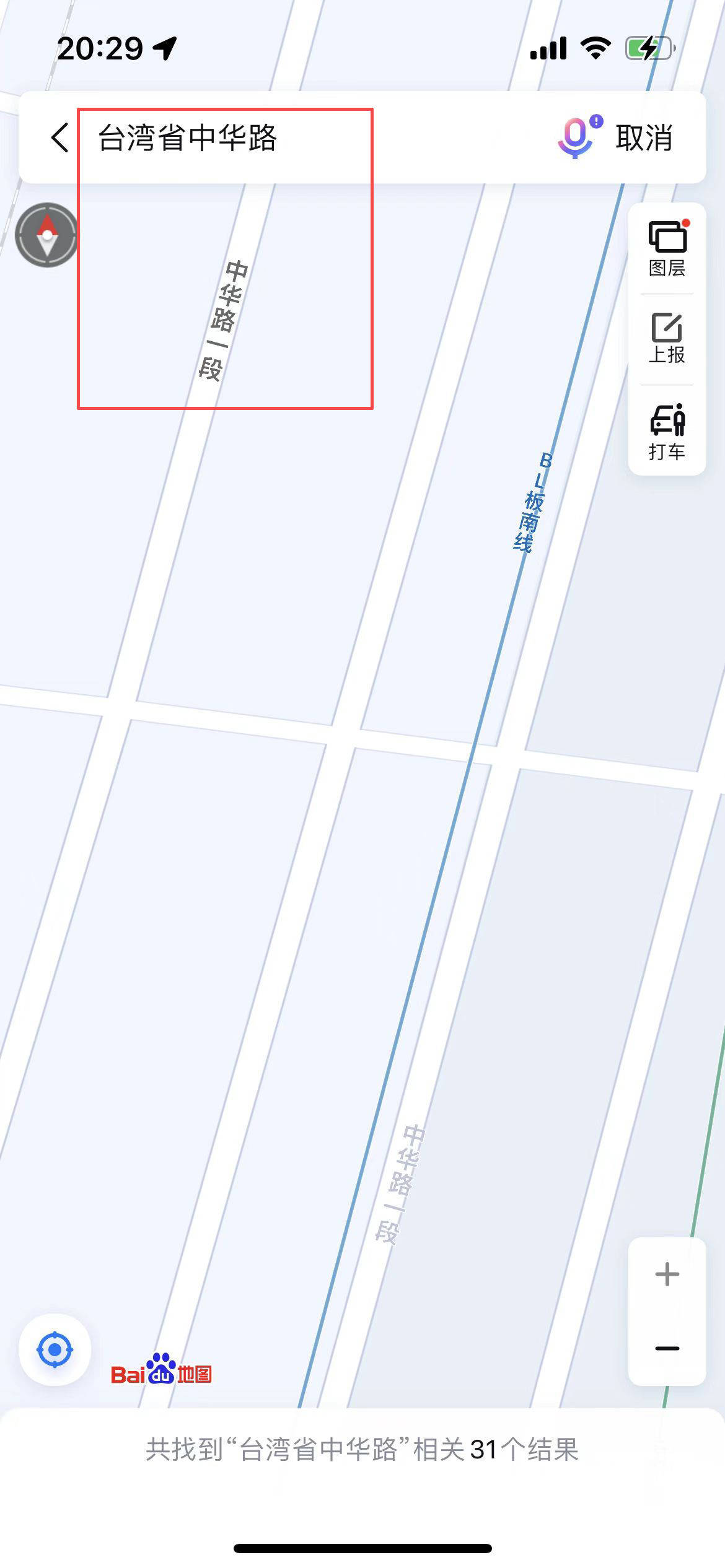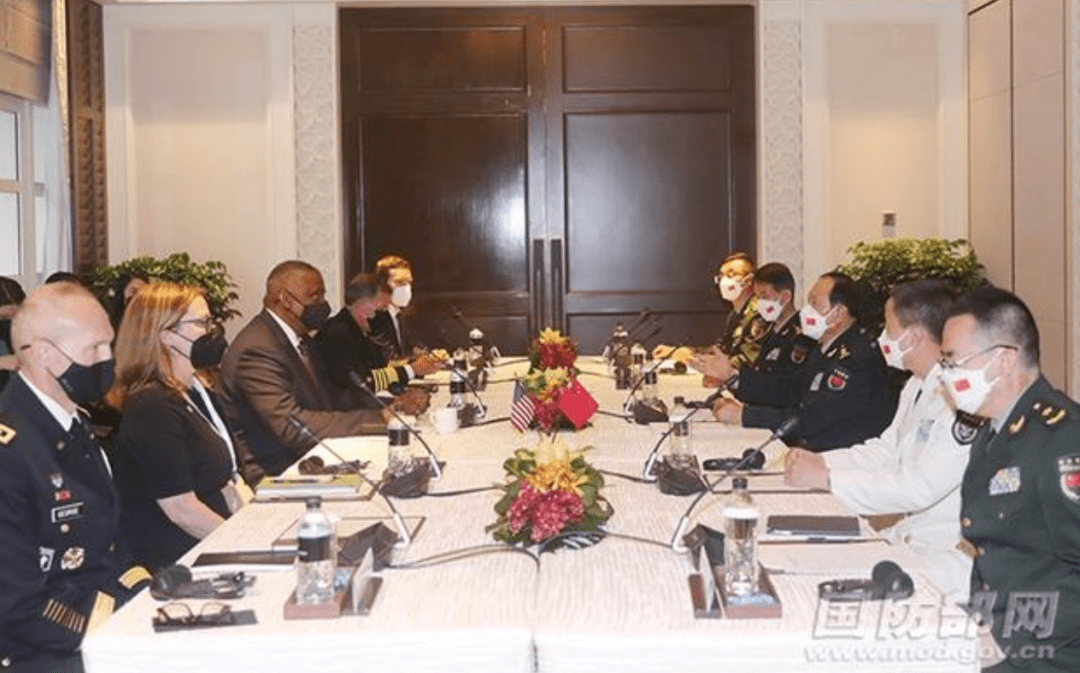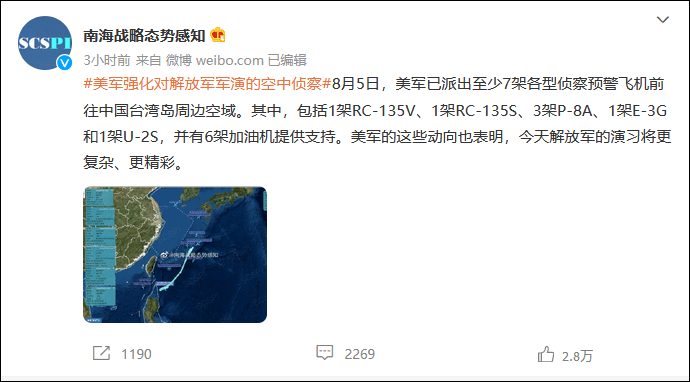俞斌
第1088期
查济从它的始祖查文熙伐木建村,历经千年,到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据说人口十万。关于十万一说我一直心存疑虑,且不说人丁如何兴旺,单从查济村的地形地貌看也断难以容下十万人生息。我曾就这一数字向村中一位威望极高、掌管家谱的老先生提出质疑。老先生以毋容置疑的口吻给我叙述起了数百年前的盛况,尽管在他的描绘下村庄像三维动画般向四周延展开去,但在围拢的山脚下依然遭到了坚决的抵抗,村庄停止了扩张。无论老先生如何复原他的桃源胜景,我却依然无法将十万之众给于妥善安置。
老先生站在桌前滔滔不绝,一摞家谱堆积案头。
此刻的老先生眼里已没有外人的存在,他已站在了査济的制高点上,俯瞰着脚下的村庄。街巷里人头攒动,炊烟四起,黑白相间的屋宇一直蔓延到他目力不及的远方。“十里查村九里烟,三溪汇流万户间。祠庙亭台塔影下,小桥流水杏花天。”这是他的先人给描绘出的昔日繁华。或许此刻站在这里的已不是他自己,而是他数百年前的祖先在借他的躯体传递着一种声音。尽管我心中还有着诸多反驳的理由,但在老先生一脸的笃定和果决前我还是做出了让步。那是一种容不得你抵抗的眼神,那眼神直射出一股透人心魄的力量,这力量告诉你,在家族的荣耀前你不得有丝毫挑衅,必须妥协。
光祥、光荣、光明、光义、宗正、宗仁、宗全、宗礼、福喜、福寿、福德、福贵。在外人看来,这只是一个个简单的符号,很难将他附着于某个鲜活生命之上,时间早已将他的躯壳风干,只剩下横撇竖捺的骨架被夹进书页,轻飘飘地一阵风便可翻过。而老先生端坐于这些名字前,却显得异常的敬畏、虔诚。陌生的身影排成长队,从时间深处飘忽而至,一闪而过。在他的老花镜里这些影子一个个充盈起来,虽然面容呆滞,却饱满而红润。一长串快速流动的影子,最终流成了一条血脉。
如果我们把千年的时光浓缩成镜头里短暂的瞬间,你便会看见这条血脉如决堤洪水般喷涌而出,彰显出他蓬勃的生命力,在大地上恣意纵横,渗透进每一个可以容身的角落,不断派生出新的支流,重新分割着大地的格局。
老先生跟我说;“查济以前什么样其实不用我说,你自己去村中看看便知。你见过哪个村庄现存有三座祠堂的?说了你也许不信,我们查济以前有108座祠堂。”
祠堂早些年在皖南的村庄极为常见,几乎每村都有一座。祠堂第一次遭受创伤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场“破四旧”运动让村庄里封建礼法最高代表形式的祠堂理所当然成了革命的对象。但这场革命不是致命的,当时的革命者还没有足够的本钱将它彻底推翻,只是将它的面目加以涂改、装饰加以铲除、功能加以转换,大多是让封建礼法的殿堂转变成传播革命思想的学校。祠堂毁灭性的灾难在上世纪后20年,急速膨胀的物质欲望挤占了本已极度衰弱的传统文化空间,拆祠堂成了最捷径的获利方式,祠堂一座接一座在皖南消失。当时间走过最初的狂躁,人们内心趋于平静,传统重新浸润人的心灵,此时转头回望,已是残基碎瓦,找不到归路了。在这里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亲手毁掉根基的正是植身于这根系之上的人们自己。
在查济的一百多座老屋中,无论它的年代多久远、建筑多精美、气势多宏阔,都只能屈居从属地位。查济的核心是祠堂,祠堂在村庄中有着不可取代的神圣和庄严。
群山叠嶂、河流纵横,使得皖南的村庄相对封闭而独立。无论外面的世事如何变迁,在山里一切依然。一个村庄便是一个家族,一个社会,族权在这里有着至高无上的威严,族权的最高象征便是祠堂。在这里每个祠堂都有它自己的法律体系,它的权威性有的甚至可以凌驾于当朝律法之上。祠堂同时也是每个家族的根基,每条血脉的源头。有了祠堂,这条血脉不论流了多远,孕育了多少支流,总归能找到他的起点,不至于散失。
在祠堂前我终于读懂了老先生的眼神,那是一种端坐于祠堂之上的威仪。正是因为这威仪辐射出的强大气场笼罩着村庄,凝聚起恣意奔流的血脉,才有了查氏家族千百年来的枝繁叶茂,长盛不衰。
明末清初,查济人的官宦生涯进入了鼎盛时期,一门六进士、三进士、兄弟进士、文武进士、文武举人,一浪接着一浪,据资料记载,翰林、京官、封疆大员、知府、知州、知县等七品以上的官宦达一百二十九人。人在两个时期最易激发起对故土的思念,一是落魄失意,一是功成名就。前者需要故土的抚慰,而后者则需要故土来彰显他的辉煌。衣锦还乡,建祠耀祖,耀的不仅是祖,也是一份自得。
查济现存有三座宗祠,宝公祠、二甲祠、洪公祠。还有一座家祠,德公厅屋,这在以前我们曾提起过。虽说同为祠堂,大致格局相似,无非是仪门、明伦堂、寝楼,厅堂内开设天井,筑金水池等,但査济的三座祠堂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它们各自有着自己的特色。宝公祠坐落于许溪边,墙高体大,以气势见长。二甲祠建在村中部瑞凝午道旁,精雕细刻,以工艺取胜。
在宝公祠内我遇到一位导游小姐正给游客背诵解说词,每天重复的劳动使她在面对祖先安息的圣殿时已显不出一丝的自豪和神圣。当说到祠堂柱础之大可以和故宫媲美时,游客随之附和出一片唏嘘之声。转至扁官巷内德公厅屋,屋内屋外都搭着脚手架,房屋正在翻修。新立起的几根屋柱与那两根楠木柱显得格格不入。也许过些时日经过工人的一番修饰外人便看不出端倪,但不知房屋的旧主人还能不能找到自己从前端坐的位置。
洪公祠建于清代,坐落在许溪边红楼一侧的山坡上。年久失修的祠堂频于坍塌,大门被砖石封砌,远远看去几根木柱斜撑着陷蹋的屋檐,祠旁杂树丛生,人已无法靠近。天色向晚,残阳透过树影斑驳在洪公祠精致的外墙上,将祠前石栏的影子拉的很长很长。
同行的胡主人说管委会已筹措到资金即将对洪公祠进行修葺,年底即可开工,明年就能对游人开放了。
胡主任这一番话洪公祠内安息的魂灵不知是否听见,这最后一块净地又将不再安宁,不知他们明年将迁往何方。
(作者系泾县统计局工会主席)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