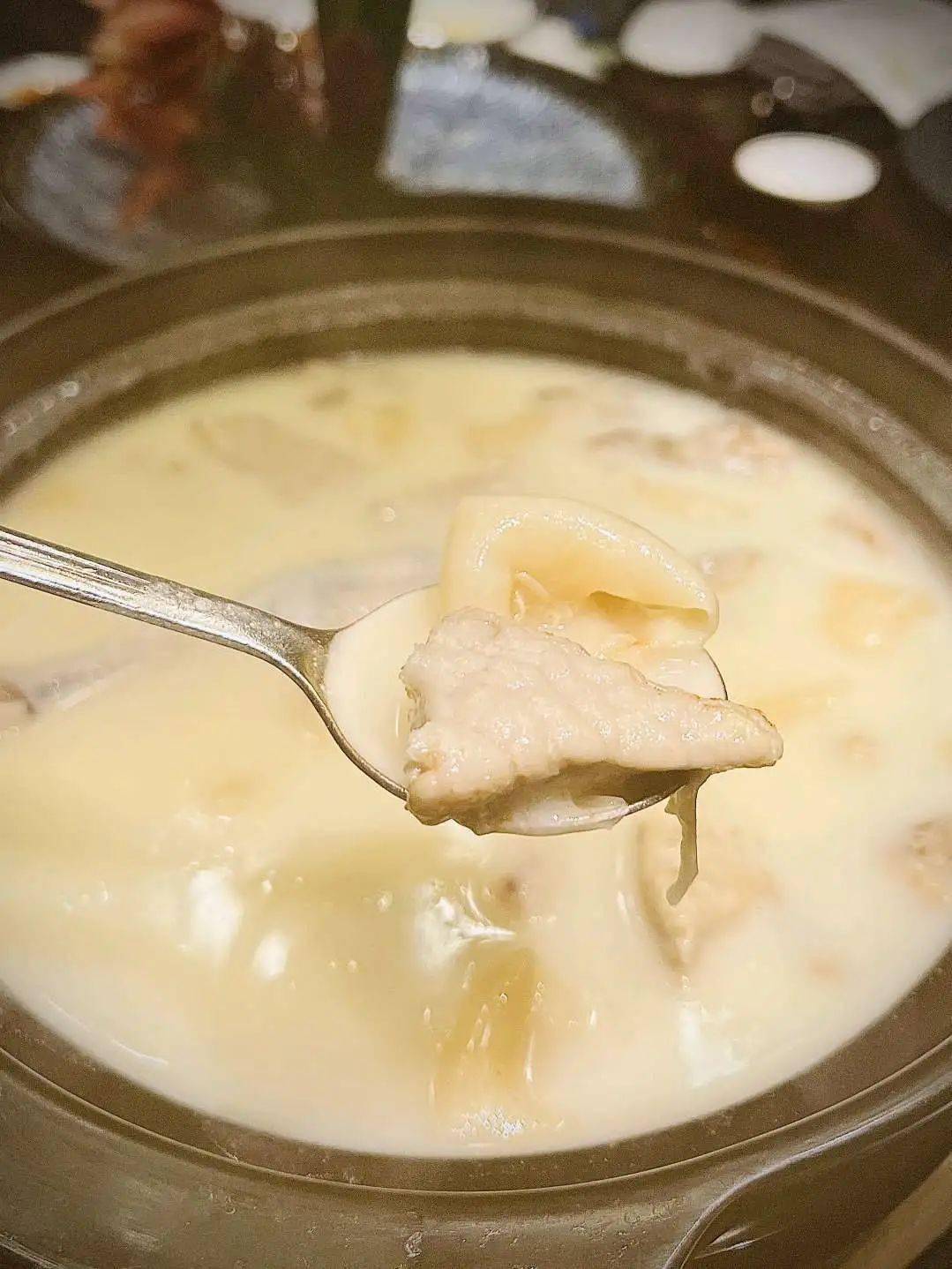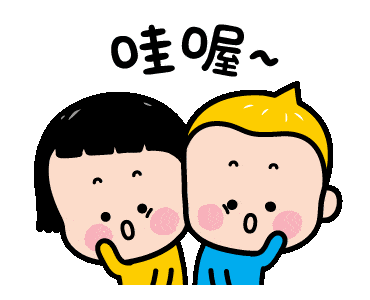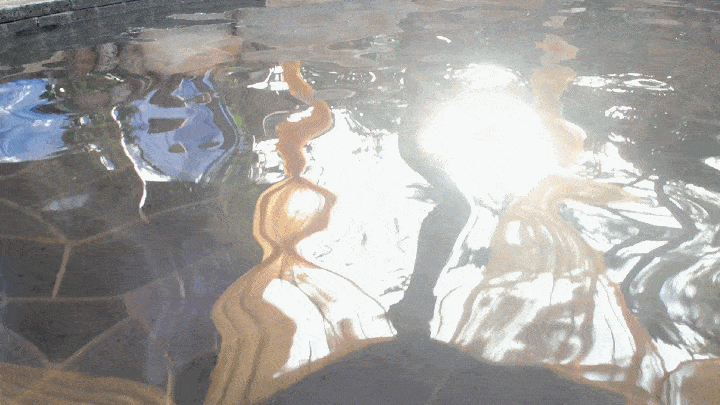其实,我与它相遇是偶然的,也是幸运的。

七步村,它的原名叫郭村,一个以郭姓为主的村庄,却因为成就七步诗之名的曹植而易名。对于一个古老的中国村庄而言,易名是件很难的事,村庄的名字就像是一把无形的锁,锁住的是一些人的家族历史、路线图和未来的时光,是一个村庄最重要的指认,沿着这样的指认走下去,也许可以发现一个村庄引以为荣或引以为耻的秘史。
然而,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它让自己久已成形的脸谱换上了一副异然的面孔。当机动三轮车沿着通往城东的乡村道路奔驰时,两边郁郁葱葱的玉米地从四面八方展开,形成了一个巨大浓绿的热力圈。我看到了这些处于青春期的玉米所拥有的向上的情绪,还有一些开着红花和白花的棉花,和另一些我无法看清的低矮的庄稼。路边的渠是干燥的,水分的蒸发在中原大地上很快,灰暗的沙土表面细腻平滑。宽大的叶片在午后的阳光中悄然静立。风是藏在树木和植物的叶条里,而此时它却深藏在它们黝黑的身体中,不肯出来照一下面,更多的是车轮扬起的灰尘。
这一趟行程在河南诗友空间热情的随行中充满了意义,他们的河南方言我似懂非懂。曾在候车室外面,我们两个相隔千里却从未谋面的朋友一眼就认了出来,那一刻的呼唤充满了激动,它辨认了两个同质的心灵。直到七步村曹植墓门前,我才恍然大悟——他们所说的“曹植墓”颇像陕南地方话“造纸墓”,让我一路迷惑不解。我的家乡古洋州是造纸发明家蔡伦的封地,也是他最终的长眠之地。

车停在“曹植陵园”的门口。木门破落,缝隙犹显。从门缝中望进去,只见一片荒草,我们的心随即沉了下来,想不到建安才子的长眠之地竟如此荒凉。木门被一把锁锁着,锁杆上有些锈迹,看来好久都没人来过。看管门的老头不在,空间兄忙着去寻找钥匙,恰好遇到陵园旁边小学的校长,他才托人寻来钥匙。
门吱呀的一声打开了。那一声有些凄迷,有些悲凉,有些泪水风干后的味道,五六点的阳光穿门而过,打在高高的荒草上,像是从黑暗中犁出了一道浅浅的亮光,一些虫子在阳光突然的照射中显得惊慌而四处奔跳,陌生者的进入让它们改变了某种已定的秩序。木门打开的声音并没有随着我的进入而消失,反而像从墓地中某处隐秘的地方传来,又似乎要归于某个草丛的深处。我知道它为一个诗人苦难的灵魂找到了述说的路径,像一个人亲近的耳语。我很想携带这样的耳语来与一个千年之前的诗人会晤,去感受他被煎熬的灵魂。
墓碑上字迹模糊,碑身高耸厚重,碑座稳憨却留有破痕。据说在一次黄河水泛滥之后,一片土地陷了下去,露出了碑尖,人们才挖出这道碑石。看来,历史掩埋得比现在荒凉,更加让人目不忍睹。在新建的墓碑前,空间找了一根蜡烛点着,小小的火苗在夕阳中显得脆弱而无奈。

花斑的树影落在墓前的一尺多深的荒草上,不大的陵园充满着一种言无不尽、言无不及的沧桑,四周的院墙长满了被时光忽略的青苔,更长的荒草从墓沿的围砖上垂下来。这是夏秋交界之际,青草的绿茵还能让人感受到一些生命力量的存在,感受到了曹植作为一代才子通过草色转换出来的诗情。如若在深秋或隆冬,这座园子又不知是什么样子,枯萎的荒草,落地的枯叶中藏着一些躲闪的时光,一丝凉意的秋风,一许雪白的霜,墓碑上的灰尘或多或少地掩饰着碑文,香台上一缕淡淡冒起的青烟,光秃秃的树枝上一两声揪人的鸟叫,三两束打在树技侧面的散阳……,那时,一个园子的破落岂能用词语来表达完整。
如若一个月光朗朗的夜晚,静静地站在园子的一个角落,聆听虫鸣从荒草中缓缓溢出,爬上碑文和碑身,再到树干和树叶之上,那将是欣慰的事。在这样的月光下,一个人的身影会像树影一样绰约,像光丝一样感人。就在下午,我看到了蜷伏在碑顶上的六只蜗牛,它们都摔掉了身上重重的壳,与那些在碑顶上雕刻的浅浅的白线相遇,像是墓碑上的几个特殊的符号,颇有一些现代画的意味。我想,爬上碑身的这六只蜗牛是多么的幸运,它们也许不知道,它们全身心倾听的是一位千年之前的诗人在月光下的吟诵,感受他的呼吸、心跳和他走动的脚步,一个月色构筑的夜晚在诗律的和声中缓缓摆动,那是多么的惬意,多么的超然。
然而,这一切的想象都会在一首七步诗前全然崩溃。人世间所有的美好和亲情会因这首诗而撕得粉碎。“煮豆持作羹,漉豉( chǐ)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想当时的曹植是非常的绝望,兄弟之间的残伐是如此的迫不及待,让人寒心。我反复揣摩着“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句诗,仿佛回到了无数年前的那个对峙的情景,曹植的绝望和悲愤让他发酵出极高的诗情:手足相残,何须太急!

从曹植墓出来,仿佛从荒凉的历史中踏步而出,我们每个人都带出了曹植的一部分,安放在记忆的一角。曹植应该是有些安慰的,七步村这个名字给了他永久的纪念。当那两扇木门再次吱呀一声合上的时候,我的心又被触动了一下,仿佛曹植送别我们的目光被一声切断。
——他依旧留在了里面,而我依然要远行。
(文/肖建新)
欢迎走进“五色石文斋”。如果您喜欢,请点击关注,也欢迎您分享、评论。在这里随时有精彩的文章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