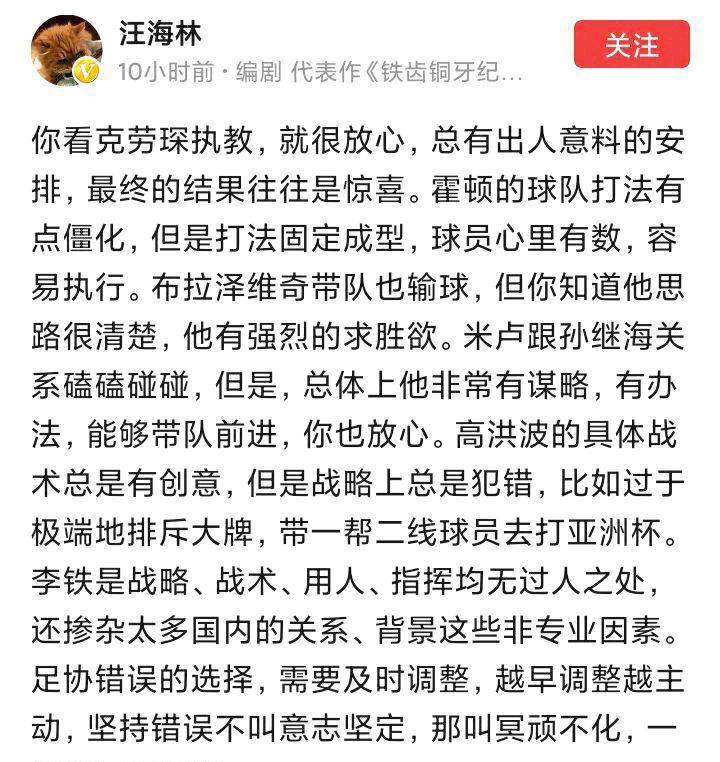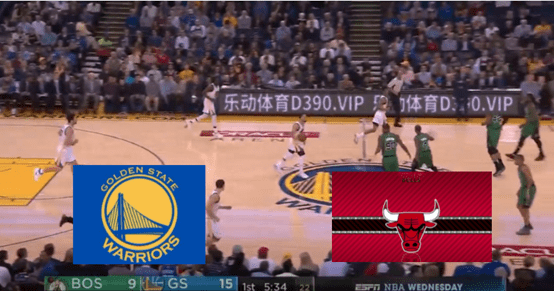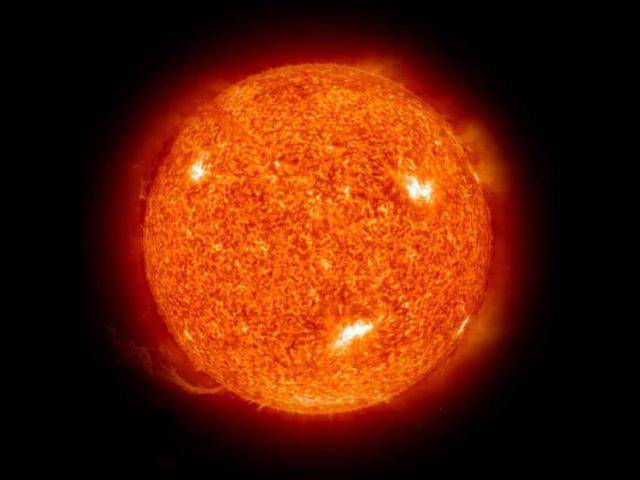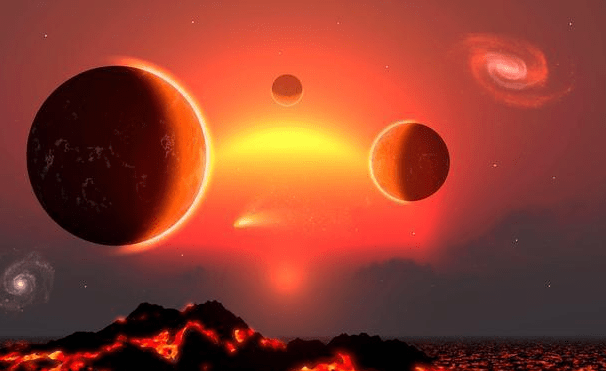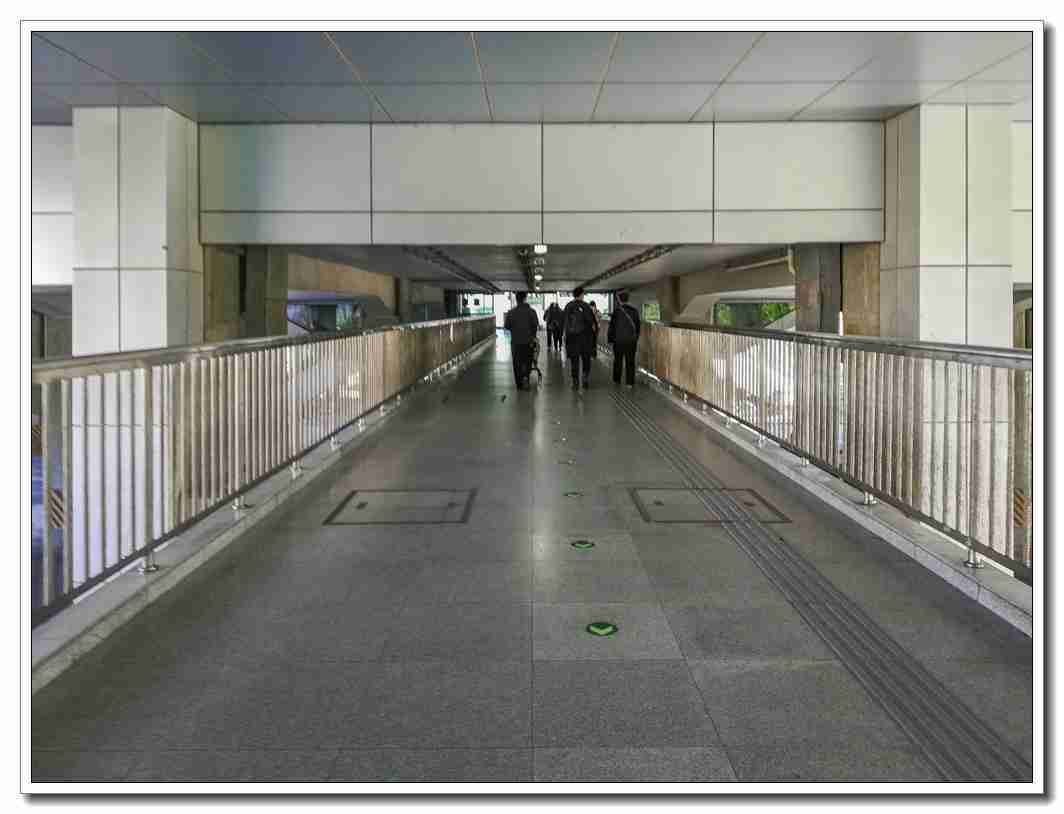2015年1月,东湖凌波门栈桥。这里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东湖南路,紧邻武汉大学。谌毅 图
在进入现代都会居民的生活世界之前,东湖在早期的地图上,更多被标注为“郭郑湖”(中国农村惯以宗族姓氏聚居情态命名村塆或山水,今天,郭郑湖仅指东湖的一部分)。后来的“东湖”字面之“东”,显然是相较于武昌乃至汉口而言的城市区位。从“郭郑湖”到“东湖”的名称迁易,潜伏着东湖从农村渔猎之湖到城市园林之湖的转变脉络。
是特定的文化而不是自然造物让旷野成为风景,对城市文明有所反思才会让城市居民也可能拥有乡愁,城市文明的心灵成长有时可能先于物质进步。因而,乡愁甚至会先于大路抵达东湖之滨。当大路直通东湖岸线,城市化进程接踵而至,反而可能使乡愁之雾于湖面上蒸腾散失。还好,这种危险至今主要还是潜在的。
21世纪初涌起的城市化巨浪,又把东湖从城郊裹入城心,而东湖成为普通武汉人生活中的亲切日常,还要远远早于环线把东湖纳入城市腹地。没有周苍柏家族以乌托邦式的努力开风气之先,难以想象精明现实的汉口人会一代又一代乘坐渡船,或者于1950年代至1990年代之间绕行长江大桥,辗转来到这片遥远的水面。
东湖布鲁斯
民谣歌手冯翔传唱最广的作品《汉阳门花园》是写给武昌滨江的,至于最令他情难自已的,则是《东湖》。
他曾说:“在我的内心里,长江汉江和东湖,是我的家乡最根本之处。”他带女儿游玩时,看到东湖景色仿若当年:“对岸的磨山可能已经变成黛青色,西面的天空可能布满紫红的云……我们慢慢走着,直到夜色降临。”这些总会让他想起童年时爹爹(武汉人把爷爷或外公叫“爹爹”)背着他在湖边,边走边唱“背坨坨换酒喝”(武汉家喻户晓的一句童谣,大意是背着小孩去换酒,酒来了还是舍不得小孩),唱录《东湖》每每使冯翔哽咽涕泣。
他还有一首《凌波门》,唱的是:“樱园的樱花又开了,东湖南路每天都堵倒,过些时热天就来了,我们就可以一起往东湖跳。”他在歌里呼唤的罗刘唐周几位老师,就住在凌波门里的青年教师宿舍。那里也是后来我在武汉大学念书时住的学生宿舍。《凌波门》歌中“花开了满树,花落了无痕”的景色,我连看七年,当时只道是寻常。
在冯翔为人熟知之前,更早传唱东湖的是达达乐队的彭坦。这个水果湖少年一夜成名后闯荡北京,“帝都”平坦干燥,他被一场久旱之后的雨水唤起乡愁,写下《南方》,歌中所唱“我家门前的湖边,这时谁还在流连”,很适合发生在与东湖主体相连的双湖桥上。冯翔的东湖有悠悠古意,彭坦的东湖则是少年幻梦,“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
在另一首《东湖隧道》中,隧道被形容为“孤岛”和“城堡”,穿过隧道就回到了家。现实中的东湖隧道则深沉湖底,从梨园到磨山,半程就有十来公里。潜行在湖底,仅有一两处,天光由风井透进,此情此景之下,不论孤岛抑或城堡,无非当事人不知不觉“以湖为鉴”,蓦然照见的自身精神镜像。

2015年7月,在鲁磨路VOX Livehouse巡演的一支湖南乐队。VOX Livehouse现已迁往七八公里之外的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意大利风情街。谌毅 图
早在本科高年级,我就在东湖边上武大樱园的一场演出中见过彭坦。演出场地位于樱园所在的狮子山山顶,名为“学生俱乐部”,那里传统上是用来给蔡元培、胡适、蒋介石、李宗仁、司徒雷登这样的人做学术报告讲演的,1937年周恩来宣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是在那里。“学生俱乐部”通称“学俱”,实际上是从学生食堂顶部隔出来的阁楼,作为小礼堂使用。这种与地下摇滚格格不入的“场所精神”,反而让那场演出更带劲了。
实际上,东湖周边是武汉摇滚(乃至城市其他原生生态)的“广阔天地”。十几年来,从西岸的凌波门,磨山半岛曾经的“我们家”青年自治实验室,小李村的录音室,鲁磨路的VOX Livehouse、PRISON、国光大厦,到更东面喻家湖的城中村……一直有无数乐手在排练、创作、演出、聚会、生活,并和其他城市隐士混居。
“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东湖参差多态的社群空间依托于它变化多端的地形条件,这里岬湾交错,115.5公里岸线错综复杂,全湖大小湾汊逾120个,每一湾每一汊都可能形成独特的小气候,一定程度上,逸出了主流社会的引力场。
“跳东湖”
如果说有一个事件能够相对集中地映照出东湖诸聚落人群的特质,那就是2010年始于凌波门的“跳东湖”。如同东湖本身,“跳东湖”的语义,既是一个开敞开放的空间,又是一个延宕自发的进程,且至今还在持续变化。

2017年8月6日,一市民和一只狗从武汉大学凌波门水上栈道跳入东湖。当日,湖北武汉市持续高温晴热天气,不少市民来到武汉大学凌波门水上栈道,用各种方式跃入东湖,亲水消暑。新华社记者 熊琦摄
对外地人来讲,它可能是一款来自武汉的苦苦的精酿啤酒;对打卡一族来讲,它可能是一年一度武汉盛夏的时髦玩水派对;对亚文化青年来讲,它可能是一场混杂了自发行为、极限运动与荷尔蒙宣泄的跳水狂欢。对当初参与发起的艺术家、建筑师、朋克、知识分子等人来讲,“跳东湖”则首先是旨在保护东湖、反对填湖开发的“东湖艺术计划”的一部分。包括“跳东湖”在内,整个“东湖艺术计划”都带有显而易见的去中心、自发、无政府主义的行动色彩,并且不是宏大目标下的激烈对抗,而是符号性象征性的机智行为。
可以想见,这样的“跳东湖”,注定将一再经历消费主义的同化与消解、权力的粗放管制与有限容忍,并且这两种力量近来有合流的趋势。既然“世界级城市绿心”已经推上前台,一个可控可运营的东湖好IP,刚好是武汉城市营销客观所需。
当年的“东湖艺术计划”中,有一件作品是在电信设备箱上,以虚拟的“东湖不动产”名义喷写“填湖就是犯罪”。现在,这个箱子外面又罩上一只焊接金属笼,箱面上的字迹显然被贴覆过,又被人撕掉贴覆露出来。九年过去,这件作品已经从一种反对性的存在,变成了体制化景观的一部分。
如同一再发生在这个城市的很多事情,有关意义的企图很容易最终自发消解,融入无意义的生活本身。一年比一年盛大的“跳东湖”越来越像是一个受人欢迎的民间节日,充斥着啤酒、市集摊位、四处打卡的带妆女生、乱入找乐子的大龄市民,以及烈日下蒸腾的荷尔蒙气息。
目前为止,这并不坏,至少在当下,庆祝无意义就是一种稀缺的意义。跳,往东湖里跳,这多带劲儿啊。“封城”结束后的第一个“跳东湖”就是如此,数万年轻人在湖岸边聚会到日落,仅仅是看到彼此就已足够快乐。
南望山与雁中咀
最后,说说我个人与东湖的聚散。如前所述,我在湖边的武大度过求学时光,毕业离开时正赶上“入世”后国运空前喷薄,九年后更是到了烈火烹油的高潮。那两年,人人都在谈论搞项目、拉投资、上市,几乎没人愿意正视,凡事皆有尽头。
我就在这样一个时刻被际遇带回了东湖,和团队在南望山的城中村租下一栋小楼,创办了一本杂志。彼时,纸媒已近落幕,这里离闹市咫尺之遥,却又偏僻之极,应聘者不时因为迷路而放弃面试。

2014年12月,东湖南望山城中村的一个下午。谌毅 图
小楼背后是一面山崖,偶尔有走失的山羊,站在悬崖边上远眺。午饭路上,在山腰遇见墓碑,上书“蛮王之墓”,证明这里曾是东汉“江夏蛮”最后的藏身之处。出村的小路边,歪牌子上书“中科院水生所白鱀豚馆”,周遭一片荒僻,那时白鱀豚已灭绝近十年。湖边淤泥中陷落小舟,船舱淤满,以微不可察的幅度荡漾、旋转。
每天驱车掠过东湖水面进村。冬天,天台的阳光房热到出汗;秋天,在后院烧烤,仿佛能看见眼前的山体断面有一天会吞没这个小院。那几年,大概就是现在所谓“躺平”吧。因为做杂志,我也多少了解到,有很多人远离今天的所谓“996福报”,散落在东湖其他角落,他们试图以做手工、开民宿等为生,当然,今天其中一些人已经把这些事做成了网红生意,游客跟随小红书指引抵达幽微,新的欲望在东湖深处滋长。
南望山距离磨山半岛鲁磨路沿线的摇滚圈子很近,我曾短暂参与他们创立本地独立音乐厂牌的项目,并为厂牌取名“野生”。野生,是武汉,确切的说,东湖的气息。
后来杂志停刊,我再次离开东湖,这几年很少再去。
前一段,同事告诉我,东湖深处有一城中村,名为雁中咀,很神奇。我打开地图,雁中咀在湖中心,就像是渗进水杯里的一缕墨迹,经过布朗运动到达极限,散淡到可以忽略。

位于东湖中心区域的雁中咀。微信公众号“HANS汉声” 图
虽然雁中咀在三环内,看方位甚至差不多是武汉江南城区的地理中心,但那里“灯下黑”,实际上是一个外卖和快递送不到的地方,无论是在互联网的算法里,还是在城市化的网格中,雁中咀目前都太“偏”了,无法凭借美景招揽游客做民宿。
村里房租低廉,生活自给自足,年轻人住进去就不想再上班工作。村民传统上是渔民,因为禁渔也不再打鱼。每天傍晚,这些前渔民和租客一起躺在湖边看日落。雁中咀租客里有过一个英国画家,还有一位神秘人士深居简出,最后被警察带走,竟是逃犯。
雁中咀并非遗世之地,它已被列入“东湖绿心”改造范围,只是改造暂时处于停滞。
除了逃犯,没人需要真正无人知晓的隐居,人们憧憬社交逃逸,但并不希望陷入“社会性死亡”。我猜,没有租客能在雁中咀经年久居。
算法时代的“不服周”
偶尔,我也会想起南望山的蛮王之墓。蛮王治下的江夏蛮,前身是巴国人,《华阳国志》载:“昔(周)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可见,巴国是周室姬姓宗亲的封国、诸夏之一,和鄂西北的随国一样,是周王室把自己人安排到南方来屏障异姓楚蛮的“汉阳诸姬”,因此,按理巴国人是地地道道的华夏,如何竟成蛮夷?
战国末年,秦灭巴国(公元前316年)后,在巴国故地置郡县,而把巴人一部流徙江夏,称江夏蛮,宋代又称为沔中蛮。可见从秦至宋近千年,原本出身宗周华夏的江夏蛮,一直是蛮族待遇,是身在编户齐民之外的非主流。如果说在先秦时代,宗周室从周礼就是华夏,那么秦以后,纳入郡县流官编户齐民治下才是华夏。否则,哪怕出身周王宗室、身居内地郡县,那也是蛮族。
蛮族聚族自治,不受朝廷派出的官员直接管理。理论上,蛮族对朝廷的义务,本质是藩属对宗主的朝贡,而不是户民对官府的税赋,一旦朝廷征敛失当,蛮族自治民比普通编户之民更容易不满反抗。公元47年、101年、169年、180年,江夏蛮至少四次起事,起因就与税赋有关。
其实,在最早有蛮夷说法的《尚书·禹贡》里,就提出了用距离国都远近来划分统治圈层和义务轻重的“五服”天下观。简单来说就是,距离越近,义务越重,统治越直接,越远反之。
根据顾颉刚先生的解读,国都附近的百姓不仅要纳谷,连秸秆都要上交。中央政府的势力范围限于第三层“绥服”以内,绥服的义务就偏重于教化和守备,而“夷”在第四层“要服”,“蛮”更在第五层“荒服”。按照《周礼》,要服之夷的义务是“六年一见”,就是说,每六年朝贡一次;荒服之蛮的义务是“世一见”,就是说,新酋长上位,去觐见一次天子就够了。
《禹贡》里讲“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三百里蛮,二百里流”,意思是蛮夷都属于化外之地,用于流放。先秦时代,楚王频繁征讨巴、随等“汉阳诸姬”,动辄自表“我蛮夷也”,正是在敲山震虎,以蛮夷游离于天下秩序的超然姿态翩跹起舞,与天子周旋博弈。今天武汉话里的“不服周”就来源于此,意思不是不服道理,而是对特定秩序、权威或强力的不信服。
以天下秩序观之,“三百里蛮,二百里流”,在被秦王灭国流放江夏的那一刻,巴子遗民的身份就从诸姬、诸夏变成了蛮族。在秦汉式强力国家面前,蛮固然是秩序的贬抑,何尝不也是命运的褒奖。

2015年1月,东湖凌波门外,一男子用湖水洗脸。谌毅 图
两千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古人执念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最终超级实现于工业文明对极地荒野的空间连接,“编户齐民”最终超级实现于移动互联网对在线个体的算法编织。
算法时代,不存在真的荒服之地。只是,面对东湖的波涛,再次纵身一跃,仍是武汉人无法被填埋的野生自在。
对了,当年我在凌波门栈桥上看皮划艇,它们驶过南望山侧便不知所踪。后来,我在自东湖新村凌空而起的跨湖大桥上找到了它们:晴光反射的水面尽头是南望山背后的U型港湾,那些皮划艇一开始只是百十条黑色的短线,直到越来越近,终于从我站立的桥面下呼啸而过,浪花碎成无数十字星,转瞬即逝。
点击阅读原文,解锁更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