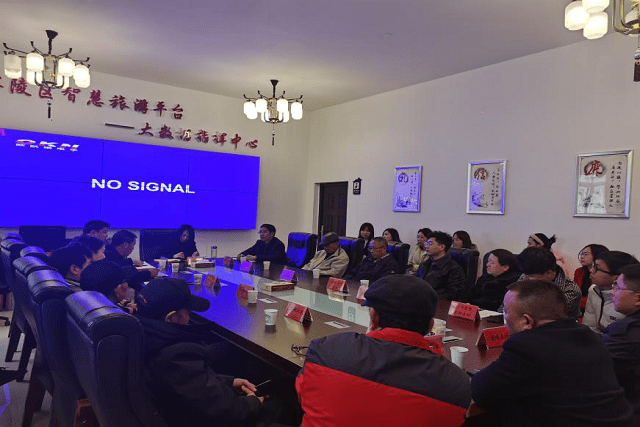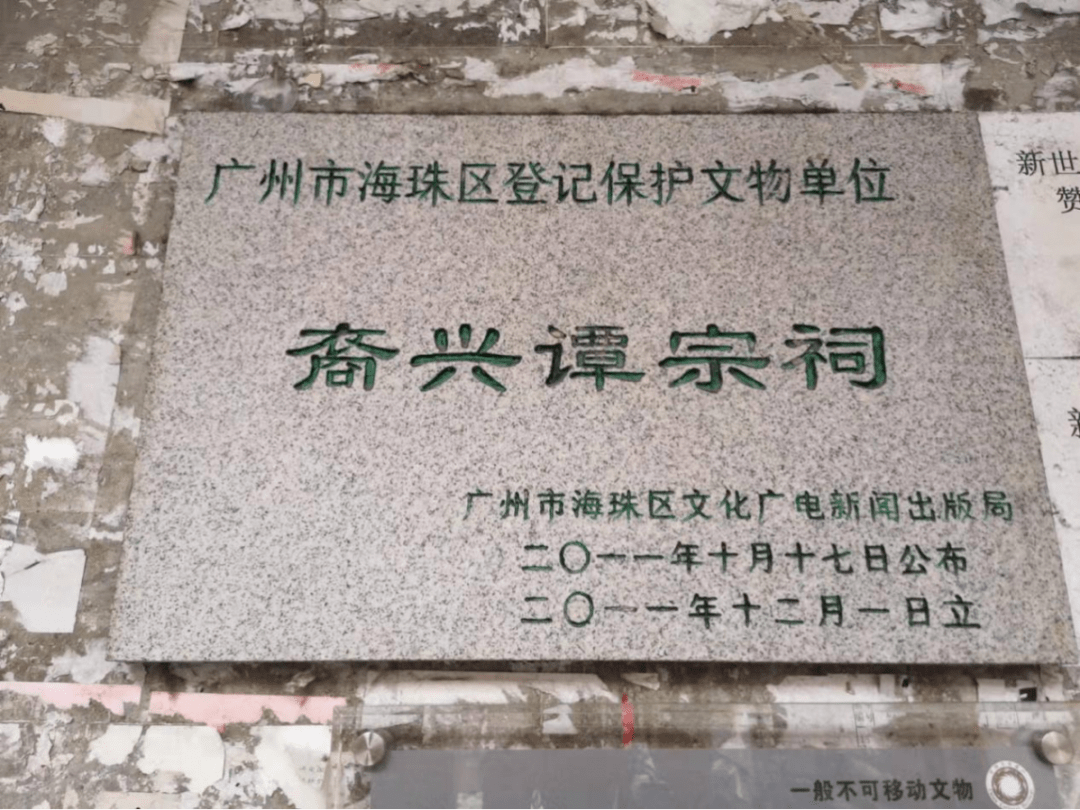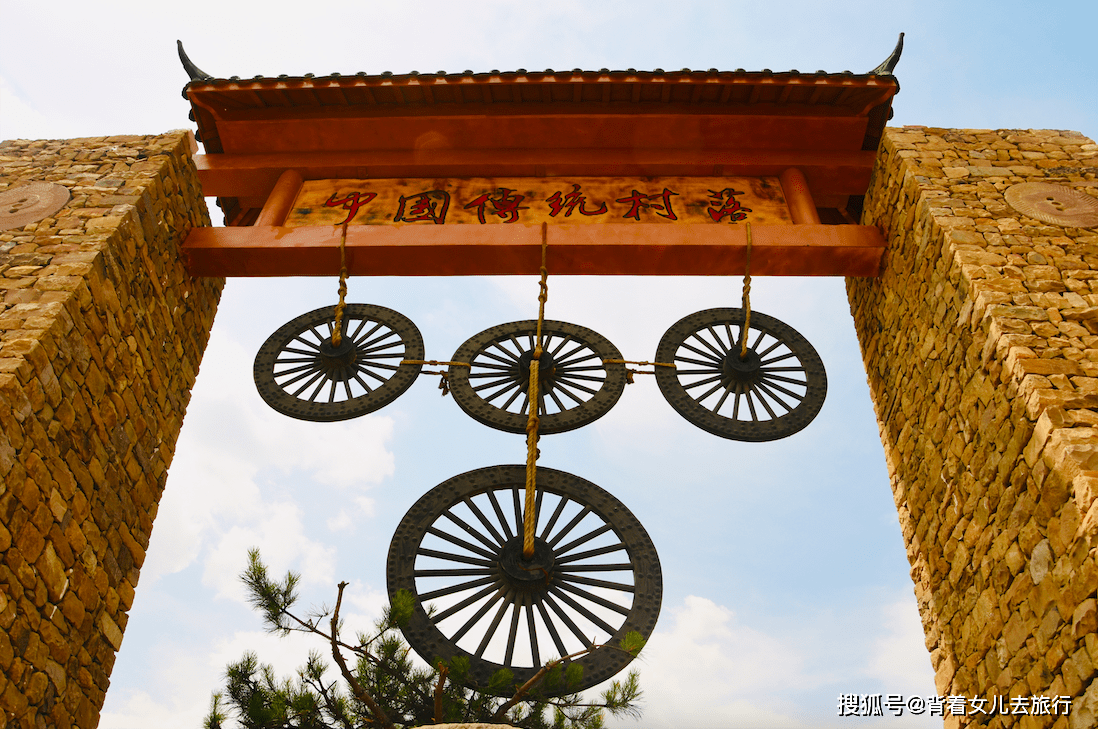不知道它有没有名字,姑且叫它天石峡,峡中的这些滩叫天石潭。我希望它是我臆想中的它。

它却有些神态冷峻,仿佛一直板着肃清的面色。但轻柔细腻的肌肤,既像穿着蝉翼的丝织物一样飘逸,又像深藏的佳酿一样剔透,得了天生丽质,又修来冰清玉洁;当看不透时却任凭你遐想,也不知道它深的去处和深埋的秘密。除非你游了过去,徜徉在它画着叶眉和沉睡着月亮的滩中,即使深陷着,也要拼了力气爬上去,再到它的另一滩中去。它那看似半开着门和半开着窗户的景致,就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投入你的视野。
刚下车,找不到从公路走向它的去处,还好,从灌木丛中拨出了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豁口,才几步下去,就发现一个个巨大的石块横七竖八地耸立着。这些石块,有的俨然一间房,又像草垛、石塔一样孑然醒目,超然夺魂;有的幻化成像饮水的大象、像爬着的乌龟、像丑陋的蛤蟆、像狰狞的蝙蝠鱼;或者,干脆就叫牛石、熊石、海豚石、怪兽石、人面石吧,任由你慧眼发掘,展翅你的想象。总之,无论这些巨石是横着、竖着、斜着、重叠着,具象、抽象,都有着各自旁逸斜出的棱角和映衬出的个性,有的还缠绕着一圈或几圈蛇一样的纹身。
真不知道这些石块是从哪里来的?怎么齐刷刷地汇集在了一起?是从更陡峭的山旮旯被移出来的吗?是从天上或者哪个星云掉下来的吗?不过,我还是最倾向掉下来的推测,但又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掉下来的呢?它们的使命是要来包围和堵截这条河去拥抱另一条河吗?
然而,这条河依然从布阵森严、狼牙突兀的间隙雷鸣般地呼啸而下。想必是倚天拔剑,或用了“开山斧”的神力劈开的;想必是积水穿石,或用了铁杵磨针的坚守磨出来的;也许,是这些大石块无心恋战、发生了内讧或感动了守门将军让出了一扇扇门。这条河终于在这里一跃,一个三级跳又一个三级跳,捧出了从大山深处绕道而来正在被迅猛融化的冰渣或正在消融的积雪。

显然,这是探险,而且我们没有任何充分地准备,除了手机必须携带要取些镜头外,什么都没有。这是盛夏,但在天石峡的字库中似乎就没有“夏”这个字,“盛”更是尚未造出来,网络用语连边也不曾沾上。近二百米的峡谷险滩,亦可谓“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一面是山陡如削,高耸入云,一面是巨石诡异,狐精妖气。无论你如何用了心去看,都似乎显出无动于衷的不屑或睥睨不驯的桀骜。潭水深处,湛如瓦青,色如墨黑,寒如白刃,气如紫霜。据说,峡谷上下时常还弥漫一层哼哈二将吞吐出的黄色和白色的浓雾。数年前因淹死过几个年轻人,就再无人胆敢涉足。
我们脱了鞋衣,小心翼翼地从一块大石头上侧身而下,头一个给我们的考验就是五米见宽十米见长的河滩。同游中一个胆量最大、水性最好的,试探着逆流而上首先就游到第一个石门处,回头大声喊:“行,可以上!”然后返回,准备携带手机,让我和另一同游先过,再接应。
石门处的中间是一块背篼筐大小月牙状的门槛石,我称其“月牙石”。看样子是硬要阻挡奔腾而下的湍流,水势之急却又哪里可以螳臂一挡。即便把水聚起来,还是要一分为二,至多能甩出两条半米高的龙头。朋友力大,几个侧身,两只手抓了门槛石的突兀处,一个腾跃就上去了。我抓了数次未能得逞,一呛水,被龙头喷出的水柱推去一米多远,立马乱了方寸,紧张的神经瞬间被拉长到极致。幸亏,我很快把头浮出水面,一眼看到了前面那块形美的月牙,犹如落水者将要抓到等待在大江上的一只船。我断然打消了退回去的念头,依然朝前游去,朋友也几乎是半趴着伸出臂膀,用强有力的手将我连拉带拽拖了上去。

另一个朋友呢,是要带上手机。手机预先装在塑料袋里再拧一个结,生怕浸水,或者掉入水中。看那壮举,像是举着点燃的火炬,他是用一只手将塑料袋举着,游到了我们接应的石门。
总算进入了另一个境界。取景拍照时,得把塑料袋用嘴含着,而且,几个人要时不时地换着互拍。我们越过的是一个七八米长两三米见宽的狭道,真想不到这种放大了的“U”型渠是谁在没有水泥被发明之前创造的奇迹?偌大的石块又是用什么起重机将其组合在一起的?虽然有些扭东列西,但未经填缝就浑然天成,如铁打一般牢固。
水很清冽,能看到底层的石头,毕竟不敢贸然,得一步一步向前试探。出了这个狭道,流水从一片高台翻滚下来,同样是边舞边唱,弄了一大堆浪花编织成了银白色的小瀑布。从这一大堆浪花的一侧爬过去,又是一个三米多宽的石门和一个十多米长的狭道。再往上走,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带着坡度的石滩。锅碗瓢盆一般大小的石块像聚在一起开万人会似的,水从这些石头的胸膛、背上、肩头上流淌着,并哗哗然响出抑扬顿挫的音律,还给河道弄出一大片梨花杏雨。少许阳光从树缝间透过来,又照射得水面像盛开的一地白棉花,蛮是要永远地这样灿烂下去。
再往上走,就要越过这片石滩。浸泡着的石头生了苔藓十分光滑。这一硬一滑,必须弯着腰半步半步地挪着,没有丝毫经验,不得不摸着石头过。一不小心,乱石就会很可能滑你一跤,轻易地别你一下,近距离地打个招呼给你个鬼脸,或者给你一个甚至多个挫折教育。

上到石滩高处,又是一个比较大的水面。水面很平静,依然是墨汁一样的颜色,生出一些森冷和高深。同游者当中那位最具水性最具胆魄的朋友,说要游过去,再过一个石门。其实,顺着石门望去,那边弹跳着雪浪花的水流已经显示出别样的美景。毕竟,朋友只游了一半,还是让我们喊着劝了回来。他说:“深得很,深得很!”
少则三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也疲惫了。返程虽是顺流,但照样得务必谨慎,就像下山要一步一步踏稳了再敢往下走。况且,各自捡拾了一块奇石要带上。我的小些,带了两个,中途不得不将一个舍弃。带着手机的朋友捡拾的是一块五公斤样子的奇石,我们怎么劝,他还是不肯丢手。退回门槛石又要跨过第一个险滩时,他便把装了塑料袋的手机先送回岸。这一次,他是抬着头用嘴衔着游过去的。再返回,从我的手里接过他的奇石,却是放在胸膛上飘着过去的。我紧随其后,最后一个也游了回去。这时,站在高处,再顺流而看,这样的景致竟接二连三。
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条属汉水流域叫溢水河的上游,坐落在何家大院那里的西侧。四周树木葱茏,悬崖峭壁。日照对于这里的人家着实很吝啬,有时看有太阳在头顶,但总不肯多一点时间停留,常常一锅烟工夫就藏匿起来了。这里早晚,不免笼罩出厚厚的清冷和浓浓的沉寂。

天石峡一游,使我忽然想起多年前就曾听说过一个采药者的亲身经历。说这天天气不错,他刚走下吊桥要继续朝深山里面走时,迎面走来两位穿着时尚的女子擦身而过。女子容颜姣好,气质雅静。当他回过神时,吊桥上的女子却突然没有了踪影。
现在想来,天石峡和天石潭莫非就是这两位女子呢?那画着叶眉和沉睡着月亮的潭中,又有谁去过?那似乎显出无动于衷的不屑或睥睨的桀骜,又有谁经历过?
(文/沙鹭)
欢迎走进“五色石文斋”。如果您喜欢,请点击关注,也欢迎您分享、评论。在这里随时有精彩的文章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