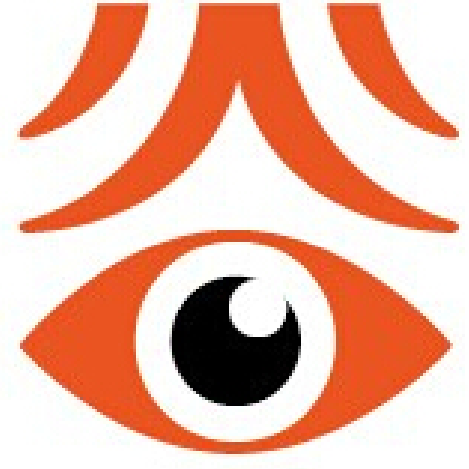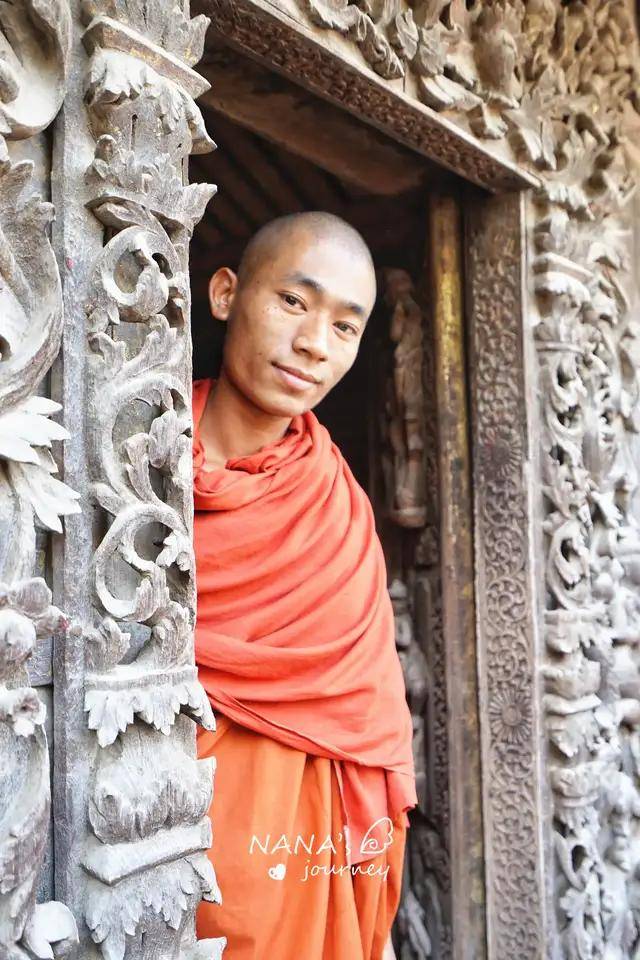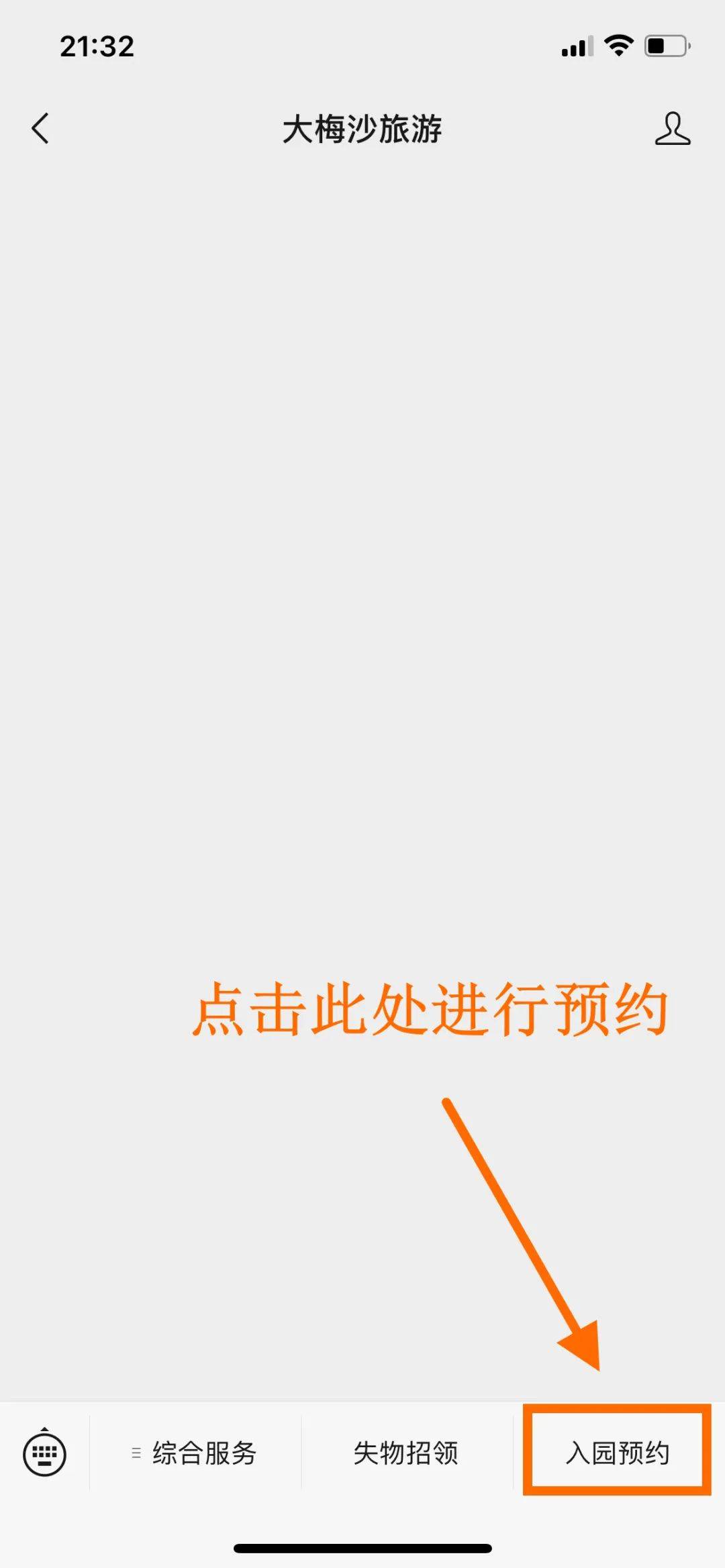本文经授权转载自看天下实验室
原标题:上网课的留学生们:被疫情偷走的时间
撰文 | 杨雯
编辑 | 谌彦辉
运营 | 屈昕雨
嗨,欢迎关注看天下实验室!《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人的一生都在成长,一起去过有趣而丰盈的人生。
比起对理想的哀叹,对未来的焦灼更加困扰着留学生们。
杜薇从沉睡中缓缓醒来,她睁开眼睛,伸手摸向床头的手机,看了一眼上面的时间——下午1点。又是一觉睡到午后,接连好几天,甚至这几个月来,她都是这样子。但杜薇并没有因为睡太久而头昏脑胀,因为她在凌晨5点才入睡,刚好完成了8小时的睡眠。
起床后,杜薇一边想着,今天无论如何都要看完老师新上传的网课,一边又打开了刚更新的电视剧。下午的时间倏忽一下溜走了,当杜薇从精彩的剧情中回过神时,已经到了晚饭时间。
晚饭后,杜薇终于打开了学校的网页,此刻时钟指向8点,夜幕已经降临在杜薇所在的城市。她再次对自己的拖延感到愧疚和焦虑,但为了完成今天的学业,她不得不再次奋战到凌晨5点,完成又一个生物钟闭环。
杜薇是伦敦一所大学数学与统计专业的大二学生,如果疫情没有袭来,4月的这一天,晚上8点,20岁的她此时应该沐浴在伦敦尚未沉下的夕阳中。从学校出发,只需半小时搭地铁就能到达剧场云集的伦敦西区,饱览世界级的文化盛宴。
这是杜薇在2019年曾期待过的。那一年9月,杜薇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留英前的预科,那时的她健康且有活力,一边抱怨着早上8点就上课,一边以此要求自己绝不晚于凌晨2点睡觉。
这种充实的生活与对未来的期盼都在半年后化为泡影。2020年的春天,预科的课程率先转到线上,杜薇没能从家乡回到北京的宿舍,她开始“家里蹲”上网课,却不想这一蹲,就蹲到了现在。
01
网课上到第三年
疫情席卷全球之初,在各国政府的防控政策下,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要求教师和学生以网课继续教学活动。两年过去,许多大学还保留着线上授课,但相对最初的网课形式已发生了许多变化。首先恢复线下教学的是Lab(实验课)这样依赖实地设备的课程,然后是小规模十几人的Tutorial或Seminar(研讨课),最后是几十到上百人聚集在阶梯教室里的Lecture(大课)。
翟可昕是2020年9月入读首尔一所大学的本科生,这一年8月,她接到了学校下学期将继续提供网课的邮件,于是决定先留在国内上网课。
2022年3月是翟可昕在国内上网课的第四个学期,学校提供线下课、线上课、混合课三种教学形式。
混合课是学校本学期针对课容量不能超过70人的防疫要求设置的新形式。选课的140人被分为两组进行每周论题,一半人出席线下课时,另一半人在线上看课堂的直播。
但因为人未到韩国,线下课与混合课都是翟可昕不能选的。翟可昕明显感觉到,学校越来越致力于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像自己这样的远程学生可选的课程越来越少了。选课时,她不仅要看授课是不是线上,还要确保考试也能线上,而这学期能满足这些条件的专业课仅占10%。
电影《阳光姐妹淘》
梁妍妍比翟可昕高一届,她亲身体验了学校这两年多以来对网课的探索。2020年疫情初期,学校采用Learning Acts线上教学,当时并没有直播课,所有的课程都由授课老师在课表时间前录制好上传。学生在Learning Acts上输入学校的名字,填进学号,就能反复观看。
但没有直播平台,讨论课也就无从谈起。讨论课本是梁妍妍读的政治与外交专业必不可少的一环,授课老师只好将Learning Acts开辟成论坛。学生在帖子里用文字唇枪舌剑,盖起一座尖锐又不失礼貌的“楼中楼”:“这位同学你好,我很开心阅读你写的内容,但是我有几点不同的意见,是一二三……”
到2020年下半年,依托Zoom和WebEx的直播课才开始在选课列表中出现。但更多的选择,也使不同老师的教学风格更加鲜明化。梁妍妍有许多课程与地缘政治、比较政治相关,在她的想象中,持不同立场的同学们在课上针锋相对地讨论是家常便饭,可现实是,课程是否精彩,很大程度上因教师而异。
很多老师风格沉闷,仍采用录播课,学生有问题时只能发电子邮件或在Learning Acts上留言。梁妍妍盯着屏幕中按照PPT照本宣科的老师,感觉他们只是一个个随着自己的点击,机械输出对应内容的AI。
可她在韩国留学的第一学期不是这样的氛围。时间倒流回到2019年9月,梁妍妍记得,那时不同肤色的面孔在教室里喧嚷着,课后总有许多人围上讲台向老师热烈地提问,那才是她心里大学的感觉。
这些生动的时刻,在网课中几乎消失殆尽了。课堂在空间维度上陷入虚拟与静止,甚至还有老师表示本学期使用的是上个学年的录像视频,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也一并消失。
留学生们已经适应逐渐怠惰的老师,甚至对枯燥乏味的网课也麻木了。姜心兰是澳大利亚一所大学会计与金融专业的学生,专业课通常是由老师讲解知识点和习题。开课最初,有老师觉得自己讲得太沉闷,想用提问来活跃气氛:“有没有谁开麦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在这门不强制要求开摄像头的课上,不出所料,几十个网格都漆黑沉默着,只剩下老师的屏幕孤零零地闪烁着。姜心兰也是躲在摄像头和麦克风关闭保护伞后的一员,她盯着屏幕上老师的神情由期待转向失望,最终无奈地说“好吧”,她心里一边尴尬,一边也悄悄舒了口气。
这样的场景出现几次后,老师便不再提问。对于那些提供录播、不考勤的直播课,到课程后期,许多学生也不再出席了。
02
一道屏幕隔开两种生活
对留学生而言,网课看似提供了许多便捷,无论身处天南海北,只要接上一根网线,在直播课开始前的一分钟点开链接,就能短暂地漂移时空,连结上世界另一头的知识与思想;当下课时刻来临,在老师的告别声中点下红叉,就又回到了可触可感的现实世界。
然而,人对生活状态更迭的感知,并非像按键就能开启、关闭那样简单清晰。如果说屏幕是分割虚拟课堂和现实生活的物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可能会在人的精神感知上,产生模糊甚至混淆。
韩国是一个重视女性妆容仪表的国家,留学时,梁妍妍会习惯在出门前精心将自己打扮一番。但当课程转到线上后,梁妍妍感到屏幕里外的自己是割裂的:要求开摄像头时她会戴上口罩和棒球帽,只露出一道眼妆;上衣会穿得大方得体,下身却套着睡裤或裹在被子里。
国内的留学生大多与家人同住,与家人空间的重叠会模糊学习与起居的界限,加剧网课生活的非正式感。梁妍妍和一大家子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常觉得自己只是“抽空上个课”——被打断成了家常便饭,要么是外公外婆敲门催她吃水果,要么有亲戚来串门。还有一次,梁妍妍正开着摄像头和麦克风声情并茂地进行作业发表,披头散发、睡眼惺忪的妈妈突然闪现在屏幕里,问她“宝贝你要吃早餐吗”,屏幕里的教授和同学都笑了起来。
这种双面生活的烦恼不限于上课时间,还一直蔓延到了日常生活之中。梁妍妍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身处中国和韩国双重时区,一个小时的时差虽使她不必像欧美留学生颠倒黑白上课,但也会提心吊胆。学校的作业通常截止在午夜11点59分,换算成北京时间是10点59分。压死线交作业的学生非常容易忽略时差,但学校不会接受搞混时差的申诉,“这属于低级错误”。
杜薇明显地感觉到,随着网课时间的拉长,自己正滑向愈加懒散的深渊。念预科时,她习惯了被室友拉去图书馆,沉浸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不去玩手机;但在家里,她的自律性越来越差,白天控制不住看剧、弹琴的摸鱼念头,只能晚上逼自己熬更久的夜去补课,陷入恶性循环。
杜薇曾以为这种状态会是暂时的,但暂停键被疫情按下太久了,生活“回到正轨”的曙光迟迟未能出现。她不得不接受,囿于网课的“非常态”生活,已经成为了新的常态。
03
难以消解的孤独
互联网可以保证课程照样讲授,考试照样进行,但是想要与网线那头从未谋面的同学发展出深厚友谊,并不是一件易事。网课课堂是和同龄人产生交集的主要场所,但是留学生们发现,因为缺乏真实的接触,和课友的聊天框大多会最终定格在课程结业之时。
尽管一起上过很多节课,梁妍妍依然不知道屏幕小框里的同学身高多少,喜欢穿什么衣服,又有什么爱好。若在高中,即便是最不相熟的同学,至少在三年的朝夕相处中,她也记得那是一个爱穿裙子的长发女生,那又是一个爱踢足球的高个男生。但大学同学,逐渐在梁妍妍脑海里抽象成一个个只有姓名的“火柴人”。
有一次,爸爸问她,如果你毕业后去旅游,到北京,或到上海,你可以让谁带你去玩呢?梁妍妍无法回答,不要说认识了世界各地、全国各地的同学,她连省内的校友都不认识。
无法在网课大学交到新朋友的留学生们,只好继续从原本中学、邻里的社交圈里寻求同辈陪伴。但原来的社交圈并不总能如愿,沈嘉是香港一所大学的大四学生,他从中学起便去外地求学,本地朋友不多;加之香港和内地的假期时间不同,一月开学、五月放暑假的沈嘉在家上网课已一年半,他几乎没能遇到和自己时间吻合的朋友。2021年8月,听到学校将开线下课的消息,沈嘉赶回了香港,这才消解了他上网课积累起的自闭情绪。
但疫情期间留在国外的留学生,可能会遭遇更加严峻的心理问题。疫情之初,梁妍妍独居首尔,一整年的网课让她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这才在2021年3月回了国。
梁妍妍居住在首尔市中心一间15平方米的单间,房间有独立卫生间、厨房和洗衣机,但空间并不大,需要推动房间里的两个晾衣架才能走出门。这是房东专门为留学生改造的房型,原本这一层有许多这样的房间,但全球疫情暴发后,隔壁的留学生纷纷搬离。梁妍妍与房东的合同一直签到她2023年毕业,本着不想浪费房租的原则,她没有回国,成了这层唯一的住客。
这间屋子紧邻交通干线,时常在耳边响起的救护车声尖锐地刺激着梁妍妍的神经。她开始对防疫神经紧张,有意识地降低出门的频率。
偶尔有留在韩国的朋友相邀。有一次,在热闹相聚的一天后,梁妍妍坐在回程的公交车上,望着窗口掠过的万家灯火。她原本很喜欢首尔的璀璨夜景,但刹那间,一种孤独感从她的脚底窜上头顶,她蓦然意识到,这些灯光里没有一盏为自己而亮。
每次用钥匙打开家门,等待梁妍妍的只有黑洞洞静悄悄的屋子,和疲惫却不敢懈怠、要立刻用消毒液喷遍全身的紧张。
渐渐地,梁妍妍无法忍受这种从热闹到孤寂的巨大落差,她开始抗拒朋友的邀约,更不愿意出门,总是一连二十几天都闷在家中。
好几次,梁妍妍被救护车的急促声惊吓,她发觉自己出现了肢体反应,产生了极端的想法。她想要寻求学校的心理咨询,但没有排上号,便决定回国。现在,尽管和家人住在一起的日子更吵闹,学习更低效,但梁妍妍内心感到了安全。至少,她不必再走回那条昏暗寂静的楼道。
04
有人评估只吸收了
50%的知识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在疫情席卷之下,本该与朋友漫步异国街头的金色青春,成了网课留学生可望不可即的生活。
尽管疫情让人们的生活与心境陷入缓慢、甚至停摆,但学校的决策让留学生们无法逃避,不得不卷入糟糕的现实之中。
翟可昕的大学对韩语成绩的录取标准很高,曾经有学姐连续考了三年语言才被录取。名列前茅的翟可昕是高中班上最早通过考试的人之一,在疫情前她就叩响了学校的大门。但疫情来临后,由于语言考试迟迟不能恢复,各大学各自举办校考来代替。翟可昕发现,许多班上成绩普通的人也通过了校考,入学后,有些人只能说出 “你好”“谢谢”等韩语也成了自己的同学。
除了入学标准,对课程的考核标准也一降再降。学校原本对课程拿A和A+学生的比例是30%以内,B以上的是50%;现在则将A类调整到50%,B以上的达到70%,只有极度糟糕到作业不写、课也不上的学生才会挂科。
在这样的课堂上,翟可昕发现即使自己只付出百分之五六十的努力,就能够轻易地拿到高中时想都不敢想的奖学金。这并没有让翟可昕开心,反而感到无比荒唐。这所大学本是她执念就读的梦校,可她现在觉得不过如此。
日剧《垫底辣妹》
翟可昕从未曾踏进过她的学校,即便用学校的VR看校园,都难以在她的心头翻起波澜。屏幕那头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只有日复一日、平淡枯燥的网课才是她面对的现实。当初理想的知识殿堂是什么样子呢?她已经不记得了。
她正是世界上无数对学校感到失望的大学生的缩影。据2021年英国国家学生调查(The National Student Survey)显示,两年来,学生对网课的整体满意度正在日益降低,从2020年的83%下降到2021年的75%。其中,在学生会、学习社群、作业反馈等分项的满意率低于70%。
长时间经历时间与空间上的双面生活,学习效率的下滑成为一种必然。有留学生认为网课效率至少比线下低20%,甚至有人评估自己只吸收了50%的知识。
引发学生不满的另一大原因是依旧高昂的学费。2020年,有近30万英国大学生联名向政府请愿,以网课的低效体验、无法享受图书馆等资源发起退学费抗议。尽管英国教育大臣给出了应该向远程课学生提供学费折扣的回应,但大多数学校并未将减免学费提上日程。
05
重返校园
梁妍妍曾经畅想过她会如何度过大学四年。升学之前,梁妍妍的父母专门带她去韩国感受各个大学的风景。她的学校里种着许多银杏树,2018年的梁妍妍快乐地憧憬着,她成为大学生后,背着书包,怀里抱着书本,从一间教室匆忙奔跑到下一间教室的画面。小松鼠会跑得比她还快,金黄的银杏叶会穿过她的发梢。
到大三的时候,她要去国外交换,再学一门外语,甚至可以在Gap Year去其他国家走走看看。父母让她留学,是期望她可以开拓视野,看到不同于国内的风光与文化,可如今只剩下虚度。梁妍妍身边有两个中国留学生失望透顶,他们已经退学,打算再战国内高考。
比起对理想的哀叹,对未来的焦灼更加困扰着留学生们。翟可昕读的是韩语专业,但在缺少语言环境的两年里,她的口语正在急速退步,甚至已经差于高中能与韩语外教对话的时候。两年的网课已经逼近翟可昕容忍的极限,如果下学期还不能去留学,翟可昕宁可先休学,也不想再虚度。
电影《阳光姐妹淘》
梁妍妍对疫情和孤独仍抱有恐惧,但她也决意下学期再回到学校去。因为她即将升入大四,要开始着手准备研究生的申请,这意味着,她必须要拿到有分量的推荐信才能申请到好的学校。
但想在网课上给老师留下深刻印象并不容易。梁妍妍只能逼迫自己多选直播课,多主动发言,多写邮件刷存在感,而这些远比线下和老师交好劳心劳力。
沈嘉清楚地察觉到线上课、线下课和老师建立起的关系亲疏有别。不擅长网络社交的他干脆放弃了在线上努力社交的这条路。好在他回学校后,学校开启了双轨制教学,沈嘉最终凭借着大一、大四两位线下课老师的推荐信,拿到了理想的硕士offer。
那些尚未启程的留学生们则盼望着重返校园,但现实又使他们不敢抱有太多期待。留学生早已习惯了一切突然的变化,习惯了航班被取消,习惯了教学计划调整,他们只能在且行且看中安慰自己。
疫情下,北半球的第三个夏天就要来了,而南半球的澳大利亚还要再等上半年。姜心兰的朋友圈里,有澳大利亚的同学在黄金海岸浮潜,呼唤她一起来考潜水证;还有人晒出了抱着考拉的照片,说别看它小小一只,抱起来非常沉。
姜心兰想要去浮潜,也想要抱抱考拉。如果她能顺利成行,那将会是她在澳洲度过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夏天。
* 文中留学生均为化名
疫情改变了太多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