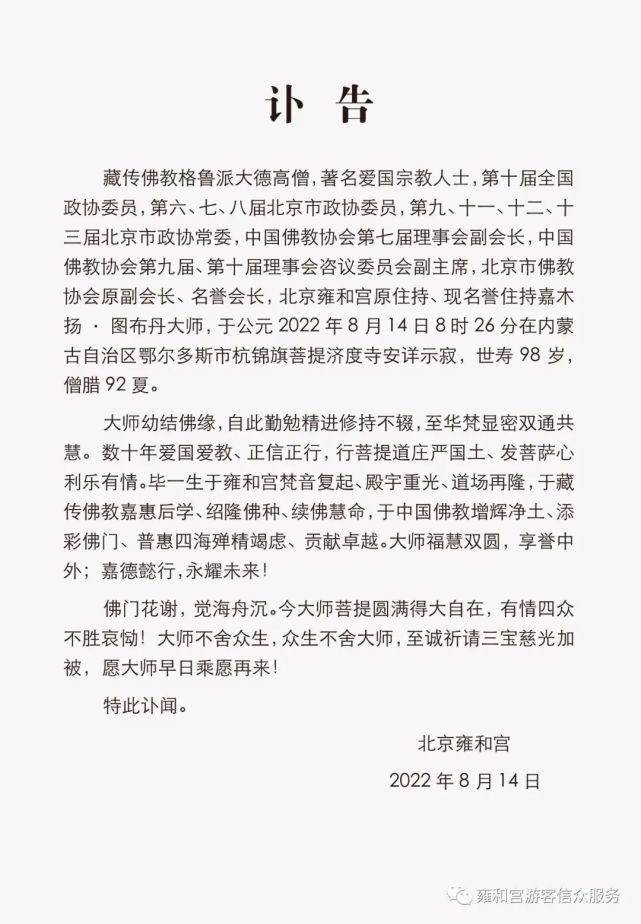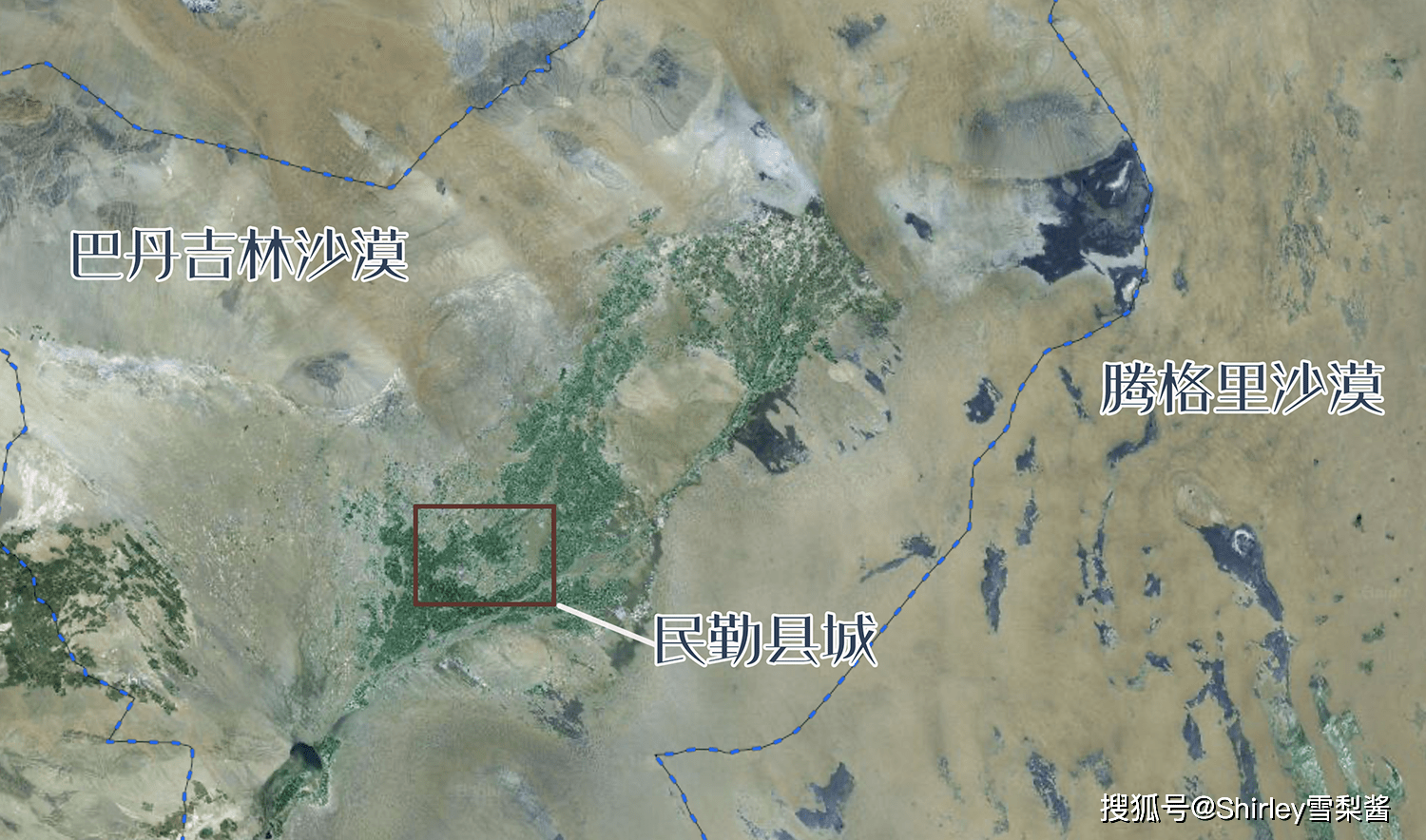文/严柏洪
老家双江口是宁乡的膏腴之地,鱼米之乡。属典型的平原地貌,阡陌纵横,沟渠交错,沃野无际。一层层金黄稻浪,一排排青瓦红砖房舍,从空中俯瞰,如同画在金黄底色上的五线谱。虽没有高山大川的险峻蜿蜒,但也十分的阔远广袤。
这样的地形地貌,注定不会有太多的飞禽走兽栖息藏身于此,除了鸟类外,其他野生动物十分稀少罕见。
小时候我们能见到的鸟类有:麻雀、山雀、喜鹊、乌鸦、翠鸟、八哥、斑鸠、董鸡婆、布谷鸟、大雁、燕子、猫头鹰等。
麻雀、山雀、八哥、斑鸠、燕子,常年能见到,感觉就像家禽一样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时时出现在身边。
猫头鹰不常见,秋收之后,田野里的田鼠出来活动觅食,失去了稻子的遮掩保护,成为猫头鹰猎杀的极好目标,这时才能一睹它的风采。
大雁是候鸟,并不在老家落脚歇息,雁群南飞,只是在迁徙的漫漫旅途中路过。每年深秋,听到声声雁叫,看到雁阵从我们头顶飞过,小伙伴们高兴不已,会仰起头,对着大雁高声呼喊:人字人字,竹篙竹篙。大雁就会按照我们的指挥,飞出“人”字和“一”字形阵形,仿佛它们能听懂我们的方言,我们就无比的开心快乐。其实,大雁迁徙就是有规律地变换着飞这两个队形。
到了芒种时节,几乎昼夜都能听到布谷鸟那洪亮、催人耕作的叫声:“布谷布谷,布谷布谷”。布谷鸟一叫,老家的人就要开始忙碌了。布谷鸟别名颇多,子规、伯劳、杜宇、杜鹃、啼血鸟,都是它充满诗情和意境的名字。
我们看到的布谷鸟体形大小和鸽子差不多,但比鸽子细长,暗灰色,腹部布满了横斑,飞行急速无声,悄无声息,不知道它从何方来,春天过后又飞往了何处。我们小孩子十分喜欢布谷鸟,跟着学它的叫声。手掌交叉合拢,形成一个内空,周边要压紧,不能跑气,两个大拇指横压在右手食指上,留出一个气孔,嘴对着气孔模仿布谷鸟叫声的节奏吹气,左手的四指随着节奏张合,发出的声音和布谷鸟的非常相似。我们一群年龄相仿的发小,悄悄走到布谷鸟附近,屏住呼吸,它叫一声,我们学一声,布谷鸟以为又来了新同伴,叫声更加殷切。树上地上,人鸟呼应,相安共处,何其快乐。也有学得不像的,发出怪异的声音,把布谷鸟吓得飞走了,遭我们大笑。
禾苗快抽穗的时候,稻田里的董鸡婆开始出没,多了起来。因为董鸡婆生性机警,丰茂的禾苗利于它们藏身。董鸡婆是我们根据它的叫声起的名字,很形象,其实董鸡婆的学名就叫董鸡,也叫秧鸡,我们那时并不知道,这纯属是误打误撞,蒙中的。
夏日炎炎,阳光明艳,田野如茵,天高云淡。清风徐来,空气中飘散着稻花的清香和泥土的芬芳,稻田里四处传来董鸡婆富有节奏的鸣叫,像击鼓一样,一声一声,铿锵有力,干脆嘹亮,音色浑厚,叫声独特,不论大人、小孩,都知道这是董鸡婆在叫。“咯-咚”,“咯-咚”,“咯”音长,“咚”音短,飘扬在无垠的旷野上空,此起彼落,激越高亢,很远都能听到。有时只发“咚”音,数声连鸣,声声急迫,情意切切,那是董鸡婆在求偶,在热恋。
清晨和黄昏之时,薄雾弥漫,炊烟袅袅,是董鸡婆叫得最欢的时候,连同公鸡的打鸣、水牛的长哞和鸟儿叽叽喳喳的欢唱,构成了乡村最动听、最天籁、最温馨、最和谐的自然乐章,似乎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董鸡婆大都是单独或成对出来活动,极少见到成群结队。它们通常匿藏在稻田或草丛中,在浅水中觅食,站立姿势挺拔,飞行时颈部伸直,善于涉水行走和游泳,行走时尾巴翘起,头前后点动,动作可爱又可笑。当然,这只是在远处偶尔看到,隔近了,董鸡婆会马上躲起来。
我们行走在田埂上时,不小心惊动了藏在禾苗中的董鸡婆,突听得“嘭”的一声,董鸡婆受惊急速飞起,又迅即落入不远处的稻田里,动作快得连董鸡婆的影子都看不清,把我们吓了一大跳。起飞的一定是董鸡爸爸,它们在孵化小董,或是小董们已经出生了,一家子正其乐融融,董鸡爸爸起飞是为了转移入侵者的注意力,保护它的爱妻和孩子们。
董鸡婆喜欢吃绿色植物的嫩枝、蠕虫、蚱蜢、蜘蛛、水生昆虫及其幼虫,特别爱吃螟蛾蛹、稻灰虱幼虫、稻蝗、蝼蛄、稻椿象等水稻害虫,是益鸟,是水稻的护士,深得农民的喜爱。
家乡的爬行动物大概就只有蛇和乌龟了。蛇类有水蛇、五步蛇、红肚皮、菜花蛇几种。菜花蛇我们叫它屋场蛇,体型较大,无毒,也不咬人,家家户户屋里都有一条,它是守屋的,盘旋、巡视于阁楼之上,是老鼠的天敌,只要它在上面守着,老鼠就明显地老实了很多,否则,追逐、打架、尖叫,不得安生。我们把菜花蛇当作家里的成员对待,和睦相处,它可以自在来往,绝不会有人伤害它。
那时的乌龟真是多,一到夏天,它们纷纷趴在池塘横斜的柳树上歇息乘凉,往往是乌龟妈妈带着一群小崽崽,看上去十分的惬意。它们很安全,生命无忧,因为老家没人吃乌龟。我有时故意蹬柳树一脚,乌龟受到惊吓,落入池塘,好像是小伙伴之间玩恶作剧一般。
前几天在步行上班路上,走到长沙地铁2号线金星路站附近,突听到几声喜鹊鸣叫,我连忙四处找寻,最后在旁边的一根高杆广场照明路灯顶上发现了喜鹊的窝,喜鹊妈妈站在窝边,几个小脑袋伸出来,喜鹊妈妈在喂它的孩子们。我掩不住内心的兴奋,赶紧拿出手机拍照,可是太高了,拍不清晰。喂完孩子,喜鹊妈妈又飞走了。
喜鹊的出现,一下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儿时的家乡,莫名地想念布谷鸟、董鸡婆、乌鸦的叫声,想念憨态的乌龟,想念呆头呆脑却又身手敏捷的猫头鹰,想念老屋里那条忽隐忽现的屋场蛇,这些自然界可爱的精灵,如今都难觅踪影。我到底有多少年没看到过它们了?它们到底是什么时候从我们眼前消失的?为什么会消失?它们去了哪里?似乎都不得而知,找不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