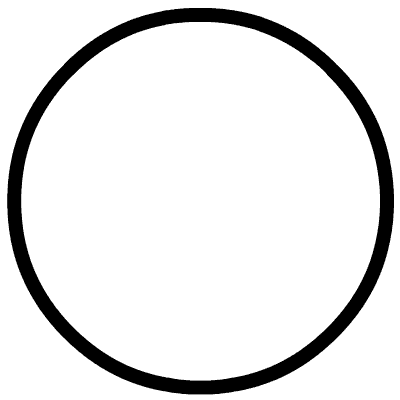一
西安的北教场与教场门实际上是同一条街巷,把猫叫咧个咪。
北教场东起红埠街,西至马神庙巷(今劳武巷)南口,在隋唐长安皇城承天门前第一横街西边。唐末以皇城改筑为新城后逐渐形成街巷,元代这里为秦川驿。
北教场,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马路南边为居民院,马路北是一片有土围墙的大空地,老百姓称营盘,驻有部队,属明清时北教场操场旧址。拐向东北处有一条南北向的半截巷子,也叫教场巷。《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载:“清初沿明代教场建有抚标教场,得名教场门。向北折小巷,称教场巷。”北教场与教场门拓建时间不详,民国二十一年(1932)《西安市区域全图》始见显示。
我就出生于教场巷21号。我姑妈家住营盘正对面的北教场5号,所以对这一带小街小巷布局很清楚。记得五十年代中,我到姑妈家,晚上曾进营盘看过露天电影,好像演的是反映黑旗军的《宋景诗》。还记得那时北教场营盘门前路很宽很平整,是铺了石子的路,比西安市中心的东西南北四大街路还宽,亦有人称之为广场。
北教场巷的街名源于这里明代就建有的演武教场,明末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曾在此检阅过军队,是清初沿用的明代教场改建成的抚标校场。抚标是清代巡抚所直辖的军队;教场即操练和检阅军队的场地。因西安城墙内南边冰窖巷有西安总兵所辖绿营兵操练和检阅的场所“镇标校场”,与府城西北的“抚标校场”分处城南、城北,所以它们分别被称为南、北校场。
《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衙署考》:“北校场即抚标校场,在万寿宫东,三营校阅之所,储藏旧式枪弹火器。”北校场后来被叫成北教场,一是“校”与“教”有时同音,二是两个字义相近互通,在很多情况下还是一致的。“校”有军训、习武、军营、营垒、演武场、考核、检阅、军队职衔校尉的意思,“校场” 即古时比武之地。唐•李濯《内人马伎赋》:“人矜绰约之貌,马走流离之血,始争锋于校场,遽写鞚于金埒。”校场是争锋较艺的地方。“教”旧时操练和检阅军队的场地。唐代杨巨源《赠邻家老将》诗:“拂雪陈师祭,冲风立教场。”
北教场不光是练兵场还建有军校,光绪三十年(1904),在北教场创建陆军中学堂。宣统二年(1910)改为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合立的陆军中学堂。应该是为了充分发挥教场的功能。
教场西北边有习武园,也叫西武园,《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衙署考》:“习武园,即演武场,巡抚循例大阅之所,在万寿宫西北。历科武闱乡试校士亦在此,科举停,遂专为校阅地。”
其实,今北教场和西武园都称教场,不过,分为东西坊而已。《明清西安词典》中载 “教场东西坊”为清中后期西安城坊名。还载:“府城西北隅有两处抚标教场。一在洒金桥北段路东今教场门、劳武巷一带,疑为‘教场东坊’。一在府城西北角,俗称北教场,亦名西武园,疑为‘教场西坊’。或此,北教场分为东西坊。”
北教场北边青年路止园一带,清光绪年间还是一位程姓武官建的军马场。看来,这一片地域应是明清时西安的军事重镇!
左一儿童时的朱文杰与姑妈家的表哥、表姐 1952年摄
二
北教场南边与西仓交会,西边与马神庙巷(今劳武巷)相连,这里原有一株古槐树,槐树下有个铁香炉,因而北教场这一带历史上曾被称为铁炉坊。1966年曾改名为红卫街,1972年恢复原名。
马神庙巷位于今莲湖路南侧,西至老关庙街(或洒金桥)。《明清西安词典》称:明清时为长安县领城内西北路教场东西坊属巷,……西起洒金桥,东接北教场门,巷内因有马神庙而得名。民国二十一年(1932)《西安市区域全图》、二十四年(1935)《西安市区图》和二十八年(1939)《西安市现有道路交通图》中,民国教场门亦并入马神庙巷。看来,在民国年间,两巷实为一体,教场门归到马神庙巷了。《莲湖区志》“劳武巷”一条中还记载:“隋朝前,这一带名杨兴村,是隋唐长安城建城以前唯一可知的村落。”
无独有偶,我去江苏扬州,发现扬州古城也有一条老街叫教场街,与之相邻也是马神庙,和西安类似。我猜想,教场训练有骑兵马队,附近有军马场或养马场,才设有祭拜马神的马神庙。当然,紧挨北教场巷南边有西仓(永丰仓),运送粮食的马车平时川流不息,马车主人也是要敬马神的。
我四五岁时,从北教场巷搬到北马道的神器库巷,再到北教场我姑妈家玩,就要走几条巷子。从香米园、洒金桥进马神庙巷,朝南拐个弯就到了。其中,马神庙巷住有我文学上的好朋友徐志忻,笔名子心。他和我姑妈家的表姐张建洁是中专同学。大学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中文系,1997年7月到2004年时,是陕西省作协机关刊物《延河》执行主编。他擅长写小说,著有反映老西安的长篇小说《黄色》。记得他给我说过,当马神庙巷(劳武巷)祖上几辈辈留下来的老宅院要拆时,他回去站在门楼里扶着门柱子任泪水横流,大哭了一场。他祖上曾是清代举人,家学渊源深厚。子心对生养自己的这处老院子感情太深了,以至于被拆后,过了两三年给我诉说时,竟哽咽着说不下去。
2015年1月18日在《西安晚报》发表阿今文章《马神庙巷的记忆》,文中提到杨虎城将军的弟弟杨茂三曾在马神庙巷居住过,他的儿子杨拯湘还和阿今是青年路小学的同学。
胡家鼐老师
劳武巷是“文化革命”时改的名。现今劳武巷15号,就是马神庙巷小学的旧址,也是早已消失的马神庙遗址。马神庙巷小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并入许士庙街小学,成为许士庙街小学分校。“文革”后,马神庙巷小学改名为劳武巷小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劳武巷最有名的是劳武巷小学文艺宣传队。我在东西甜水井小学的老师胡家鼐曾调这所小学任过一段音乐教师,后成为西安市青少年宫负责宣传的干部。在我眼中胡老师就是个音乐天才。
胡老师是音乐家刘炽的学生。他说,1974年刘炽老师收我为学生,除了看了我的作品,认可我写的旋律外,主要是对儿童音乐创作的大力支持。后来,随着我常去刘炽处上课,他考我几个问题,我都回答到他的心上,足以证明我对他音乐作品的理解与无限热爱,最终我俩成为无话不谈的师生和朋友。当年,我和刘炽都不知道彼此在甜水井街三仙庙和私立甜小任教的经历,所以今天想来,我和刘炽老师的相识、相遇、相知,真是天缘!
胡老师还说,和刘炽老师有两件事成为我终身遗憾。一是刘老师曾提出要陪我观看电影《英雄儿女》,亲自为我讲解电影音乐的创作过程。只可惜那几天,偏偏西安没有上映这部电影。二是刘老师当年在西安止园招待所为电影《四渡赤水》谱曲。任务完成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王平等人从北京来接他,我也赶去送行。因时间紧,竟忘了合影留念。记得刘炽老师当时对我说,以后有机会来北京,让我给他带两斤教场门的饸饹,可惜当年我一直没机会赴京,让他老人家吃上教场门饸饹,以解思乡之情。
刘炽先生
我1970年在铜川市歌舞团工作,曾专门观看过劳武巷小学文艺宣传队的演出,后来团里还招收了几名从劳武巷小学毕业的舞蹈演员。其中一个叫何嘉敏,1978年后调到青海省歌舞团,九十年代中又调回宝鸡市歌舞团,担任舞蹈队队长。那年月除过部队文工团,西安的省、市文艺团体基本不进人。所以,铜川歌舞团招生,竞争特别的激烈。
还有被聘为西安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的宗鸣安,出生于老马神庙巷,后改为劳武巷,门牌为45号。宗鸣安是西安地方史、老街巷的研究专家,供职于西安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任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古藉碑帖专业委员会主任。出版有《西安旧事》《金文考说》《龙旗下的长安》《汉代文字研究与欣赏》《碑帖收藏与研究》《长安节令与旧俗》《长安骨董客》等十多部专著。
他的家是一个偏开门的四合院形式,院中花草树木甚多,而房间并不多,这个安静的独家小院就是他儿时生活与学习的地方。他告诉我:马神庙巷,是一个充满了文化气息的街巷。清末民初画家祝竹言在1号院,杨虎城之弟杨茂山在7号院,大古玩商白集五在10号院,辛亥老人景莘农在西巷口,作家徐子忻在中巷内40号院。
我与宗鸣安,2015年8月26日认识于西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召开的编辑《西安老故事》一书的组稿会上,后来又一起参加了在西关八家巷莲湖区文化馆召开的首发式。我们俩同为《西安老故事》一书的编委会成员,我俩加上商子雍先生,分别有十余篇作品被收入书中,占了全书五十五篇的多一半。以后来往增多,经常在有关开发西安的研讨会上见面,遂成为朋友。例如:西安规划研究院有关开发提升冰窖巷文化品质的研讨会和《东大街上的吃货》一书的编辑座谈会上。
三
我出生地的北教场巷,今已消失,我家的老院子原址上盖了三座高层住宅楼,门朝许士庙街开,一座是陕西省能源中心办公大楼,一座是宿舍楼。
北教场的中心营盘位置,七八十年代,这里是西安警备区招待所,南边一部分盖上了二层单元楼,成为陕西省军区干休所,还有西安市广播电台家属院。陕西省邮电局也迁到这里西北边直通莲湖路的一条小巷内。后来省邮电局的院子又成了省邮电医院,地址为劳武巷1号。
我集邮上的朋友曹彦,曾任未来出版社副总编、太白文艺出版社编审,我和曹彦相约一起编组邮集,参加了1983年在西安举办的陕西省首届集邮展览。他的父亲曹竹俭1980年至1986年任陕西省邮电局局长,我正好1985年在教场门37号的《长安》月刊上班。记得曹彦曾赠送我一枚“文革”编号邮票编7《严惩入侵之敌》的样票,还说是他父亲在国家邮电部开会带回来给他的。这枚未发行的样票自然很珍贵。
曹彦的父亲曹竹俭(1919~1997)河南偃师人。先后在晋察冀边区抗日政府、张家口晋察冀边区邮政管理局、华北人民政府邮政总局任科员、指导员、队长、视察员、副主任等职。1952年任邮电部干部司副司长。1961年至1966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经委企管局、基层局副局长、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77年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1980年任陕西省邮电管理局党组书记。1986年离休。1997年11月18日因病逝世,享年78岁。
西安警备区招待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曾是西安市文联租住的办公场所,文联下属的《长安》文学月刊在招待所二楼东边办公,是我经常去的地方。1981年前后《长安》杂志曾刊发过我写煤矿的一首诗《我是天轮》,和一篇小说《矿山传奇》,责任编辑商子雍还为我的小说写了一篇评论,配发在小说后边。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被人评论。记得我一次从铜川回西安到警备区招待所的《长安》编辑部来找商子雍、和谷两位谝闲传,中午他两位要请我吃饭,叫上贾平凹,我们一行四人,步行到南院门春发生吃葫芦头泡馍。又是酒又是菜,摆了一桌子。回想那年月,文人交往,纯真得一塌糊涂,他们几人当年的盛情,至今仔细想来,仍让我感动。
阴差阳错的是,我1985年元月从铜川调回西安,成了《长安》文学月刊的编辑,竟然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的北教场。在这里两年中,每当把这些联系在一起,就会有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
和谷在他写的《我说文杰》中有:“人生旅途,很难预料自己生存境地的变迁。就地域而言,文杰是地道的西安人,我是铜川的土著,在我们二十来岁时,彼此的栖息地作了一次交换对位。他去铜川就业,我到西安读书。我们换了故乡,做一个客居者。当然这是命运的安排,或者说,是命中注定的。后来能在一起共事,也是不浅的缘分。红火热闹过,尔后各奔东西,天各一方,也是缘分。”
当然,北教场、教场门是我的福地,是我人生又一个风云变幻而震荡,丰富多彩而美丽,最值得记忆的转折之地。而住西安警备区招待所的《长安》文学月刊社地址是教场门37号,说明教场门之名已代替了北教场巷。
朱文杰为西安市作协文学讲习班学员讲课
朱文杰(二排中)与西安市作协文学讲习班学生合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