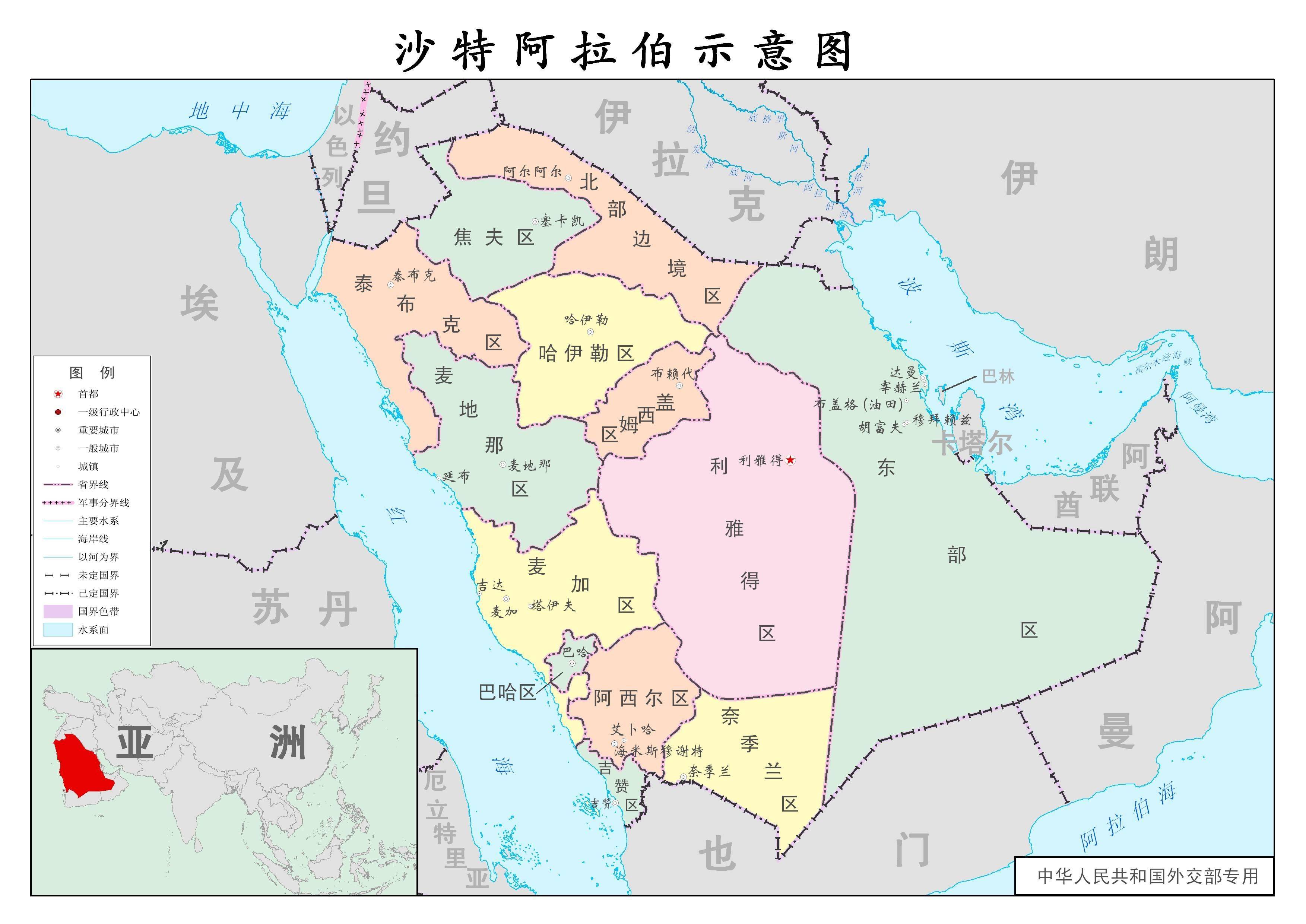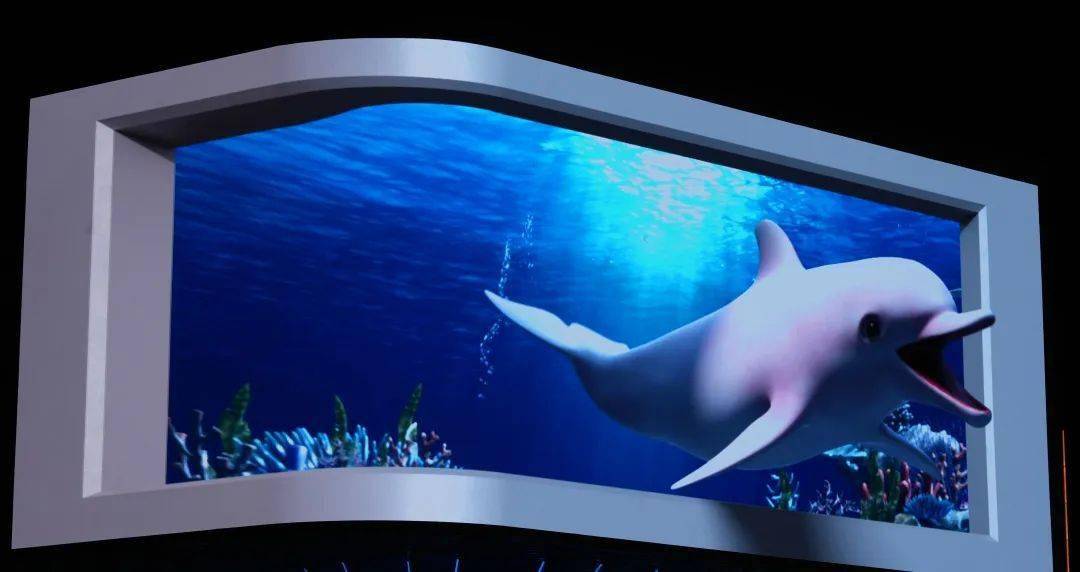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胡美英
我想去山丹,放一群马。马放南山,风吹草低,马儿的皮毛像雪山的粼片,闪动着丝绸的光亮,山丹大地如土佛寺里的金佛般安详。
那些马儿,原本就是一群载着骠骑将军霍去病射向祁连的箭矢!那时的它们,在公元前121年的春天里奔跑,马鬃飞扬,棕红如血。那是怎样的一种浊浪排空、壮怀激烈?
曾经两上山丹,都是草原最美的季节。
第一次去的时候,和同事们坐着大巴车在草原中迷失了方向,先是从西向东,后又从东折向西,兜兜转转跑了几个小时。青色的草丛间,杂色花儿七彩的笑脸,仿佛一下子将我们带到了天边,又像是来到了地心的深处。那时的我刚从南方来,草原的辽远是我心中行走的天涯:“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这是生长于水乡深处的我,曾经多少次向往的诗词里的景象,可第一次见到辽阔的草原,还没看到盛唐诗人韦应物这《调笑令·胡马》里迷路的马群,我们却先迷失在草原之中。
再次去山丹的时候直奔焉支山,坐在野花摇曳的焉支山坡,看草甸从山脚一浪一浪地铺向祁连山边,有大江大河奔涌的声音,轰轰隆隆地滑过耳际。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摇曳的水花,在大地上漫延。其实,草木本就是一种有根的水,它们以生长的姿势,漫延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我遥想的当儿,忽然有硕大的马群从草坡上漫过来,狂暴如雪,如我想象里的那群汗血马,鸟儿般飞落于草甸之上,时而仰天长啸、飞奔如矢,时而低头觅食、静如处子,它们静静伫立远望的表情,像想起它们祖先所向披靡的豪迈。突然觉得,它们就是一群扇着青草般羽翼的鸟儿,从古时西域飞来。它们飞翔在西北落日的余晖里,追逐着祖先的谣唱和弯刀,如时光里的精灵,让每一朵云絮、每一滴鸟鸣都泛出青草的味道——西北大地,是一匹从佛窟里飞奔而来的汗血马啊!环山的雾霭笼过来,山丹的每一棵水草里都住着神灵。
山丹,这块秦时月氏地、汉时匈奴国、中国最大的牧马场,汉初养马30万匹,北魏的草地上遍布着200万匹马、100万峰骆驼以及无数的牛羊,盛唐时期70万匹马儿在草原上游牧生息,大明和清道光年间也养马数万……水草,水草,有水才有草呢!也许是在雨里长大的缘故,置身这数十万顷青草繁茂之地,我不禁估摸起该要多少祁连雪水,才能供养得起这一泻千里的草色波涛!
我知道,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山丹,处于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的合围之中,是石羊河水系和黑河水系的分水岭,属甘肃省最干旱缺水县份之一。历代文人墨客多有对山丹缺水情状的描述。清代许乃谷说“流沙沙强弱水弱,峡口况无水一勺。只仗冬春冰雪积,五月消融灌阡陌”,“弱水”即指山丹的母亲河山丹河。有资料说,山丹河从青海穿祁连山而来,顽强地穿越绿洲、戈壁、沙漠、盐泽,一点一滴地渗入山丹的土地,滋养了焉支山,造就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山丹军马场。
曾于最酷热的天气里,去看过山丹河的上游马营河,那时的河里竟找不到一滴水的影子,那些马群样拼命朝上攀爬的河岸,让人首先想到的是渴死的群马,而不是灌溉出始建于汉朝、中兴于唐明的马营河灌区的那条河流。从古时的“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到汉武帝开浚河渠、引水灌田,再到明清、民国时期的修渠记载,山丹人民从古至今,一直走在节水、惜水、造水的艰辛路上。如今的山丹县,已有八座中小型水库和三十余座塘坝,众多矿泉水品牌产品也游走天下。缺水的山丹,将冰雪的清凉送进了我们的生活。那是山丹人民用三年时间修一条三十公里水渠、两三代人修一座水库的艰苦奋斗换来的;缺水的山丹,用如水的深情,养育着飞奔的骏马、青翠的草地。
人,其实是一种沿河迁居的动物。一方地域如果没有了河流,也就没有了人烟。在这方数十万顷的草原之上,腾跃的其实是一条河流的走向。
每次乘列车东行,必经山丹。从列车奔驰的窗口望出去,那时多半正是夜色沉沉,昏黄的灯光沿着长城的方向漫过来,像路过一个有老祖母居住的村落。村庄旁,安静的山丹河轻轻地绕村流淌,老祖母脸上城墙色的皱纹,在烟火的映照下,让人在寒冷的冬夜心生温暖。而坐汽车路过山丹的时候,总能看到骆驼样静卧的长城,在阳光下闪耀着时光的斑点,仿佛那视野的深处,有一群身披水色的驼群,沿着长城的方向踢踏而来,搅起漫天云彩。
从某种意义上说,山丹更像一座守护在汉明长城旁的村落,一头连着苍茫的远古,连着那些“衣皮革,被谢裘,住毡帐”的游牧祖先;一头连着瞬息万变的高铁时代,让时光系上了高铁的翅膀,在西北的天空下展翅翱翔。
在山丹,还应该有一座钟声清亮如雨滴的教堂,教堂里一定安放着那个叫艾黎的新西兰老人的灵魂,他的身上,有土豆和油灯的烙印,有山丹马纵横驰骋的烙印。想象着他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对山丹的诉说,那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丝绸之路上的风土人情、山丹周边的长城烽燧驼队铃声的一往情深。他先后在山丹办起的汽车运输、发电、造纸、陶瓷、玻璃、煤矿等近30个小型工厂或作坊,成为助力山丹大地发展的种子,沐浴风雨生根发芽。这位老人,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在长城边一住就是许多年。生前曾七次返回山丹,终老后又安眠于山丹大地。在我的脑海里,这样一些人,总是和长城交织在一起的;这样一些村落,总是融进了不朽的长城精神,成为人类精神的故乡。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北考察时,还专程去看望了培黎学校的孩子们,对他们寄予殷切的期望。
绵延在山丹境内近百公里的汉明长城,像一本历史的经书,让每一个走近它的人,都能嗅到书页翻动的气息。我渴望去草原深处放一群马,像无数的古人,在大西部空阔的山川中游走。如果有一天,我用我草色的歌喉,唱着“我用我自己的流浪,换一个在你心里放马的地方,像那游牧的人们一样,把寂寞忧伤都赶到天上……”的歌儿,来开始我的“游牧时光”,山丹一定是我出发的地方:从大草场出发,向西再向西,叩拜大地,向所遇见的每一朵花儿问好,听山川和河流像山丹的风儿一样欢笑;从大草场出发,将马儿赶进沙漠,让它们去经风历雨、搏击风暴,承接长途迁徙的历练;从大草场出发,将马儿赶进雪山,历尽风寒,在艰难的行进里去追赶春天……我的那一群山丹马啊,驮得起小鸟的啁鸣,更能驰骋疆场、翻越万里关山!我更要把它们赶到长城旁,像那个拍摄山丹长城20多年的摄影家陈淮老师,终日守护、奔走在长城边,守护成长城边的一团团草棵、一堆堆雪垛,融入山丹这方古老的土地,不悲不喜,有阳光的照耀就好,听得见雨水划过燕麦草的声音就好……
山丹,有大草原的苍茫,有万马奔腾的野性,有弱水长流的温婉,有野花青草漫漫流淌的柔情。走在山丹的雨天里,雨丝滑过脸颊,感觉它一会儿像刚出世的小马驹活蹦乱跳,一会儿又沉寂如苍穹,跳动着千年不老的历史脉搏……
“你住长城头,我住长城尾。”美丽的山丹,如嘉峪关东头的一个长城驿站,横贯古今;山丹草原,更像河西走廊上一枚无涯的肺叶,释放青绿的氧气滋养着苍茫的河西高原。如今,我可以坐着高铁去看我的那群心心念念的马儿啦……(作者:胡美英,系甘肃嘉峪关市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