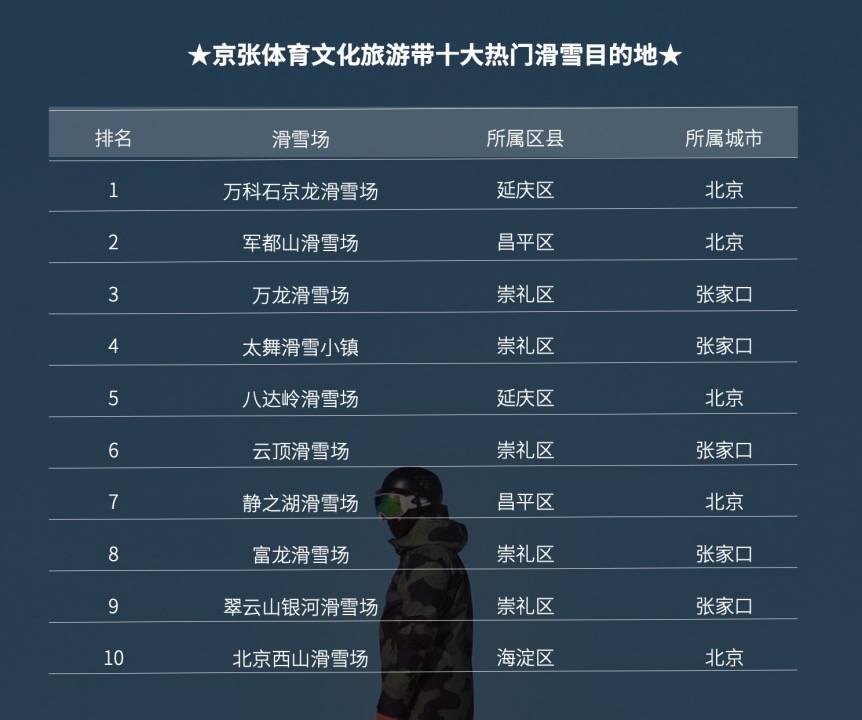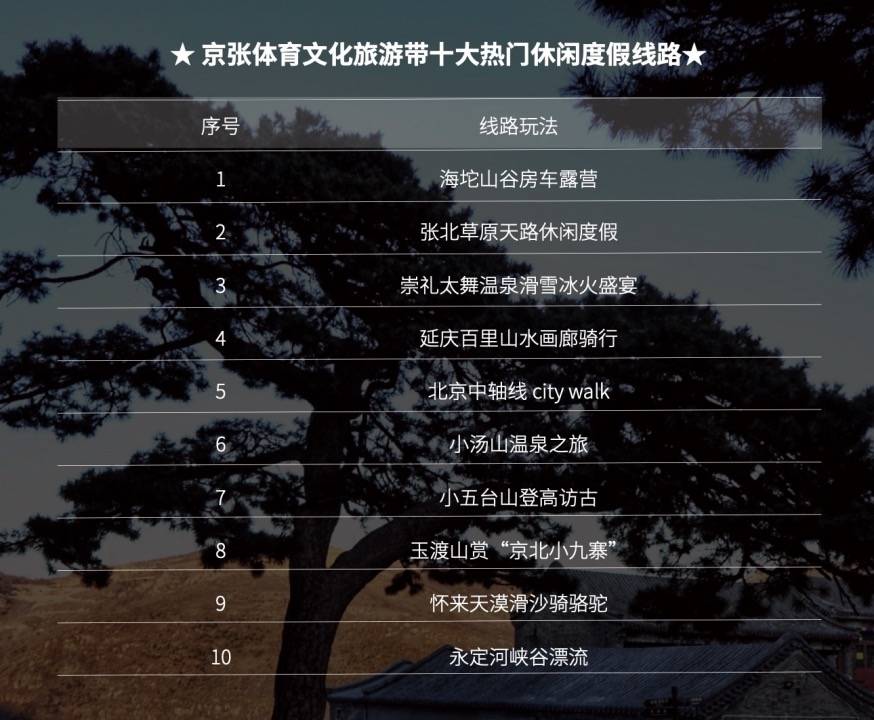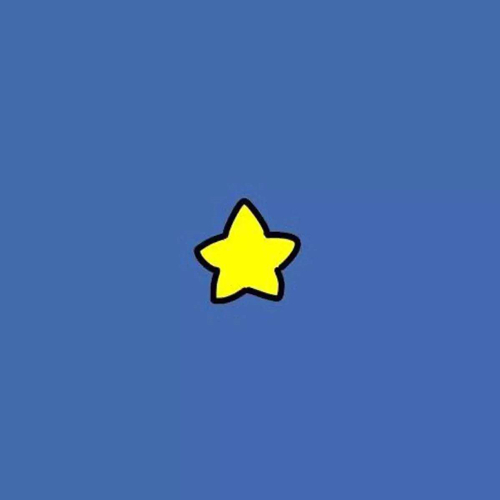阅读是精神的行走,行走是另一种阅读。
盛夏,不管是居家的一杯茶、几缕风,还是旅行中的几处山水、一两人家,阅读,可以让你与作者一起神游,也可以让你更沉浸在旅途。
本期,我们邀请到莫言与阿来,看他们笔下的文学,经由途经的地理,构成我们这个夏日的一次读行。
前不久,莫言回了一趟故乡山东高密,“在故乡土地上,驾驶着我们高密农机厂生产的大型收割机,收割小麦,这是亩产1600斤的高产田。这样的大型农业机械,这样的大片土地,这样的滚滚麦浪,这样的丰收景象,让我心潮澎湃。”
今年,莫言最近出版了《莫言的奇奇怪怪故事集》,他说,“我出生在一个闭塞的乡村,每到夜晚,村子里便一片漆黑,老人们便给我们讲妖精和鬼怪的故事。老人们说得煞有介事,我也就信以为真。这些故事既让我感到恐惧,又让我感到兴奋。越听越怕,越怕越想听。”
故乡,成为了莫言故事的源头。临近青岛,在胶莱平原之上,这里是莫言文学的故乡。
缘起·初到
看过不少莫言的作品,与莫言打交道多次,但直到他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年,我才第一次去高密——那是9月,他还没得奖,但是获奖热门。我想,无论莫言是否获奖,我都是免不了要去一趟的,不如早去。
这座神秘而魔幻的村庄,自从第一次出现在小说《白狗秋千架》中后,就与《红高粱家族》《檀香刑》《丰乳肥臀》《蛙》《生死疲劳》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它暗含着什么奥秘,能够给莫言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第一天飞青岛,再坐车到高密。第二天,出发去东北乡,出租车师傅告诉我,高密大栏乡平安庄,准确来说这才是莫言的故乡,车向故乡疾驰而去。
道路两旁的白杨树刷刷地倒退,叶子在阳光下招摇。一望无际的田野,成片的玉米地里,头上裹着头巾的农妇在埋头干活,皮肤黝黑的汉子蹲在马路边抽着旱烟。
我趴在车窗上,四处搜索属于“红高粱”的印记。但只有一垛一垛垒在一起稻草模样的东西。
“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红高粱家族》
后来,在莫言获诺奖的第二年,周迅主演的《红高粱》电视剧开拍了,当地要打造红高粱旅游王国,无数记者受邀前去,那次我终于看到了成熟的红高粱,一望无际,沾满露水柔韧的叶片,和它沉甸甸的头颅。
“随着车辆驶进村庄,那些寂静的文字瞬间被激活了,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红高粱家族》
那些在南方城市不曾见过的天高云阔,宽广又荒凉的土地,明晃晃的阳光……冲击着我,陌生、新奇,而又似曾相识。
大河·童年
一条宽广的河流无声流淌着。
这是胶河。站在高高的河堤上,干裂的风把脸吹得生痛,吹得一旁的芦苇东倒西歪,吹得树叶哗啦啦作响。莫言的二哥管谟欣指着堤坝下的一间矮旧的土房说,这就是莫言的童年。
二哥推开摇摇欲坠的木门,院落的一个石磨已被杂草淹没。进入房间,破败不堪,满是灰尘的木桌上放着满是灰尘的海燕牌收音机。
里屋有一个炕,上面叠着很脏的被子。二哥说,莫言就是在这里出生,并开启了他充满饥饿、孤独的童年时代,莫言曾吃过煤块,并在脑海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煤香。
在里屋内站着,我注意到炕上的窗户被封起来了,窗户本来正对着河堤,儿时的莫言就是趴在这扇窗户上,看胶河泛滥时,滔天的激浪,河水滚滚东去,堤岸上随风摇曳的野草,野草里飞舞的夏蜢和秋虫,听田野的蛙鸣。
家人·故事
快到晌午了,莫言的二哥骑着一辆老式自行车领我们去他家里,经过村落,砖瓦搭建的平房门口,铺满丰收的玉米棒子,莫言《红高粱家族》中除了大红色,另外一种鲜明的颜色便是这些成片的金黄色,这些金灿灿的光芒倒映出了黝黑又流淌着汗水的脸。
离开了莫言二哥的家,我继续去找莫言笔下人物的原型。莫言说过,他的爷爷、三爷爷、大爷爷都是传奇故事,他调查过,这个村子里每一户人都镶嵌着传奇的色彩。
莫言的《蛙》中的主角姑姑就是以他姑姑为原型,我到了他姑姑家,姑姑正在包饺子,她手脚麻利,说话爽快,和书中的姑姑相差无几,书中的姑姑从事了50年的农村妇科医生的职业,而莫言的姑姑也是一个妇科医生。姑姑说,莫言为了写《蛙》,经常找她聊天。
看来,这个村子的历史,一草一木,每家每户茶余饭后的谈资,都是为莫言的创作而生。
那天,我坐车离开村庄,道路延伸到远方的地平线,两旁笔直的白杨树,落日挂在树梢边,《红高粱家族》的画面再次浮现。要说哪一位作家身上有故乡的烙印,莫言一定是最突出的一位。
很快,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高密东北乡”不再是过去的模样,其实,早就不是了。但文学的故乡会永远存在的。
(文/陈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