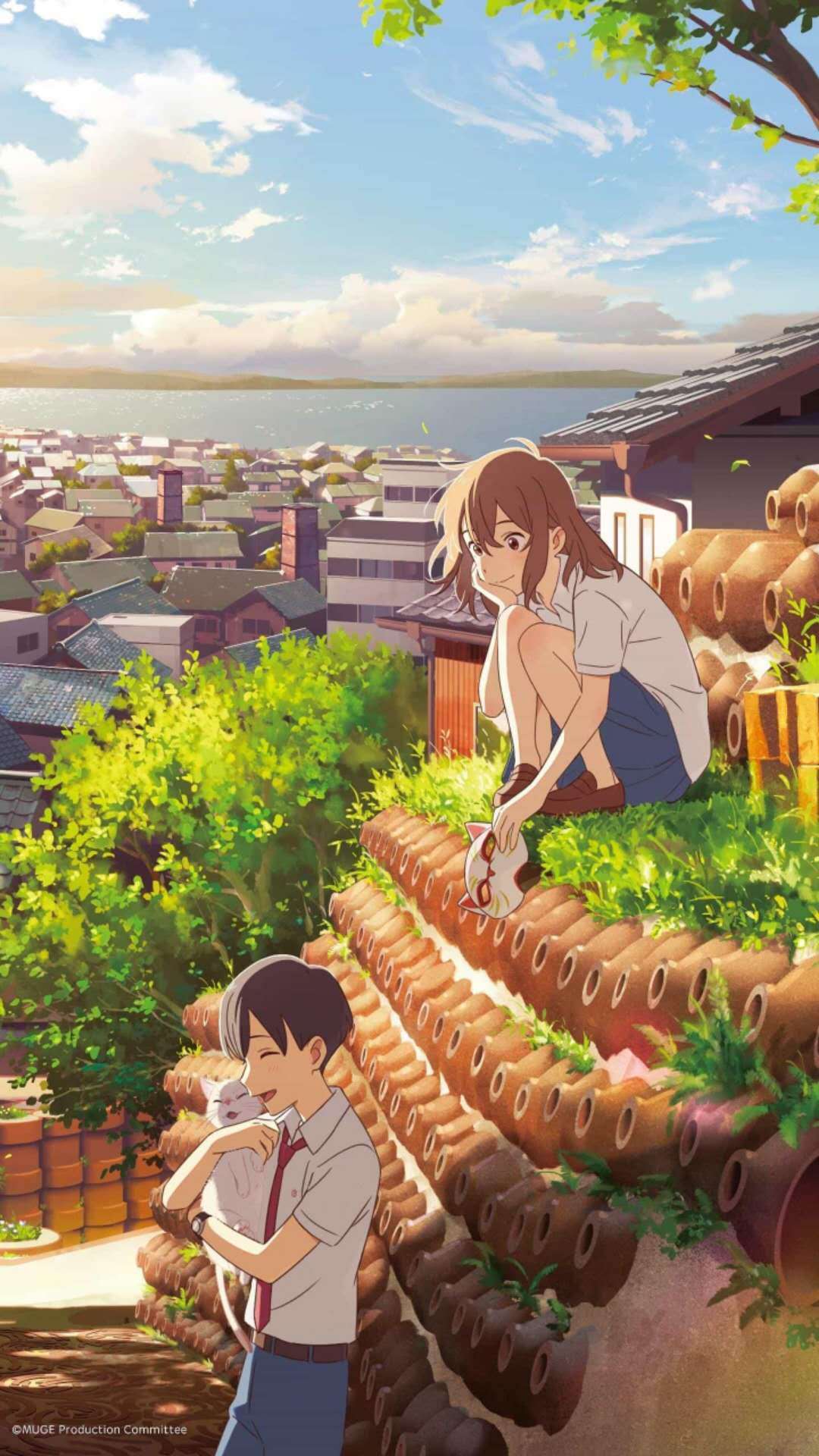“大卢舍那像龛”是龙门石窟开凿规模最大的摩崖像龛,也是龙门唐代雕刻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然而千百年来,渗漏水及危岩体,一直是威胁此地文物安全的主要病害。
去年12月份,奉先寺渗漏水治理与危岩体加固保护工程开始进行,工程范围从奉先寺底部至上部山体高度接近50米,宽度为70米左右。今年7月19日,工程通过了洛阳市文物局组织的竣工初步验收,较原计划提前了近俩月。
这次,距离上一次奉先寺大修已过去了整整50年。
7月24日,被绿网覆盖的奉先寺。
8月1日,整体保护工程完工后的奉先寺。
50年首次与卢舍那大佛近距离“对话”
越过东山的阳光,掠过伊河水面,照进西山的龙门石窟群。
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前的安全施工区域,数名工人垂直站在脚手架上,徒手拆卸传递木板钢管。随着笼罩大像龛的脚手架和绿网的拆除,卢舍那大佛逐渐显露真容。
为卢舍那大佛除尘的工人。
卢舍那大佛前拆除脚手架的工人。
千百年来,卢舍那大佛,以其“相好稀有、如月如日”的微笑,征服了海内外游客。
67岁的老石匠刘建设是龙门石窟研究院唯一一位两次参与奉先寺大修的保护者,17岁时跟着父亲参与了上一次的保护工程。在他的记忆中,那时的卢舍那大佛可以用惨烈来形容,头顶肉髻、身体都有窟窿,从发际线到下颌一条3-5厘米的裂隙贯穿左脸,左鼻翼和嘴唇各有缺失,右臂摇摇欲坠,而大像龛南壁西侧的天王像胸部雕刻崩落在地,需要吊装归位粘连。
在卢舍那大佛右侧胁侍普贤菩萨的右眼处,保留了完整的琉璃眼珠,呈暗绿色,质地均匀,熠熠生辉,左眼眼珠保留了外侧的一半。卢舍那大佛虽然双眼内没有眼珠,但从与普贤菩萨相似的喇叭状楔口,可以推断出在造像时也应有与普贤相似的眼睛结构。
考古发现,卢舍那大佛右侧胁侍普贤菩萨的右眼处,保留了完整的琉璃眼珠。
近观卢舍那大佛。
走到卢舍那大佛佛头跟前近距离观察,会发现卢舍那大佛脸上除了一些壳状的、长条形的陈旧疤痕,鼻尖、嘴角部分破损脱皮外,本体保护非常好。大佛双唇微闭、嘴角深陷,左耳有绿色彩绘痕迹。
在保护工程进行的228天里,所有曾经顺着脚手架贴近通高17.14米、头高4米大佛的人,到达大佛头部,都会被这脸对脸的古代工匠的视角所震撼,感慨这是50年一遇的难得机会。有龙门石窟研究院邀请来的学者、艺术家登上架子后,默默地与大佛做着无声对话,有的则激动得潸然泪下。
周边是脚手架的卢舍那大佛。
卢舍那大佛50年前面部修复的痕迹明显,早年卢舍那大佛左侧面部出现数公分的裂隙。
保护修缮从未间断
2000年1月,龙门石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审会议评价:龙门地区的石窟和佛龛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493-907年)期间,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这些翔实描述佛教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说,龙门石窟作为皇家工程,有着顶级的设计、顶尖的团队以及最适合精雕细刻的石灰岩,但也是因为石灰岩的岩性,易受流水的溶解和侵蚀,以及西山山体的形成与构造,导致危岩体及渗漏水,一直是威胁龙门石窟文物安全的主要病害。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马朝龙说,“造像是雕刻在石头上的,如果石头‘生病’,文物也会受到影响”。
整体保护工程进行中的奉先寺。
不论官方还是民间的保护修缮工作从未间断,至今仍能在部分石像上看到古代修复、描画的痕迹。
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十项主要任务,列在首位的是加大石窟寺抢救性保护力度。
此后,龙门石窟奉先寺渗漏水治理与保护工程(危岩体加固)启动,严格按照项目立项、勘察、设计、方案审批等程序进行报批。经国家文物局文物批复立项,按照国家文物局批准和河南省文物局2021年6月核准的保护方案实施。
奉先寺除尘的工人。
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脚手架搭建要求既不能接触到壁面,还要保持一段距离。施工人员采用了“悬挑架杆”的工艺,用岩体锚点与脚手架相连,斜拉加强筋,加装防坠网、防护网,确保架子更加稳固。
40000米钢管、8000平方米防护网、6900平方米脚手架,搭建奉先寺大修的“满堂架”可费了一番工夫,“光架子前前后后就搭了一个月”,马朝龙说。
脚手架一层层的拆除,奉先寺巨大的群雕显露出来。
这次奉先寺渗漏水治理与保护工程是抢救性修复,同时以考古发现和数据采集,为下一步制定龙门石窟整体5-10年的保护规划提供依据。依托脚手架,一架三用,是史家珍的创新之举。
“最初的架子为了不影响游客观赏,留出了卢舍那大佛周身。史院长雷厉风行,说做就做,和设计方、施工方商量后就开始给架子分层,每层往里加板子一直加到了佛像面前。”龙门石窟信息资料中心主任高俊苹告诉记者。
奉先寺除尘的工人。
龙门石窟历史人文研究中心主任路伟说,史院长一直强调石窟寺考古才是龙门石窟最好的保护手段。石窟寺考古的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汲取文物的数据信息,经过数据分析后,用数字技术还原文物本真,从而再现它最初的容颜和经历。
利用难得一遇的“满堂架”,6月到7月,路伟带队对奉先寺开展了全面的考古
调查。
奉先寺,“虚拟复原”海外流失文物。
北京一家三维科技公司的团队在这里采集数据已经有三个月,“运用高科技手段提取了文物残存的信息,摩崖、岩石、窟龛、造像、浮雕、藻井、环境等等,每一寸都要扫到,以保证数据的真实、完整”,然后进行整理研究,将多图像摄影测量与激光扫描的模型贴合,从而还原本真,再现文物初时风采。
“将来大像龛建好了三维模型,戴上VR头盔再看卢舍那大佛,就跟你今天登在脚手架上看一样贴近”,高俊苹说。
护佑石窟
奉先寺引人注目的渗漏水治理与危岩体加固保护工程虽已落幕,但龙门石窟的日常保护工作却一样引人入胜。
“游客到龙门石窟都是来看大佛的。”马朝龙说,龙门石窟在中国三大石窟里比较特别的地方之一是,除了洞窟里有佛像、碑刻题记,窟外满山也都是摩崖的造像,一下雨,这些造像无处躲风避雨。
古阳洞内,搭起来的4层脚手架直达窟顶,便于维修和考古。
龙门石窟洞里洞外有上千处小型窟龛存在不同程度的病害,窟檐也已脱落,导致窟内文物受到雨水直接冲蚀,西山的岩性是石灰岩,含碳酸盐的水反复溶解又析出,在造像表面形成病害。另外,水害进一步诱导窟内苔藓类生物生长,对石窟长久保存造成了严重威胁。
古阳洞上部的石壁有一股小水流从小臂高的佛像脸上流过,把佛像局部“染”成了黄色、白色。
古阳洞内,被山体缝隙水体污染的洞窟雕像。
“水是堵不住的,只能引流。”刘建设一边说一边先观察水的流向,然后用水硬石灰(和水接触后硬化,然后逐渐在空气中碳酸化,最后变成石灰岩一样)在合适的位置做了个V字型小排水系统,把水流引到V字的最低点再滴落下去。
因为修复的时候没有下雨,洞里渗漏水不明显,加之洞窟光线昏暗,为了迅速判断保护工程是否有效,刘建设在修好的位置贴上一张白纸,再次验证水流的路径。水很快就按着他的设计路线在白纸上留下印记。下雨过后,马朝龙来检查,“昨天下暴雨,我们看效果都很好”。
石匠刘建设用水硬石灰在合适的位置做了个V字型小排水系统。
古阳洞外,因为修旧如旧,来往的游客根本就注意不到许许多多的小佛龛都加上了一个个像雨棚的小窟檐,马朝龙用随身携带的激光笔对着摩崖上那些毫不起眼的窟檐来回比划。
古阳洞内,考古人员在观察洞窟内的石刻艺术,并做登记和描述。
古阳洞是龙门石窟开凿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一座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93年),洞窟高11.2米、宽6.9米、近身13.7米,规模极为宏大,整个壁面乃至窟顶遍布了大小不一、形式各异的像龛1000多个。古阳洞佛龛大多数都刻有“造像铭”,有800品之多,是中国石窟保存造像铭最多的一座洞窟。
洞内光线幽暗,潮湿闷热,脚手架将洞窟从窟顶到地面分割成6层,即使贴近辨认题记、图案,也很费眼力,李晓霞告诉新来的同事,“要使劲看,看明白,仔细看,直到看得没啥可看的”。
龙门石窟研究院考古团队在古阳洞进行考古工作。
古阳洞里,龙门石窟研究院信息资料中心在做另一件事——通过三维重建测绘,获取高精度、高分辨率、真实、完整的洞窟数据,为龙门石窟的保护、研究、展示和管理工作提供基础数据。
古阳洞内,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李志荣团队使用关节臂高精度激光扫描正射影像图采集数据。
日常维护
“龙门石窟如今还保留着唯一一处唐代窟檐遗迹,有的洞窟虽然没了窟檐,但还能明显看到镶嵌窟檐的凹槽。”马朝龙说,加窟檐可不是凭空想象的,“我们参考了历史窟檐遗迹,结合现有的窟檐防水效果,才最终确定了窟檐修复方案”。
龙门去年的年降水量超过了1000毫米,而当地年降雨平均为500-600毫米,这种可逆性的临时窟檐能将雨雪有效排离文物本体,效果很好。马朝龙说,这些窟檐有天然岩石头打磨的,靠刘建设的选材经验,也有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还有用3D打印技术来协助坍塌窟檐的修复。
修复渗漏水问题的匠人,在古阳洞进行渗漏水问题排查。
马朝龙说,目前龙门石窟日常维护里增修小型排水系统121处,利用纤维增强复合材料修复窟檐1296龛,保证排水系统的通畅。
对于龙门石窟的日常维护,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说,保护是良心活,“我们的老技工刘建设有很多土法,比如怎么做个窟檐,如果按项目报几十万块钱都可能,但是我们做就是几百块钱、几千块钱,讲的是实用性、融入性,可逆性”。
刘建设对古阳洞内的渗漏水问题进行“治疗”。
可逆性,就是要在文物保护修复的过程都要采取可逆措施,使其回到原始的状态,不使用无法清除的材料;融入性是指修旧如旧,保护修复后的文物不破坏整体的风貌和美感;实用性就是要节省经费,减少对文物的损伤,实现良性控制。
7月24日,俯瞰龙门石窟全景。
记者 陈杰 摄影报道
记者 刘旻 文字报道
编辑 刘晶 张湘涓
校对 杨许丽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