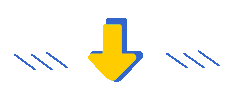目前关于夏朝的直接文字记录,均源于西周。早在商周鼎革完成之初,周公即在“殷遗多士”的诰令中提到:“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司马迁耗毕生心血所写的《史记》中亦将夏朝历史脉络梳理清晰。
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无论是西周文献亦或战国以后的传世史书,成书年代至少已跨越了500年以上,间隔了商朝整整一个朝代,其可信度已然大大降低。
此外,文献中对夏桀的种种描述以及商汤灭夏的整个过程,与后世对纣王的描述以及武王克商的过程存在雷同,让人不免怀疑是否是周人出于对灭商的合法性需要,而复制出一段商汤灭夏的历史。
那么,作为“殷革夏命”的最直接见证者—商朝,又是怎么描述前朝的呢?
让人困惑的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并未发现有关夏朝的卜辞记载。武丁在对始祖商汤的歌功颂德卜辞中,屡屡提到商汤的征战,却唯独忽略了灭夏如此大的功绩,这一奇怪表现也让西周以后关于夏朝的记载可信度再次降低。
当然,甲骨文没有找到夏朝的记录,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出土甲骨文目前还未全部释读,下定论为时尚早;二是甲骨文并非史书文字,而属于卜辞,不能苛求其将一个早已灭亡的政权脉络写入卜辞当中。
所以,在殷墟出土之后,考古学家们开始了对夏墟的寻找,以期望能让夏朝“自证”其是真实存在的。
1959年,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被发现,出土的宫殿、井字形道路网络以及手工作坊遗迹表明这里具备了都城属性,经碳十四测定,二里头遗址一期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
但由于没有直接的自证文字,我们无法断定二里头究竟是属于夏朝都邑还是早商都邑,就连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教授都提出了“二里头可能是早商都邑的假说”。
不过,殷墟的考古发掘和西周的金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商朝始年。
根据碳十四测定,武王克商的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商朝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前后。而对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碳十四测定,发现其时间上限为公元前1560年—公元前1580年,佐证了商朝的始年不会早于公元前1600年的结论。也就是说,二里头遗址的时间上限要比商朝始年早100余年。
此后,陕西石峁、山西陶寺等大型都城遗址相继被考古发现,碳十四测定年代均在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其文明程度也完全具备国家形态。
特别是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扁壶朱书文字,与甲骨文呈继承关系。经过释读,第一个字为“文”,第二字则有两种观点,有认为是“尧”字,即认为陶寺是尧都;也有认为是“邑”字。
但不论是哪种释读,石峁、陶寺碳十四测定的时间下限,与商朝始年的时间上限,跨度刚好可以容纳一个500年左右的文明时期。也就是说,在商朝和尧之间,必然有一个朝代,这从考古学上其实证实了夏朝的存在。但是,我们无法直接得出它就是“夏朝”。
朋友们看到这里或许会产生困惑,什么叫“证实了夏朝的存在,却又无法直接得出它就是夏朝”?
因为如前所述,夏朝目前无法实现自证,我们只能通过时间跨度去比对文献记载,得知尧舜禹与商朝之间为夏朝。
但是,夏朝这个国号其实是周人给的,正如曹魏称刘备的政权为“蜀”,东吴称“西”,后世称“蜀汉”,但刘备却绝对不会如此称呼一个道理,夏朝人会不会称自己为夏还无法确定,这或许也是甲骨文中不见“夏”的原因。
“夏朝”(暂时用这个称呼代替)虽然得到了考古的证实,但考古也同时发现了它的一大硬伤。
目前二里头遗址共分四期,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一期比商朝始年早100余年外,二期至四期的碳十四年代均已处于商统治时期,第四期的时间已经介于公元前1565—公元前1530之间,此时商朝早已经建立。
出土的陶器和墓葬显示,二里头从一期到四期,未发生大规模颠覆痕迹,也未发现有商时期的贵族墓地。反倒是从三期开始,一改简陋的陶器随葬,出现了大规模的青铜器随葬品,特别是有了束颈盆等极具商朝文化特点的随葬品。
但与同时期的二里岗商朝青铜器相比,二里头的青铜器还非常原始,陶器上出现的刻画符号证实文字尚未形成文句,甚至还不如陶寺朱书文字,其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商。
这也就意味着,夏文明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落后的多。在商汤建商之后,夏商并存了很长时间。商汤或许并未灭夏,夏朝可能属于在先进文明侵蚀下的自然消亡。
参考资料:《史记》《考古发掘简报》《殷虚文字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