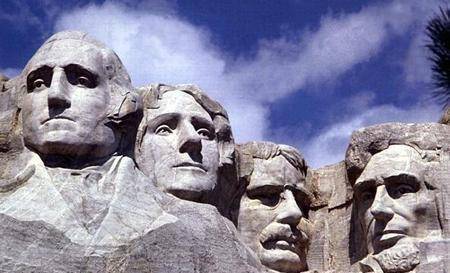她失过身。词典上对“失身”的注释为:“封建礼教指妇女失去贞操。”在30年前的中国,失身几乎是和堕落连在一起的。
她叫卫蓉,某医学院病理研究室年轻的女教师,时年二十六岁。她中等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圆酒脸上挂着娴静的微笑,两颊现出圆圆的小酒窝,没抹过口红却红浸浸的薄薄的嘴唇适度地开启时,线条优美地舒展开去,露出两排洁白的仿佛经过人工精雕细刻的小牙。她举止稳重成熟,浑身洋溢着桅子花的香味和浓浓的气质。
学院领导说:小卫事业心很强,工作认真负责,生活上艰苦朴素。
研究室的老师说:卫蓉作风正派,谦虚谨慎,不苟言笑,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
医学院的学生说:卫老师和蔼可亲,造诣很深,我们都愿意上她的课。
应该说,这是一个值得自豪的女人,一个应该拥有幸福的女人。
然而,她失过身。虽然并不完全是她的过错。这事发生在1983年。
当时上高二的卫蓉还是个十八岁的小姑娘。由于父母早亡,哥哥和姐姐又在外地工作,平时难得回家,只有卫蓉一个人在家守着四间大瓦房。在这期间,治安员肖红兵常来家里看她。卫蓉是通过哥哥认识肖红兵的,他比卫蓉大了十一岁,又是哥哥的好朋友。所以,卫蓉—直把他当作哥哥看待,而肖红兵也像哥哥那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她,充当着保护神的角色。每天晚上,她都要来卫蓉家坐坐,嘘寒问暖,关怀备至。走时还要先在四间瓦房中巡视一通,看看有没有小偷潜入室内,然后看着卫蓉关好窗子,倒锁上门,才骑着自行车离去。
那天晚上,卫蓉已做完作业,刷了牙,洗了脸,洗了脚,肖红兵却还没有离去的意思。卫蓉感到有些奇怪,但出于礼貌,她没表达出逐客的意思,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依然挂着娴静的笑。
肖红兵终于放下手中的一本文学刊物,抬起头来,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卫蓉。
卫蓉从他的目光里仿佛察觉了什么,打了个冷颤,正想站起来,没想到肖红兵已抢在她之前站起来,大步来到她面前,将双手放在了她的肩头。
“肖哥,你……”少女的声音本来就是动人的,何况带了颤音。
“蓉妹,我爱您!”肖红兵直言不讳地说。
“不!”卫蓉挣扎着站起来,想推开肖红兵,但肖红兵已张开双臂,将她紧紧搂在了怀里……卫蓉哭过,挣扎过,因为她没有爱,也还不懂爱。她甩尽了所有的力气,也没能逃出厄运。
从那晚起,卫蓉心灵上就被凿刻下一个永远难以消失的标记,留下一道深深的,难以愈合的创伤。由于少女的羞涩、懦怯、无知等诸多原因,她没有告发,没有声张,没有泄露,默默地咽下了这颗苦果,她唯一能做到的是,再不准肖红兵跨进她家的门。
1984年,卫蓉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医学院。她离开家乡到广州上大学时,哥哥和姐姐到火车站送她,肖红兵也忐忑不安地跟在哥哥身后。卫蓉没和他说过一句话,甚至连眼珠子也没向他偏移一下。并且,从此她再也没见过他。
但从此,肖红兵的影子却跟定了她,就像她自己的影子一样。
大学是用笑脸迎接卫蓉的, 她天资聪颖,纯洁善良,待人和善,刻苦好学,不仅专业基础好,外语水平高,而且善于从专业理论与专业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去阐述问题和解决问题,因而博得了同学们的尊重,老师的喜爱,学校领导的赞扬,成了全校屈指可数的三好学生。
在大学期间,卫蓉和八四级五十八班男同学盂超凡相爱了。爱得水深火热,爱得你死我活,受得难舍难分。
五年的大学生生活,一眨眼就过去了。毕业分配时,卫蓉意料之中地留在了学校。而孟超凡却出乎意料地分配到边远地区的某矿务局医院工作。
孟超凡懵了,好几天回不过神来。
孟超凡绝对没有想到,半年后他会重新回到这里,而且还奇迹般地调到了一家著名的大医院里。
半年来,卫蓉为了孟超凡能调回,几乎每天都在奔波着,跑大了脚板、说哑了喉咙、不知送了多少礼,不知流了多少泪。
当孟超凡重新回到学习、生活了五年的母校时,他望着消瘦了许多的恋人,想象着腼腆的未婚妻是如何劳神费财,抛头露面,求亲托友,奔走呼号,想象着她曾遭到的挫折,忍受的白眼,孟超凡伤伤心心地哭了,边哭边说:“蓉蓉,我太感激您了!您为我做出的牺牲太大了!蓉蓉,我永远爱您,永远永远,海枯石烂,心永远不变……”
卫蓉笑了,笑出两行眼泪,她用手掌紧紧捂住了未婚夫的嘴巴,不让他说下去。她丝毫也不怀疑这些话的真诚,她感到很幸福,还有什么可奢求的呢?为了她,孟超凡可以去死。尽管她十分不愿意他吐出那个不吉利的字来。
1990年8月,他们结婚了。当高高大大,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西装革履的孟超凡挽着娇小玲珑,端庄文雅,仪态万端,白纱长裙的卫蓉出现在宾客们面前时,谁不夸他们是理想的伴侣呢?
那晚,他们高雅的洞房内来了那么多客人,有同学,有同事,有老师,有领导,客人们笑着,嚷着,嗑着瓜子,吃着喜糖,逼着新郎新娘表演了那么多的节目……
客人们离开时已是凌晨一点多钟。
“蓉蓉,睡吧。”新郎温柔地抚摸着妻子的头发。他有些迫不及待了,恋爱几年,他的蓉蓉总坚守着最后一道防线,使他又恼火却又对她怀着深深的敬意。
“蓉蓉,睡吧。”丈夫铺好床,又发出亲切的呼唤。
妻子用尽全身力气站起来,一步步挪向丈夫,她身子一歪,瘫软在丈夫怀里。丈夫抱起妻子,将她轻轻地放到床上。
事实证明,卫蓉的担心是多余的。那晚,夫妻间发生的事情都平安地过去了。
婚后,他们的生活是幸福的,甜蜜的。卫蓉含着深深的爱,当然也有深深的歉意——对丈夫百般柔情,万般蜜意。她尽自己所能,让丈夫吃好,睡足,玩够。她不知从哪里听说牛奶加山药蛋营养价值最高,并且,要在天亮前吞服。于是,每天凌晨四点,她就给丈夫熬好,端到床头。他怕丈夫晚上睡不好觉,每晚上床时都要叮嘱她尽管放心睡觉,每天清晨,她都要把早饭煮好才叫醒丈夫。她用自己的工资,买来拉力器,哑铃,腰力器供丈夫锻炼身体。她不管自己是否需要,只要丈夫需要,她就尽量满足他的需要……
这样柔情似水的妻子,这样和睦美满的家庭,孟超凡怎能不乐不笑不爱呢?他常将头埋在娇妻温暖的怀中,梦呓般地说:“蓉蓉,这辈子能碰上你,也不枉自活一世了。”
在这个家庭里,一日三餐卫蓉全包了。锅碗盆勺,卫蓉全洗了。家里的里里外外,大事小事,全由她管。她无形之间成了家庭的主人。她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每一个家庭成员。领到奖金,她给公公买皮毛裤。领了工资,她先给小姑子买衣物。而她直至锒铛入狱,手腕上戴的却还是不足十元钱一只的电子手表。
这样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还有什么好埋怨的呢?
但卫蓉始终忘不了那个肖红兵和她的夜晚。
卫蓉无微不至的爱自然换来孟超凡无微不至的爱,同志们都说他们不是度蜜月而是在度蜜年。孟超凡把卫蓉捧若明珠,噙在口里怕化了,放在手心怕飞了,每天和她形影不离。而丈夫越爱妻子,妻子越觉得对不起丈夫,因为她觉得自己隐瞒了那件事,自认为欺骗了丈夫。
该不该把那件事情告诉丈夫呢?卫蓉常常这样想,以致弄得神思恍惚。
告诉他吧?他能不能经受住这沉重的打击呢?他会不会伤心,愤恨,从此对自己另眼相看呢?不告诉他吧,爱情是高贵的,纯洁的,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隐瞒和欺骗。其实,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没有属于自己的秘密,那是天真或者是虚伪,封建思想的爱情观曾经坑害了多少人啊。经过长达数月的紧张,激烈的思想斗争。卫蓉决定将那件事告诉丈夫。
她选择了一个最适当的时机。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看完电视,回到卧室,关上房门,丈夫轻轻一按录音机,简单、整洁、舒适的卧室内立刻响起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多瑙河两岸美丽动人的风光画卷般展现在他们面前,蔚蓝色的河水,翻腾的白沫,旖旎的风光,在春光里翩翩起舞的少女,向姑娘倾吐着爱情的小伙子乐曲声中,卫蓉换上了那件丈夫最喜欢的蔚蓝色的睡衣,然后静静地坐在丈夫身边,将头放在他肩上。孟超凡开始抚摸妻子的秀发,她抬起头,身子一歪,仰进丈夫怀里,用含情脉脉的眼睛鼓励着丈夫。
卫蓉说:“超凡,我不该瞒了你六年呀……”
“您什么事瞒了我?别哭, 慢慢说,啊?”
“七年前……一天晚上……”卫蓉冷静了一些,哽哽咽咽,断断续续地说。她把那夜发生的事情彻彻底底地向丈夫坦白了。尽管这种“坦白”是不必的。
讲完后,她先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心里轻松了许多。但紧接着,这种感觉又被惊恐所代替。因为她发现,丈夫抚摸着她秀发的手掌停止了蠕动,在头顶停留了十几秒钟,好像在思索,在犹豫,在彷徨。但那只手很快就触电般地飞开了。丈夫慢慢站起来。步履维艰地走到床前,坐下,燃起一支烟。点火时,他的双手哆嗦得太厉害,连划了三支火柴才点燃纸烟。
卫蓉倏地翻身坐起,慌乱地奔到满脸雷鸣电闪的丈夫面前。蹲在地上,双手紧抓着他的膝盖,就像溺水的人抓着救生圈,可怜巴巴地说:“超凡,我对不起您,您能原谅我吗?您会原谅我的!您说会的……您说……您说……”
他看着天花板,什么也不说,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
卫蓉双膝一软,跪在丈夫面前,用力摇着他,流着泪呼喊着他:“超凡,超凡,您说话呀……求您了……”
盂超凡往卫蓉胸口上狠狠推了一掌,使她跌坐在地上。他嗖地站起来,扬长而去,“啪”一声碰上了房门。
这天晚上,孟超凡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弄得客厅里烟雾缭绕。
从此,在孟超凡眼里,妻子的美丽,聪明已不复存在。过去,妻子对他的体贴,温柔,对公婆的孝顺,关怀,对小姑子的亲热,关照,现在看来全是有意的伪装、粉饰,矫揉造作,目的只有一个, 骗取信任,窃取好感,以掩饰她的过去。卫蓉在丈夫眼里已完完全全地变了个人。他开始看不惯她,越看越不顺眼,越看越生气,越看越觉得她奇丑无比,黑皮肤,凸牙床,小眼,阔嘴,蒜头鼻,排骨……甚至连她换一件漂亮的时装,他也觉得东施效颦,令人作呕。丈夫开始把所有的不快都往她头上发泄,所有烦恼都归罪于她,轻则恶言秽语,重则拳打脚踢,完完全全地把她从家庭主妇的位置上一脚踢到纯粹的奴仆和泄欲筒的地位。
卫蓉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丈夫骂时,她忍气吞声,沉默不语,垂着头垂着眼帘垂着双手,像个做错事情的小学生,让他骂个舒服,骂个够。丈夫打时,她仅用双手护着头,躬着身子让他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打个痛快。
难道这就是我多年追求,辛勤奔波,无私奉献所换来的硕果吗?卫蓉常常这样问自己。固然,面对丈夫的打骂,冷淡, 我可以忍,可以受。然而,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呢?她有怨,有气,有仇,有恨。但她矛头所向的始终不是自己的丈夫。她怨肖红兵……
终于,她按捺不住了,忍受不住了,她要报复了。
1990年12月18日,隆冬季节的城市,天高云淡,阳光驱赶着冬季,但成都总给人春意盎然的感觉。
卫蓉步出火车站大门。来到公用电话亭拨了个电话号码。
电话通了。
“喂,请找肖红兵。”由于紧张,她捏话筒的手和声音一起抖索不已。
“请等等。”
不一会,话筒里传来了普通话中仍夹杂着方言的男中音,声音中带着职业的警觉。
“喂,你是谁?
“我叫卫蓉,我找……”
“小卫!小卫,我就是红兵呀,您现在哪里?”能听得出,接电话的人又惊又喜,激动万分。
“红兵,我来这里出差,顺便看来您。”她的声音也饱含着热情,但嘴角却挂着一丝阴沉的笑。
“我马上来接您!马上!您千万不要离开电话亭。”
放下话筒,卫蓉咬了咬下唇,用手帕擦干眼泪,找个地方坐下,掏出化妆盒,左右看看,就着盒盖上的镜子,先用粉饼往脸上均匀地抹上一层粉,然后精心地将细眉描粗描黑,涂上唇膏,又往身上洒几滴香水。
一辆出租车迎面疾驰而来,在她身边停下,肖红兵从出租车上走下来,冲到卫蓉面前,在离她两步的地方站住,百感交集地打量着她。
卫蓉也站起来,默默打量着肖红兵?还是老样子,英武的剑眉,微微上翘的嘴角挂着笑容。只是胖了些,黑了点。
简单寒暄后,肖红兵接过卫蓉的挎包,一招手叫住一辆出租车,领着卫蓉上了车,吩咐驾驶员到饭店。
女招待飘然而至,双手把菜单放在桌上,又退回半步,双手交叉着放在前面。
肖红兵把菜单推到卫蓉面前:“蓉蓉,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别客气。”
卫蓉又把菜单推到他面前:“你点吧。”
肖红兵不再客气,拿起菜单,豪爽,大方地一口气点了七八种名贵菜肴和两瓶啤酒。
卫蓉没阻止他,因为她知道他已经没有节约,存钱的必要了,最后一次晚餐,浪费点也是可以的。
酒菜上桌后,他们开始边吃边谈。
“蓉蓉,您怎么知道我调到了这里?”
“听我姐姐讲的。”卫蓉回答。她没完全说实话,为了调查肖红兵的去向,她给包括姐姐在内的亲朋写了好几封信。
“听您姐姐,哥哥说,您结婚了?”
“嗯。”
“怎么不通知我们一声?”
卫蓉淡淡一笑,愿他这样没完没了地问下去,反问道:“老肖,谈谈你吧。”
“工作,生活倒没什么好埋怨的。只是精神上空虚得很,老想起过去……”
卫蓉牢牢地盯着他的眼睛,她想知道他现在的真实心情。可惜,由于被报复的情绪所驱使,她什么也看不出来。
肖红兵的谈锋很健,兴致极高,滔滔不绝地谈个没完没了。卫蓉却不想听了,因为她已没有多余的时间,她要立刻实施她的计划。
“红兵,”卫蓉扭头看着邻桌的一个胖子,胖子正津津有味,嘴角流油地咬食着烧麦,“去给我买几两烧麦。”
“好的。”肖红兵站起来,往小吃部走去。
卫蓉飞快地从挎包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剧毒药品氰化物,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毒药倒进了他的啤酒杯里。
肖红兵很快就把烧麦端了过来。他坐下去,端起酒杯,和卫蓉很响地碰了一下杯,一仰面喝了一大口啤酒,咕嘟一声咽下去,皱皱眉,大约是感觉到了啤酒中的铁臭味,又端起酒杯,小心翼翼地抿了半口,咂咂嘴唇,误以为啤酒已经变质,也不便说破,毫不在意地把酒杯推到一边,和卫蓉一起吃烧麦。
卫蓉没劝他继续喝啤酒。作为医生,她很清楚,仅他抿下的那半口啤酒,也足以夺走他的生命。
果然,没过多久,肖红兵就感到胸憋,气闷,恶心,头晕,想呕吐。他放下筷子,强打精神坐在那里陪着卫蓉。
“我……有些不舒服。”肖红兵实在撑不住了。
卫蓉知道药性已开始发作,就放下筷子建议说:“我到那外面散散风。”
“好吧。”肖红兵说。
卫蓉主动上前挽住他的手,用身子支撑着肖红兵离开了饭店。他们看上去像一对恩爱夫妻或热恋中的情人。
卫蓉挽着肖红兵拐进了一个胡同。肖红兵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哇哇”呕吐不已。
“你咬咬牙,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去给附近医院挂个电话,叫他们派部救护车来。”卫蓉此时也十分紧张,她感到了恐惧,甚至有些后悔。她慌慌张张地逃离了现场,拦住一辆白色出租车,跳上车,价也不讲,急切地说:“火车站!”
她当时或许没有想到,饭店女招待和这位出租车司机,后来都会出现在法庭上。
当路人把昏迷不醒的肖红兵送到医院后,因中剧毒,已无法抢救了。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当卫蓉以重犯的身份被投进那与世隔绝的严壁高墙,铁门冷窗后,当冰凉刺骨的脚镣手铐禁锢着她娇弱的身躯时,她似乎才恍然醒悟。于是,她开始捶胸跺脚, 号啕痛哭。她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迁悔,反正现在有的是安静的环境和时间。她悔恨自己在光天化日之下投毒杀人。她悔恨自己不顾后果和危害,杀死一人,毁了两个家庭,葬送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