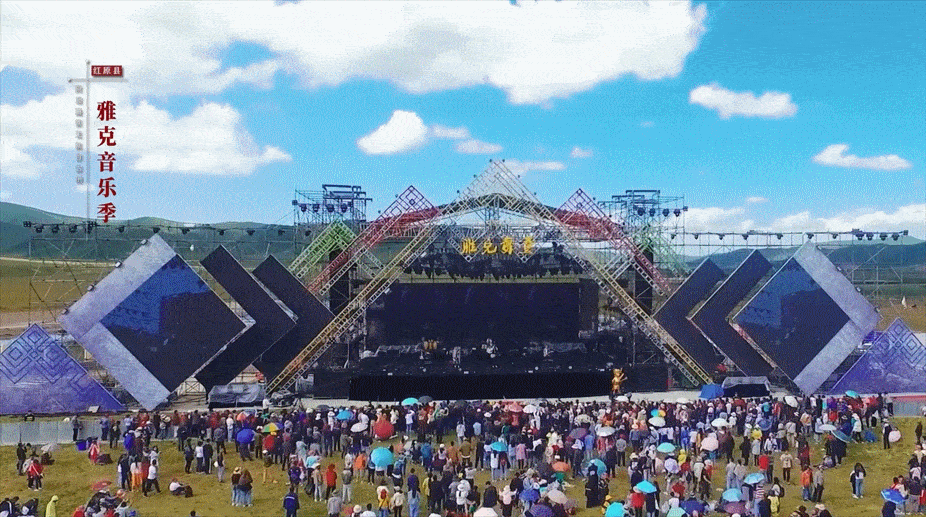《博南冬晨》 杨迤夫 /摄
我们的车子就在永平坝子中央缓缓行进,在连绵群山间,其实很难见到这样一块平地,但似乎仅一眨眼工夫,平地就到了尽头。汽车驶入年代已经有些久远的320国道,眼前交替出现的是山岭、丘壑、峡谷、溪涧、沟渠和险坡。天气阴沉,层层叠叠的大山深处云遮雾隐,给人呈现的反倒是一种桃源胜地般的神秘。
但说实话,我却有些喜欢这样的地理变幻——忽而流出一条河、忽而呈现一个村庄、忽而又是一片田畴,阡陌往来,富有诗意。一丘丘梯地,被修在大坡小岭之上,盛夏时节,大地被换上了盛装,眼前全是一色墨绿。但在快速行进的车中,我却看得清地里栽种的是拔过节的玉米、换过苗的稻子和正打着苞的万寿菊。高山、低地、村庄、田野,一概层次分明。我同样看得清车窗外面一溜而过的榕树、松树、核桃树、花椒树、楸木树和芭蕉树,郁郁葱葱。
毫无疑问,今天的永平依旧还是滇西大地的咽喉要塞。这里有从两千年历史深处走出的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有抗战烽火弥漫下的国际救援大通道滇缅公路,同时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修通的320国道和大保高速穿境而过。于是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不仅流传着云南高原上最早的古歌《博南谣》:“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还留有杨升庵、徐霞客、徐悲鸿等历代大师的足迹。
走进永平,我们其实还是更愿意走进大山的褶皱,去寻访古道的历史沧桑。一道跨越千年的古道就隐在茂林深处,连绵起伏的博南山中,我清楚地看到了古道被修成了一条深壕,两边是刀削一般的路壁,路心被铺上细密的石板。同行的文友张继强,是当地有名的文史专家,在他的导引下,我还寻得到许多当年留下的马掌印,一块、两块、三块……历经数千年的岁月光影,我似乎还听得到当年渐渐远去的马蹄声、吆喝声、歌唱声和叹息声。
一道“深壕”过后,又是一道“深壕”,在历史的光谷中穿行,眼前突然一片豁亮,我在一棵被设上围栏的桂花树后面,看到了一个深涧,继强说那就是古道上著名的“万马归槽”遗址。万马归槽,其实是一个颇有渊源的古道文化典故,大概意思就是马帮队伍从丛莽包围的古道中走出,来到此处,离古博南郡旧址的花桥镇已经不远了,于是大伙便常常三五成群,在这里安营扎寨、烧火做饭,疲惫的马儿当然可以直接下到山涧深处饮一口水,也就有了万马归槽的生动景象。
事实上,永平就是一本无比厚重的历史大书。我曾在这里吃过味道极好的“黄焖鸡”“辣子鸡”“赶马鸡”“大块鸡”“菌子鸡”等,也曾和一干文友,在一两个店子里喝过一种劲儿很大的“马道子酒”,据说这些都是当年从这条古道上流出的佳肴陈酿,在滇西的美食地图上向来极负盛名。一次次来又一次次回去,我估摸这样的人间至味,兴许就诞生于我身畔的某一个野灶上。
在永平县境内,蜀身毒道又被称作博南古道。为寻访古道遗迹,我们经历曲硐、铁厂、花桥、杉阳、江顶等大小村镇,时而乘车,时而步行,终于在天黑前来到澜沧江边。两岸大山如峙,谷中大江奔流,不想狭窄的视野里,居然同时出现了三座大桥,而其中一座铁路桥被称作是大瑞铁路澜沧江特大桥,我只感觉气势尤其壮观。
一桥飞跨南北,从此天堑变通途。即将全线贯通的大瑞铁路,很快就将把滇西高原带入高铁时代。行走于昔日的古道之上,不断涌现的桥梁、隧道,让我心中也生发出一种新的畅想。
作者:王灿鑫 (单位系大理州教育体育局)
转载请注明来源《民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