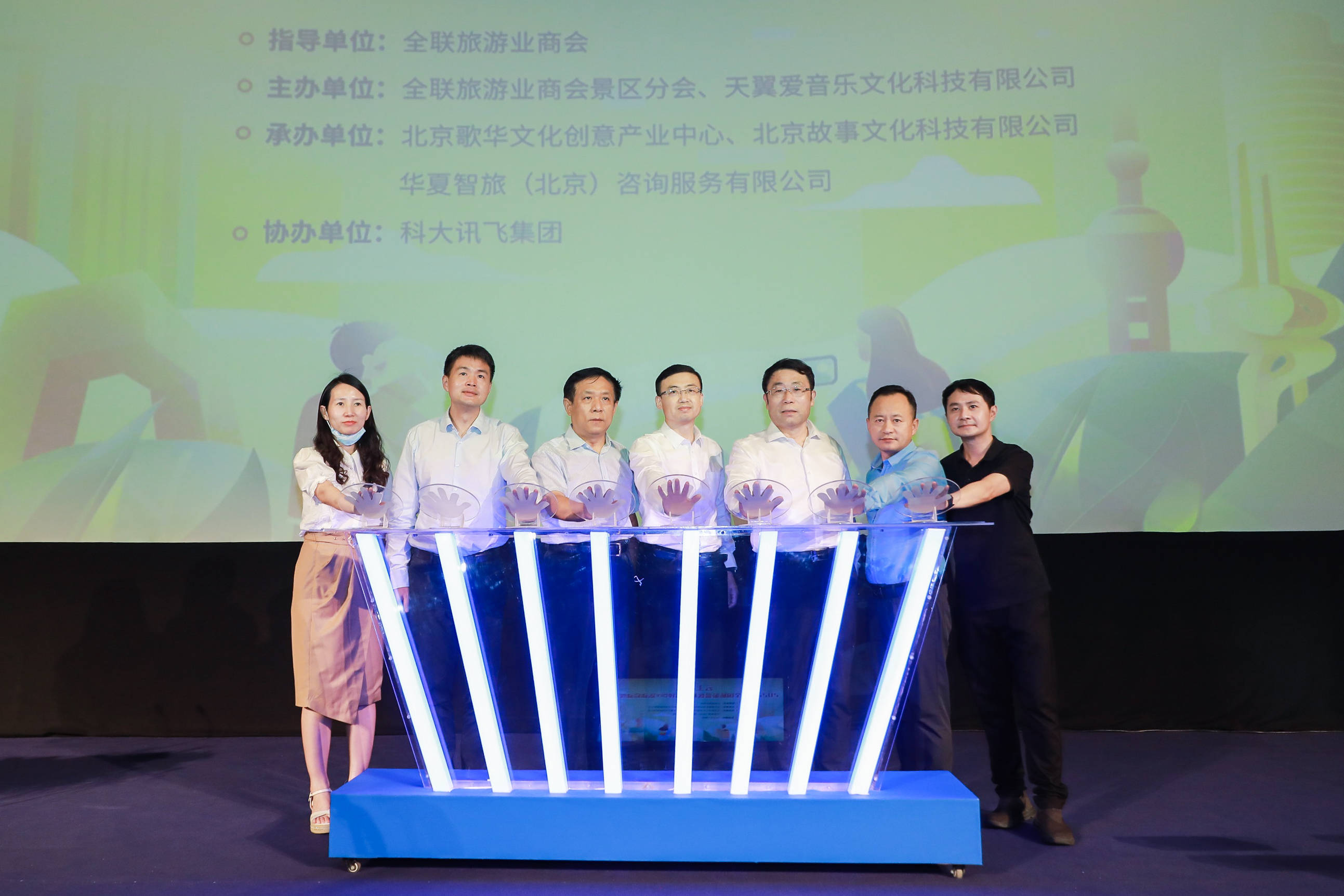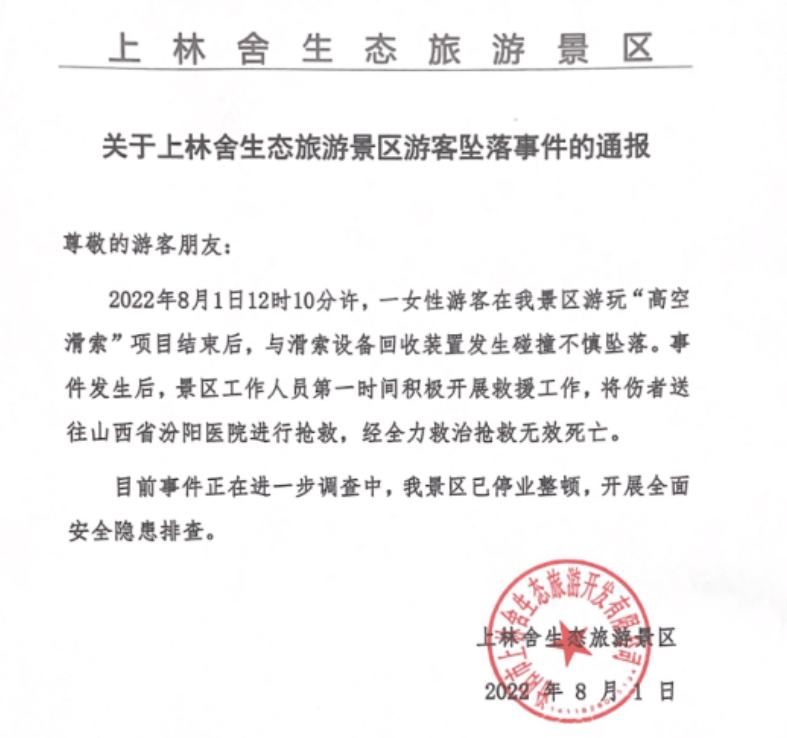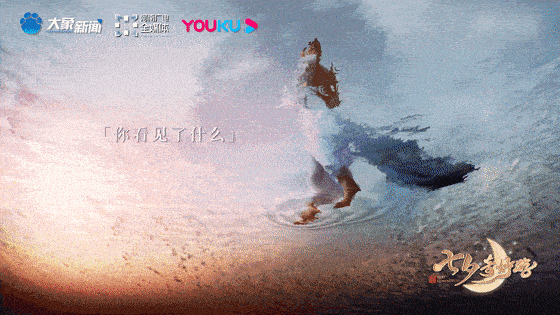雨后的黄水
莫测
夏天的重庆主城,好久没下雨了,温度一路攀升,热得我们赶紧往三百余公里之外的黄水逃跑。
奇怪,刚到黄水的中午,就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偏东雨。它是为了迎接我们而铺洒的银花雪帘?还是要冲去我们那一身的汗水与暑意?我谢绝了打麻将,告别了午睡,奔向山坡,奔向大自然,好好领略了一番雨后的黄水。
雨,湿润了空气,湿润了草木,湿润了土地,也湿润了我燥热的心境。我踩着温柔清芳的汪汪积水,好像踩着一面面镶嵌在大地上的、规格各异的水银镜片。从镜片之中,可以看见乱云飞渡的蓝天和摇曳舞动的灌木。刚被雨儿吻过的树叶,腮边还闪烁着激动的泪花。吻痕是那样深情,那样真挚,那样情意绵绵。羞得柳枝垂下了头,羞得芭蕉掩去了脸。
薄如蝉翼、灵动活泼、如锦似缎的云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了山岭沟壑、峡谷密林。它们似乎早有约定,东一团,西一缕,悄悄地从山麓、岩缝、沟坎中跑出来,相会于低空。然后互相拥着抱着、唱着跳着,聚集成了偌大的云海,把山峦、树木、村庄、道路,全部淹没其中。她们在干什么呢?在过滤空气,在洗涤山川,在沐浴草木?我不知道。我站在山的肩头上,等待云烟把我一起淹没,一起包围,一起溶化。但是,云烟忸忸怩怩,不即不离,只在我身边羞羞答答地环绕、观望,就是不靠近我,似乎在躲着我。
一会儿,云烟氤氲,结伴而行,潮水般涌向天际,与高空的彩云融为一体,使整个天地一片混沌,一片朦胧,一片迷茫。看不清哪是天,哪是地,哪是雾,哪是云?不知是天覆盖了地,还是地吞没了天。
这云烟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地心冒出来的,是从草木中蒸发出来的,是被那场偏东雨浇出来的,还是雨霁天晴的象征?总之,它不是农家房顶那袅袅炊烟,也不是风儿吹下的云裳绵缎。
松树湿漉漉的,每根松针上都有一滴晶莹剔透的水珠儿,她们多像一双双扑闪着的眸子啊。她们是在留恋刚才那一场偏东雨呢?还是与我一样,在欣赏雨后的黄水,在呼吸洁净如洗的空气?
每一片树叶,每一根青草,都像那刚出浴的少女,一尘不染、冰清玉洁、光彩照人。一股朝气蓬勃、青春洋溢的气息扑面而来。看着她们,自己似乎都年轻了许多。
偶尔,脸上掠过几丝清凉的微风。风是那样浸透柔嫩,那样入骨爽心,似乎身处溶洞,慢步冰川。从火炉中逃出的我顿时感到了满满的舒爽惬意。那微风,似乎不是吹来的,不是刮来的,我甚至怀疑它是天仙专门召唤来降热伏暑的。
半小时左右,天和地终于分离开来。但分得依依不舍,分得牵肠挂肚。云烟走走停停,走走停停。有的刚迈开步子,又转身拉住云的衣角不肯松手。有的停在空中,左右徘徊,不愿挪步,满脸都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忧伤与牵挂。
西面,太阳伸出巨手,拔开云层,横空出世般把透明、绚丽的阳光洒向大地。把山峦峻岭森林大地从厚重密集的云烟中一一解救了出来。此刻,我看清了,云烟醉入了树林的怀抱,钻进了群山的褶皱。远山一片深绿,绿得沉静,绿得庄重,绿得厚实。似乎那绵延起伏的群山,都穿上了统一的国服。
近处,那些淡黄的剑竹、山杏,瓦灰的塔松、垂柳,墨绿的含笑、榕树,以及各种叫不上名的小草、小树、小花,她们刚从雾障中出来,在阳光的辉映下,浑身上下挥金洒银,熠熠生辉,似乎皆在尽情地享受着雨露阳光。
刹那间,天空变了。变高了,变远了,变宽了,变得无边无际、纤尘不染了,只有几朵流动的云雕急急忙忙向北方飘逸而去。飘着飘着,云雕也不见了,剩下了满天深蓝、万里晴空和在喧嚣闹市不可能有的轻松、静谧、明丽、爽朗的好心情。
无疑,雨后的黄水是唯美的。其实,彩虹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在风雨之后啊。
(作者简介:重庆作家协会、散文学会、杂文学会、公安作家协会会员,重庆报告文学研究会理事。曾从事过文化教学、新闻宣传、报刊编辑等工作。偏爱文字,先后尝试过小说、散文等多体裁写作,数年笔耕不辍,偶有小文见诸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