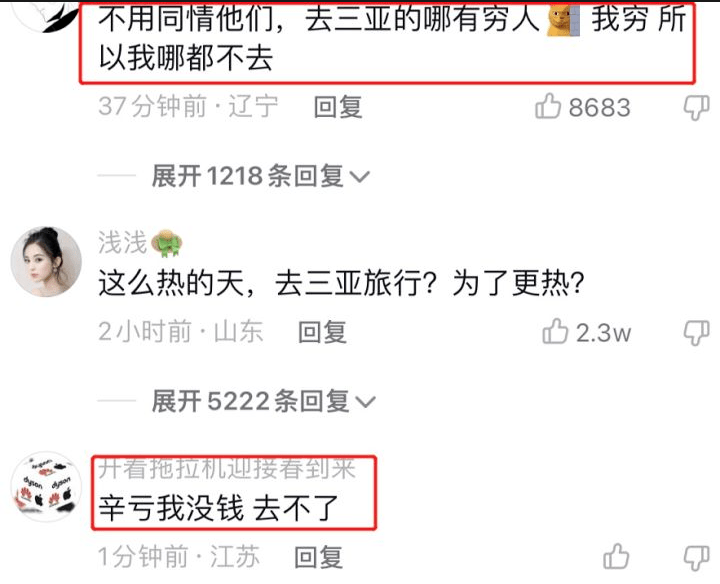●刘鹏凯
花园里很静。
白色的姜花在阳光下显得十分耀眼,从斑驳的木门望过去,它们像一群白鹤立在绿草中。墙是有些老了,从青色的古城砖可以辨别出它的年代,但这些丝毫不影响它生命的延续,因为,这是历史。更何况还有许多草,它们长在墙根下、墙缝里、墙头上,给灰色的墙注入了绿色,带来了生命。
花园里还有许多树,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正当我想象着它们的年龄时,就冷不丁听到一声鸟叫,抬起头才发现,鸟儿不是一只,而是两只,它们在树上亲昵地交叉着脖颈,或者梳理羽毛,或者东张西望,或者一起啾啾啾地鸣叫,那是呓语,那是撒娇,其实那是鸟儿们在树上谈着自己的恋爱。
顺着小径继续往里走,阳光就顺着树冠间的空隙漏下来,洒在身上,浑身上下顿时觉得暖暖的。
这个时候,从拱形门庭里闪出一个老人来,他非常瘦小,一件毛衣几乎裹了全身,趿着一双绒拖鞋的两个大脚趾处,分别都烂着一个洞。这个老人将双手插进袖筒里,脸上泛着幸福的笑容。他三两下就走了过来,问我们从哪里来?是干什么的?又问我们等会儿还到哪里去?他很健谈,双手时不时从袖筒里抽出来比划几下,然后再插回去。走近了我才看清楚,他的脸和那些墙一样了,头发却不像墙上的草,都已花白了,但仍觉得他很是年轻,慢慢才发现,那全是因了他的笑容、他的乐观态度。
正说着话,这个老人突然一声不吭地走了。我正纳闷着,他却又一声不吭地出来了。他手里提着一把锃亮的菜刀,只见他顺着老墙走到那片姜花前,手起刀落,将那绽放的姜花砍了好多抱在怀里。之后,他又顺着老墙飞快地走到我们跟前,将手中的姜花分发给我们。霎时,我们被笼罩在香气扑鼻的姜花里。老人说,它们早都开了,清早起来,满园子都是香味。他还说,从北方到南方,我见过许多花,只有这种花的香味最怡人。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人早年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去了安徽,在当地的一所大学任教。他会说粤语、会说英语,但最爱说北京话,纯粹地道,字正腔圆。老人在沧桑的人世间见到过许多种花,香的或者不香的,开放的或者不开放的。老人七十多岁了,是老了,可他又很年轻,像姜花。
我把目光从老人的身上转移到他身后的房子上,几缕轻烟从甬道里漫出来,空气里立即有了些许烧干草的味儿。从屋顶看上去,是一方蓝天,还有几片白云,它们一直就这么存在着。微风吹过,不留一丝痕迹。这时已是深秋了,树照样在绿,花照样在开,不知是时间改变了空间,还是空间改变了时间,反正这就是年月日,这就是水火土。
偌大的花园里依然寂静无声,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老人守护着自己的花园,就是守护着自己坚强的灵魂。那两只鸟儿飞走了,或许它们明天还会再来,但它们永远不会明白,老人小的时候离开了这里,老了为什么又回到了这里。
我们要告别了,老人依依不舍地把我们送到门外,送到巷道口,然后挥挥手,不说一句话,脸上却一直挂着笑容。我们都走好远了,他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