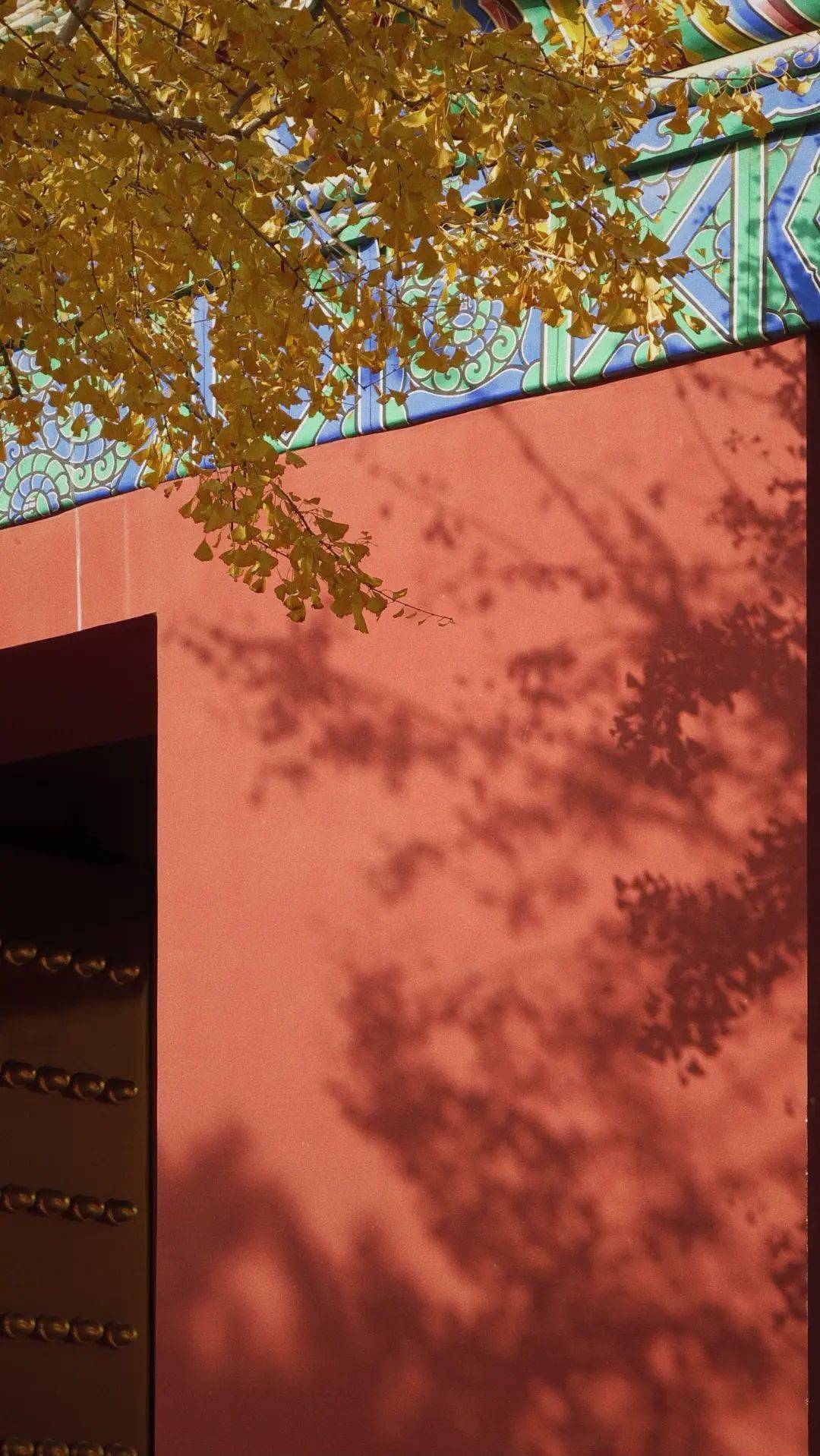老家在茶陵的一个小山村,文水河缓缓流淌绕村而过,三面环水的小村庄,安逸静谧地躺在小河的怀抱中。濒水有一片两百余亩的苦槠林,树木高大粗壮,枝叶葳蕤。
苦槠树属珍贵常绿乔木,树干通直,树冠浓密,叶阔质厚有光泽,春末开花,秋末果熟,立冬前后果子自然从壳斗脱落,即为苦槠。
小村庄依偎树林,树林簇拥小村庄,村里人皆姓段,树与人和谐相处已有几百年,却没有人说清楚,先有树林,还是先有村庄。村里老人们把这片树看成神明所赐的风水树,不敢轻易冒犯。我曾祖父的护林故事,过去了百余年,至今却还在村里口口相传。
苦槠树材质坚硬,是上好的家具材料。每个年代总有损公肥私的刁民,那时有位村民偷偷伐树取材,村里人碍于同族情分,敢怒不敢言。曾祖父召集全村人商议护林,定下规矩:砍树毁林者,以杀猪宴请全村人作为惩罚。第二天,曾祖父自演了一出“苦肉记”,伐树一棵,只得宰肥猪两头,宴请全村老少。此后百余年偷伐树木者绝迹,从而留下了这片树林。
前人护树,后人乘凉。1944年一队日本鬼子进犯茶陵城,路过小村,村民再次凭借树林掩护逃脱,而无一伤亡,而别的村子就没有这般好运气,死伤众多。
我的童年就在那片苦槠树林里度过的,那是我的乐园。
夏天里的林子,绿树成荫,凉风习习。炎热的中午,我和小伙伴们结伴去河里游泳,累了爬上岸钻进林子来乘凉。
在这片林子里,我甚至学会了爬树掏鸟蛋,一次抓了两只小斑鸠回来饲养,却被爷爷训斥送回鸟巢,还罚背杜甫的诗歌《鸟》。至今我还能背诵“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秋末冬初,霜风渐起时,就是苦槠成熟的季节。开心的是早早起来,拿个蒲瓜瓢或提个竹篮,去林子里拾苦槠。刚掉落的苦槠灰褐发亮,外壳坚硬,形同板栗。要是夜里下过一场雨或刮过一阵风,地上到处都是苦槠,一个早上拾满一竹篮是常有的事。
拾苦槠最好玩的,还是晴天的早上,小伙伴们就地取材,拾起地上的枯枝落叶,拔下开裂的片片树皮,生起一堆堆火苗,一边烤着火,一边把苦槠放在火里煨烤,只要听到噗的一声,那就是苦槠熟了,趁热而食,一点儿也不苦,香酥可口,美滋滋的,那时我感到那是人间无上美味。
捡拾苦槠,聚少成多。一有半桶就可做苦槠豆腐了。把苦槠在阳光下曝晒,外壳自然开裂,去壳后浸泡一两天,用石磨磨浆,注入一口大锅,一边用火熬,一边不停地搅拌,火候一到凝成胶状,倒进大盆自然冷却后切成方块,苦槠豆腐即成。
制作好的苦槠豆腐,光滑、略微透明,呈现酱褐色,散发着淡淡的香气,令人垂涎三尺。苦槠豆腐烹调还颇有讲究,锅热油老、少翻慢炸,作料红辣椒粉、香葱不可少,端上桌来观之如美玉凝脂,食之柔嫩爽滑,鲜爽清香,美味可口,风味独特。
今天看来,苦槠树远离环境污染,不施化肥,不打农药。苦槠变成豆腐上餐桌,不加任何添加剂,世界哪里有比这更绿色健康有机食品,这是大自然的馈赠。
苦槠豆腐,村里人吃不完,除了送亲朋好友,还会挑到集市上去卖,换些钱给孩子们添上过冬的鞋袜或衣服。
冬去春来,小村里的人一代代老去,苦槠林也似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小村庄在门前的文水河上,修建一座大型石拱桥,需大量的木材,大家把目光投向了这片树林。大型锯木机器搬进了树林,数十棵几人才能合抱的苦槠树倒下了,向村里人献出了自己的伟岸身躯。时光变迁,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青壮年村民大都外出务工,腰包渐鼓了回来,回家起房盖楼,慢慢侵蚀这块林地,隔三差五伐倒一棵大树,来扩大自己的地盘,满足自己的私欲。
村外的最近的两座县城茶陵与莲花,在大搞建设开发,沙石价格水涨船高。林地下面厚厚的细沙石成了一笔大财富,水泥预制场建进了树林,日夜轰鸣,树林开始每天战栗。大型挖掘机开进了树林,一车车的沙石、一车车预制水泥板,运出了村庄。苦槠树失去了存活的土壤环境,也失去了昔日的容颜与风采。
今年春节回了趟我的小村庄,到树林里转了一圈,林地坑坑洼洼,破败不堪,剩下的几十棵苦槠树都已死去,却棵棵嶙峋铁骨指向天空,令人肃然起敬。 文/段元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