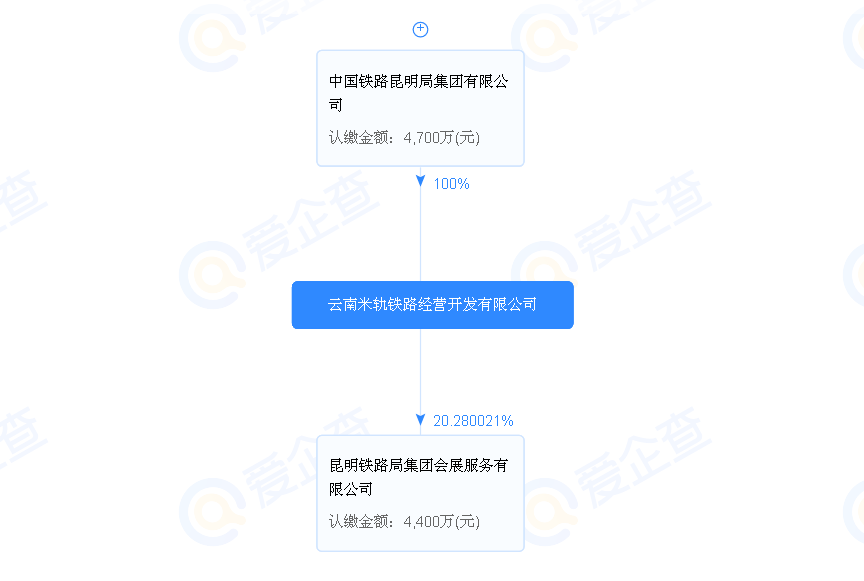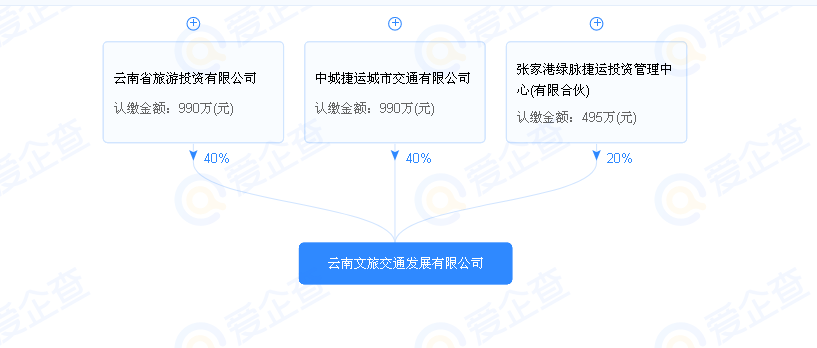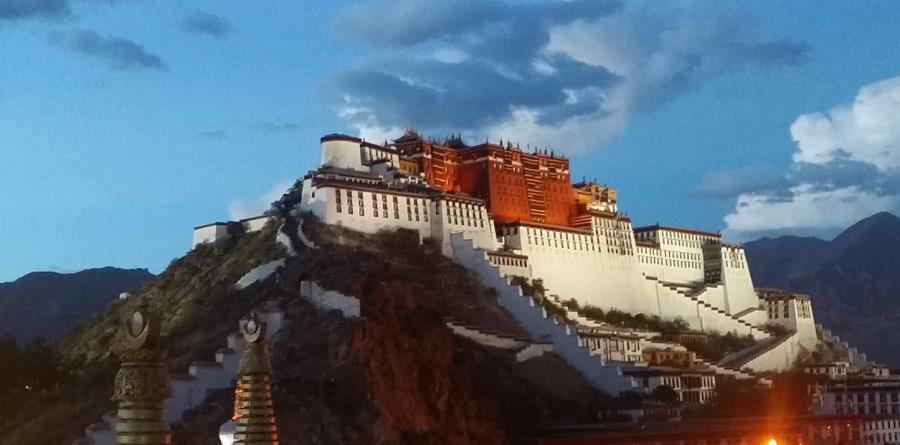8月2日,南都第九期数字经济治理论坛“新反垄断法上路,影响几何”主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围绕新法新增的“轴辐协议”规定,会上,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詹昊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此次新法对轴辐协议的补全,回应了执法的需求。”在詹昊看来,新反垄断法中有关“轴辐协议”的条款,并没有创设一种新的垄断协议类型。其核心目的是解决对垄断协议中不同行为主体(如组织者和帮助者)的行为界定,及确认相应法律责任问题。
1
平台通过规则和算法更易帮助达成垄断协议
8月1日,新反垄断法正式施行。其中涉及“轴辐协议”的新增规定受到不少关注,该条明确“经营者不得组织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或者为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提供实质性帮助。”
研讨会上,詹昊提到“武汉新兴精英医药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
该案中,某销售公司(下游经营者)与两家原料药生产商(上游经营者)单独达成独家销售协议后,大幅度提价。
“但由于无法将涉案上下游企业的行为同时定性,最终只能认定涉案的销售公司通过独家销售协议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对两家原材料公司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詹昊说。
“湖南娄底市保险行业价格垄断案”也存在类似问题。2007年,湖南娄底市保险行业协会组织11家财险公司与湖南瑞特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共同组建娄底市新车保险服务中心,规定所有新车保险业务必须集中在该中心办理,并划分各财险公司在新车保险业务中的市场份额,同时规定不得对新车保险给予任何费率折扣和优惠,并约定了相应的违约责任。
2012年,湖南省物价局认定湖南娄底市保险行业协会、11家财险公司与湖南瑞特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实施“价格联盟”,对当地新车保险市场构成垄断,涉案单位被处以219万元罚款。
詹昊认为,在这起案件中执法机构只依据《反垄断法》处罚了具有竞争关系的保险公司以及行业协会,没有处罚作为保险中介机构的保险经纪公司,折射出立法上的一些缺失。
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2月发布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规定也有涉及“轴辐协议”的规定。其中提到,具有竞争关系的平台内经营者可能借助与平台经营者之间的纵向关系,或者由平台经营者组织、协调,达成具有横向垄断协议效果的轴辐协议。
詹昊强调,平台运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具有纵向关系,利用便利的信息交流条件,平台内经营者之间更容易达成协同行为。此外,平台规则和算法也会起到重要作用,比如更容易达到价格调整的目的、降低垄断协议参与者背离横向共谋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由于平台独特的经营方式,尤其是算法和平台规则的存在,有可能使平台去协调其不同的经营者,最终促使他们达成横向垄断协议——这是我们对平台经济和横向垄断协议之间内在联系的一种顾虑。”他说。
2
平台应防范利用规则和算法,促成商家共谋
这样的顾虑并非没有事实依据。据詹昊介绍,在2016年的“苹果电子书垄断协议案”中,美国法院认定苹果公司通过分别与出版商签订代销协议的方式,参与并促成了出版商之间关于固定电子书售价的共谋。
据悉,苹果在开发出iPad和应用软件“电子书店”后,与美国五大出版商分别磋商并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传统批发模式的新的图书销售合作模式——代销模式。
在这种合作模式下,出版商将自家的电子书在苹果的“电子书店”中销售,苹果则提取销售额的30%作为佣金。双方还约定,出版商给苹果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如果亚马逊等苹果的竞争者以更低价格销售电子书时,那苹果也可以降价。
关于电子书的定价,代销协议约定采取“分层式最高价格”机制——即参考相同内容的纸质书的定价,将电子畅销书的定价分为两个档次。后来的事实表明,几大出版商对电子书都直接实行了顶格定价。
在欧盟也有相关的执法案例释出,一个典型案例是2016年欧盟法院审理的E-turas案。E-turas是一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向旅行社提供在线预订系统。2009年8月,E-turas通过内部的通讯系统向平台内的30家旅游代理商发出信号——要求“减少旅行折扣”,并将折扣率设定在3%以下。同时E-turas借助技术手段设定折扣上限:若旅游代理商提供超过3%的折扣,经系统处理折扣将会自动调整为3%。立陶宛竞争委员会认为,E-turas与旅行社实施了协同行为。
事实上,这样的行为在国内也有先例。为此詹昊强调,处于轴心优势地位的平台经营者,应该防范利用平台规则或算法,促成或帮助平台内的商家达成横向垄断协议。平台内商家也应该小心经营,避免竞争性信息泄露,对于自己交换的信息或作为轴心的信息应该有所保留。
如何认定“轴辐协议”?詹昊注意到,反垄断法的相关配套措施正在征求意见。其中《禁止垄断协议规定(征求意见稿)》明确和细化了“组织”和“实质性帮助”的认定标准及相关违法情形。即使不是协议方当事人,只要对协议主体内容的履行条件起到了实质上的决定和主导性的作用,也需承担责任。
以平台为例,詹昊解释道,如果平台干预平台内商家的自主定价行为,协调统一其价格和涨幅折扣,即便没有直接参与达成垄断协议,也可能受罚。
但对于“实质性帮助”的定义,詹昊认为现有规定还存在一定欠缺。比如具体何种类型的支持行为、何种程度的作用将被认定为作用“显著”,以及如何证明“因果关系”还有待细则明确。
采写:南都记者樊文扬 李玲 黄慧诗
出品:南都反垄断课题研究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