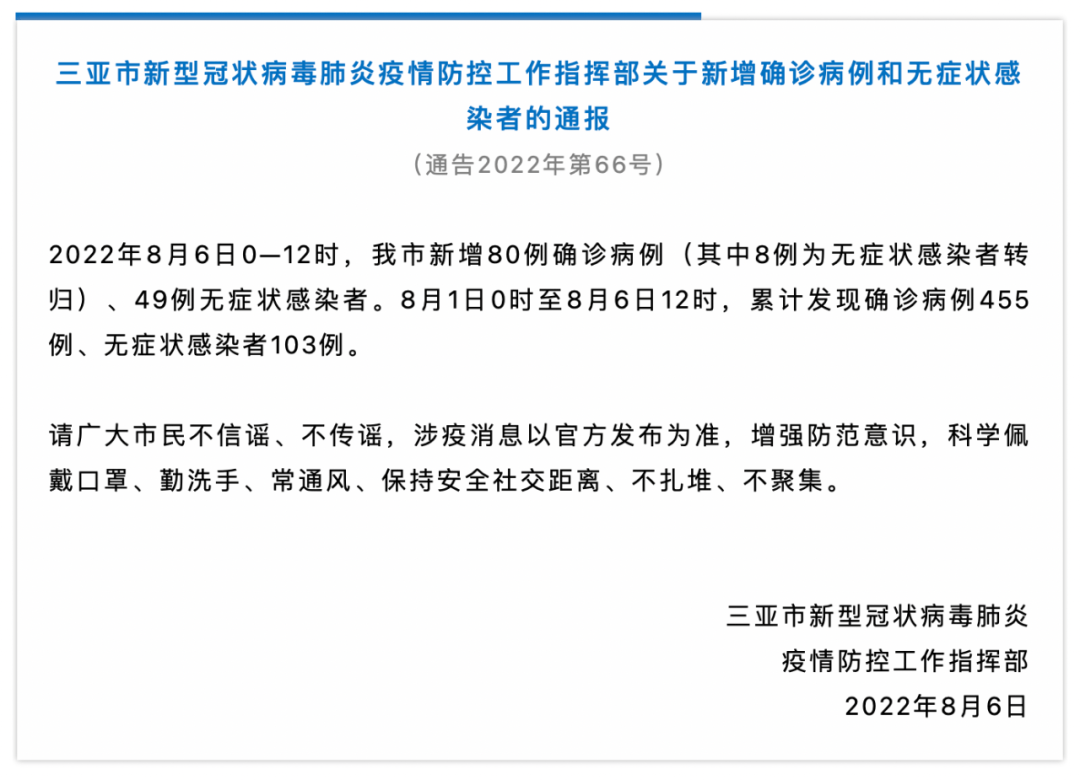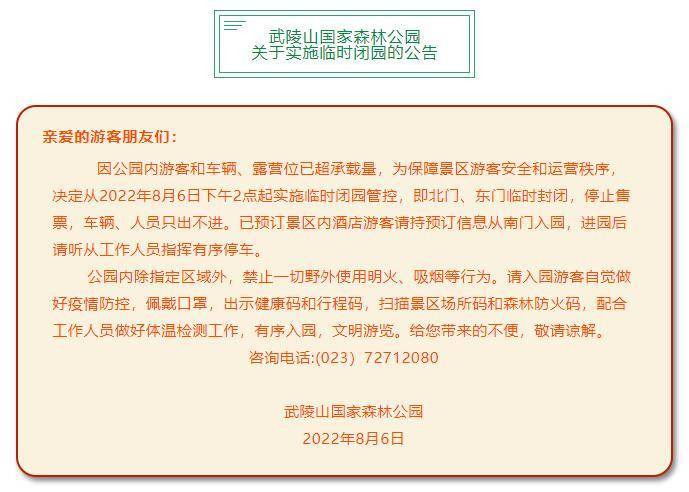我的花园,我的老街
伊禾
七月之末的清凉夏日,我走在午后的街头。确切地说,这是一条老街,很多年前我选择这条街住下来,也许就是它花园村的名字令我怦然心动。花园总是芬芳的,与其说我走进了一条街的名字,倒不如说我希望从此以后的日子芳香弥漫。
微风卷起地头的热浪,顿感暑气升腾。从太阳镜后打量,困乏的老街在烈日的炙烤下带着些许疲沓,偶尔几个行人从马路上走过,显出少有的静寂。
“唉,花园村这条老街,好多地方都变了,又像很多年都没咋变。”我心里嘀咕着,快步来到十字路口。
倏地,一道熟悉而别样的景致嵌入眼帘:几个穿着朴实的中年妇女,在一架玻璃棚搭建的简易摊旁,坐列成整齐的一排。每人面前摆放着一台黑身木质面的老式缝纫机,只见她们双手摁住一件正在缝制的衣物,不断地往缝纫机的针床下运送。“笃笃笃”,霎时传来机器走线的声音,时而,又抬起右手快速地翻转机车轱辘,脚下同时发出“哒哒哒”踩踏板的响声。
“老师,你放假了呀?”中间那位大姐朝我热情地寒暄。
“是啊。大姐,您好!麻烦帮我看看这两件体恤,穿着肥大了点,看能不能收两根腰线,再卷个边儿?”我拎起兜里的两件旧衣,笑嘻嘻跟大姐攀谈。
“要得,我量下尺寸,一会儿就好。”大姐娴熟地操起卷尺,顺势圈住我的腰围,用手卡了两下,再用画粉条做个标记。然后剪裁,缝制,卷边,走线,熨烫……一系列动作麻利且干净,感觉那些旧衣就像她手里的珍物,不急不徐,温柔以待。
明晃晃的玻璃棚,并不见得防晒,炽热的日光晒射到大姐脸上,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在湿透的发丝上打颤……忙碌的大姐来不及擦拭,嘴上招呼客人,手却一刻不闲。
一小会儿工夫,两件旧衣就改制出炉了。
“好多钱?可以刷微信不?”我牵扯着两件改头换面的旧衣,满意地点点头。
“可以,支付宝、微信都行,就拿十块就是,老熟人了。”说完这几句,大姐脸上充满和善的笑意,问我:“你看起来没变,怕都教书好多年了吧?”
我努力搜寻脑海深处的记忆,不知眼前的街坊大姐姓啥,只知她一直做改衣行,在自家楼下狭窄的过道摆摊。从我随父母工作调动搬迁到花园村时就认识她了,那时我才十四五岁。
刚来时,感觉花园村好大,几十幢高楼耸入云端,周围大大小小的工地聚满民工,推土机“轰隆隆”地来回奔忙……站在野花遍地的小山坡上,母亲指着右前方对我说:“三妹你看,前面过石门大桥是沙坪坝,往左走是花卉园,再往前两站就是观音桥,这个地方后劲足哦,以后会越来越闹热。”
身为土生土长的重庆渝北人,心里的确有几分难以抑制的自豪。比如穿着优雅时尚的你,从花园村出发,走进江北T3航站楼,登上偌大的飞机满世界飞,你心里自然有种说不出的傲娇。再比如外地畅游回渝,机落的那一瞬,望着窗外熠熠闪烁的万家灯火,你有没有忍不住感叹:哎,在家千日好啊!
每次归来,总是更加热爱我的家乡。我生活的这个地方,现在被称作临空之城,无论站在哪个角度俯瞰,它都显得古朴雅致,山水如画,绝对值得晒。而我却总是想起它最早的那种青涩,那种乘舟欲行的决绝,那种含苞欲放的灵动。那就是初心,在老街,在乡村,在生活的每一个细微处。
花园村就这样脱颖而出,但现在仔细观察,又觉得花园村变小了。高楼大厦和住宅小区林立其中,广场、酒店、社区、医院应有尽有。当年的小土坡摇身一变,出落成大龙山公园,周围新建了好几所公立学校。
“大姐,收十元钱太少了吧。就你这手艺,要是跟商场的大品牌合作,起码多收好几倍。”我有些过意不去,对大姐说。在我熟悉的花园村买菜购物,我几乎从不讲价,也不问价。买完了,老板说多少就是多少,好像心里笃定街坊四邻不会蒙我。
“这么多年都这样收的,习惯了。现在都是流水线操作了,还有的买了迷你缝纫机自己在家改,以后我们这行,怕是没有人做啦。”听了大姐的话,我鼻头有些酸楚。
那次之后,我回家又翻箱倒柜找出一堆旧衣,有的熨烫,有的改良,去惠顾大姐的生意,跟她们唠家常。有意思的是,我随便拿给哪家整改,她们都手艺一流,收费厚道。一直守着本分,在低微的角落里与世无争,勤勤恳恳。很难想象,在如今买菜都刷微信的大数据新时代,还有她们这一类手艺人的存在。
常听楼下的邻居感叹:“住在我们花园村好啊,方便,闹热,干净,下楼就是菜市场,出门就是好吃街。还有修表的,弹棉花的,改衣服的,啥子老本行都在!好多老手艺现在根本找不到了,我们这里都还有。”言语间,是毫不掩饰的自得和满足。
我忽然生出几丝隐忧,杞人忧天地想,如果有一天我们再也寻不到棉花匠的踪影,找不到一家称心的改衣行,那我们的生活该失去多少的便捷与温暖?
其实每一种民间手艺,都蕴涵着文明的积淀,它们铭刻在生活每个角落的记忆,总能牵动着很多人的顾盼。在城市嬗变的间隙里,它们貌似悄无声息,却又常常投射出独特的光芒。
我慢慢地向着远方走。或许,老街确乎有些显老。但我想说的是,当老街在一块版图上变得小起来的时候,城市的璀璨,正在以我们曾经梦想的方式,犹如繁花一般在原野上盛开。
(作者系渝北区作协会员)
版面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