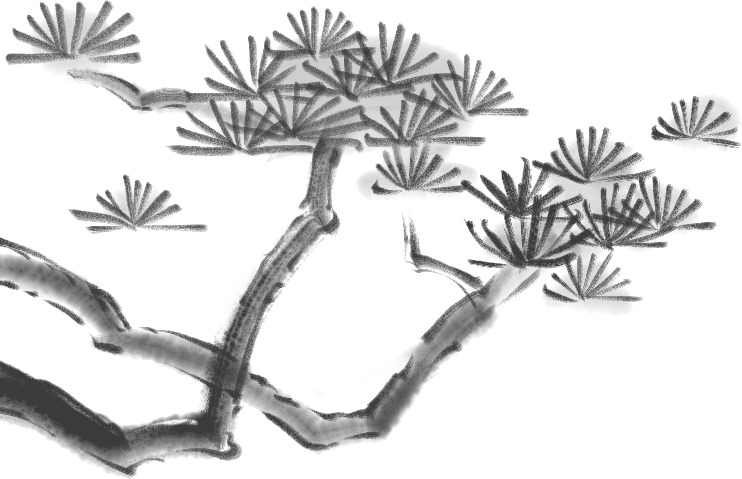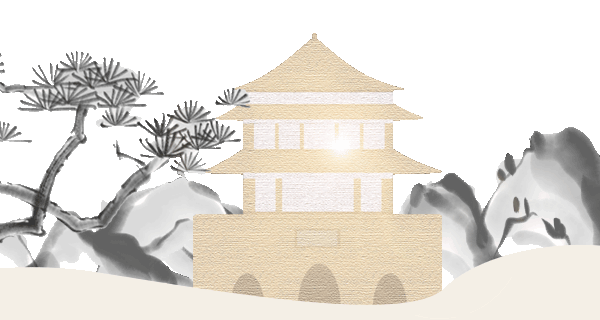编者按
人是旅行的动物,也是讲故事、听故事的动物。“旅行文学”在给我们讲故事的同时,也邀请我们,让读者在诗与远方的召唤下,去追寻更多可能的世界。
红星文化邀请莫言、阿来、迟子建、李娟、罗伟章、龚学敏、胡成等作家,用他们笔下的文学,经由途经的地理,构成我们这个夏日的一次读行。
在这场意犹未尽的夏日读行之旅将尽之时,我们特邀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西湖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德明先生,一同探讨“当代旅行文学”。他曾在著作《旅行文学十讲》中通过文字重现人类千年旅行文学史。那么,如今的旅行文学又有何种倾向?我们该如何看待如今的旅行文学?
以下为张德明教授关于“当代旅行文学”的观点。
到心灵的漫游
从文本、身体
张德明
立秋一过,日光渐斜,但暑气依旧,蝉声急急,走出都市的人们抓紧最后机会,在草原撒野,在海滩冲浪,在长江邮轮上赏景,在古镇民居、乡村农家乐避暑;更有体力强健者,踏上了自虐之路,寻觅古道废墟,指点江山;徒步雪域高原,考验意志和耐力……
我一向认为,无论对个人还是民族而言,旅游或旅行,都是释放剩余能量,让梦想照亮现实、想象超越当下的举动。一个生命力萎顿的人,不会产生旅行的念头;一个视野狭窄的民族,也不会鼓励自己的国民出国。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旅游业是当代中国崛起的历史见证者、积极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首先是一些感官特别敏锐、生命力特别强旺的个体,迈开自由的脚步,走出家门,开始了穷游之旅。1989年2月崔健创作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传遍了大江南北,激发了一大批荷尔蒙满满的年轻人变身为“假行僧”,他们一无所有,却情愿为了寻找花房姑娘,而踏上了自我启蒙和探索之途。他们只想“从南走到北,从白走到黑”,他们“要所有的所有,却不要恨和悔”。从这个意义上说,崔健不仅是中国摇滚的教父,也可算得上当代中国旅行文学的先驱之一。
以2011年中国旅游节的设立为标志,中国的旅游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国人钱包的鼓起,剩余的精力和能量越来越充盈,急于找到宣泄和释放的出口。精明的商人瞄准商机,适时跟进,配合中国崛起的节奏和方兴未艾的国学,开始热切地考察、寻觅、踏勘和设计,将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建构为旅游景点,为破败的城墙、古道、古镇、古庙、古村寨一一找到相应的历史定位,让它们成为集怀旧、审美和治愈于一身的场所。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的扩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旅行平台,它们鼓励旅游者以自己的手和眼睛写下旅游攻略、沿途观感,摄下美景美食,传于网络空间,与人分享。如果我们不那么拘泥于学院派的定义,也理应将它们归入旅行写作文类,但由于其体量庞大,且大多呈碎片化状态,无法统计、引用、分析,只能存而不论。就相对狭义的旅行文学而言,据笔者粗浅观察,出现了三种主要的倾向。
借助名家名作的读与游
旅行和文学,是一对天然的孪生子。我们很难相信一个足不出户的人能讲出什么故事,也很难相信一个走南闯北的人说不出点儿奇闻逸事,哪怕他人再笨,口再拙。其实许多情况下,我们是先读书,再上路的。先知道有孔乙已,再去绍兴咸亨酒店喝酒,吃茴香豆。先读了莫言,才来到秋天的山东,去高密看满村的红高粱。硬件必须配合软件,空间必须注入历史,通过文学的讲述,才能成为人类活动的镜像,吸引游客前来膜拜、怀旧和消费。纯粹的自然风光固然也吸引人,但缺乏本雅明所说的那种经历史打磨后的“光晕”。
我曾在不同的时间点,分别在美加两国观赏过尼亚加拉大瀑布,但当时只有激动,没有感动,更没有写诗的冲动。因为再壮美的风景,缺乏人类活动的痕迹,只是一堆光影和色彩的颤动。相机能记录的,只是瞬间的物理之光,而缺乏人的目光和思想的穿透力。黑格尔说过,人之所以为人,一定要在自然中打下自己的烙印,看到自己“精神的对象化”,心理才会满足。而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做到的,正是这一点。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字面意义上的“阅”历和“履”历同样重要,同样值得珍视。
考察历史地理的独游
2016年,53岁的北大历史学家罗新,一位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的专家,做了一件他惦记了15年的事——从大都走到上都。他自北京健德门启程,沿着古代辇路北行,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用了15天的时间,一步一步用脚丈量了450公里的河山,抵达上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归来后用一年时间写成并出版了《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全书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虽会比较累,但读完后的愉悦感是实在的,收获是良多的。书中既有细密的考据,旁征博引的趣闻,又有途中生动的观感和对当下的反思,使我想起了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那本著名的南美游记《忧郁的热带》。
另一位旅行作家刘子超,在2020年,前往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归来后写出一本22万字的游记《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很快收获学界的一片赞叹。许知远称他是“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游记作家”,罗新则评价这本书“为今后的旅行写作树立起标杆”。
挑战自我、拓展人生的自虐游
旅行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充电器”和“安全阀”,其功能之一便是帮助都市居民舒缓日益加剧的生存焦虑,治愈因疏离感和孤独感带来的精神抑郁。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平,丰富多样的人性变得越来越单一、趋同和萎靡不振时,对奇崛、差异和刺激的追求就成了人的深层渴望。在一些旅行者眼中,相隔时空越是遥远,行程越是艰苦,文化和地理景观反差越是巨大的旅行,越能提供持续的生理和心理能量,激活潜伏在灵魂深处那头永不安分、渴望刺激和行动的小兽。这就是为什么当下许多公司定期组织员工在荒郊野地创办训练营,推出拓展课程;而一些大企业、大公司的CEO们则热衷于作自虐性长途旅行的根本原因。对此类现象作“仇富”式社会学解释无济于事,认真对待和深刻反思才是旅行者应有的态度。
在当代中国文学家/诗人中,我发现了一位将自己的旅行生活“完全诗化”的诗人——黄怒波(骆英)。这位集企业家、登山家和诗人三种身份于一身的作家,在2011年出版了一部诗集《7+2,登山日记》。在这部作品中,他以诗的方式逐日记录了他6年间登上世界七大峰和南北两个极点期间所经历的情感和思绪。诗人抛弃纷纭的俗虑,摆脱了各种眩目的社会角色,直面残酷的大自然,在冰山雪峰上与真实的自我对话,与死去的相识和不相识的登山队友对话,毫不避讳地记下自己在面临生与死的抉择、滑下冰峰或跌入深渊的考验时,所经历的恐惧与战栗,放弃与坚持,也忠实地记录了跋涉的痛苦与疲累,登顶的兴奋和欣喜,下山的感悟与思考等。诗人将每一个登山的日子都变成了诗,将极端的生存体验“完全诗化”了。
宫崎骏说,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长夏即将到头,秋光将更灿烂,让我们读起,走起,来一场从文本、身体到心灵的漫游。告别信息茧房投喂给你的各种精神垃圾,用肉身体验代替二手阅读,从单纯的“知”,走向真正的“识”,进而让自己的生命变得前所未有的充实,丰满和喜乐。
(编辑 段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