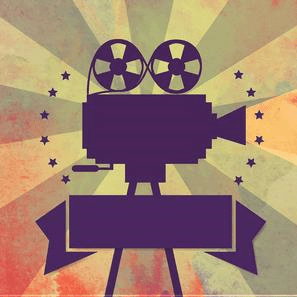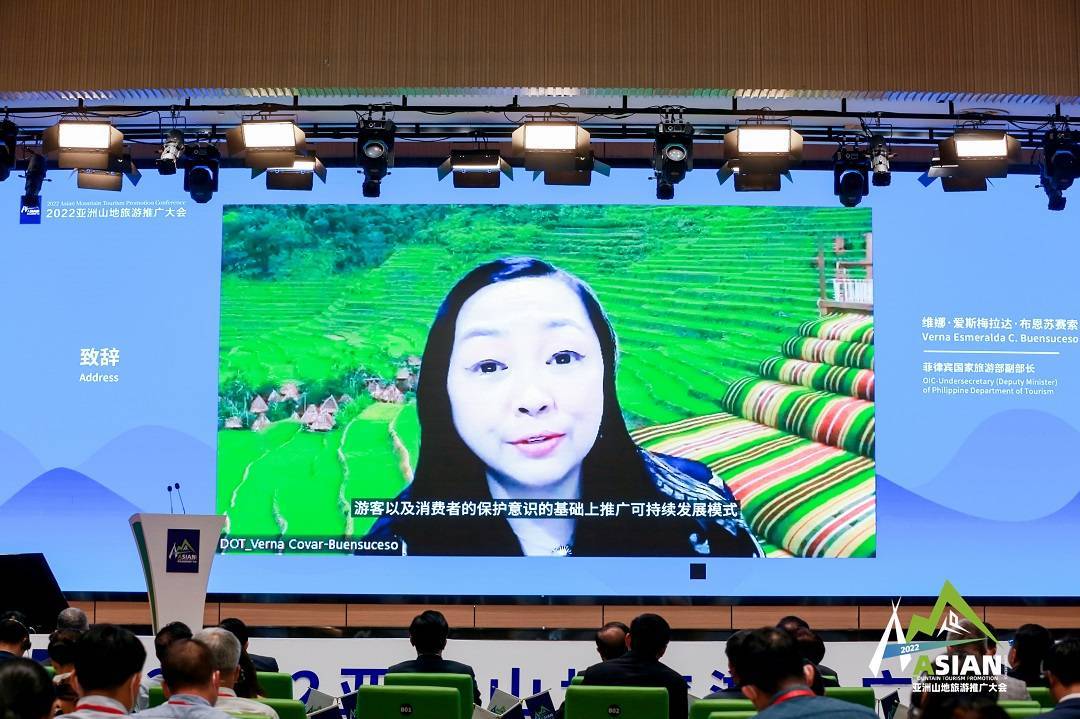一城梧桐,醉了一座江南的古城;一片绿意,邂逅这个夏天的诗意;一次相遇,诉说金陵人的情怀……
“凤凰生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这是《诗经》梧桐引凤凰传说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提到梧桐,相信很多南京人脑海中呈现的多半是南京钟山风景区那条雄伟壮观的美丽大道——陵园大道的“梧桐”,也就是很多南京人所称的“法桐”,高大挺拔、雄伟壮观,一派庄严肃穆。
20世纪20年代末,为迎接孙中山奉安大典,南京的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和陵园大道规划了国内第一条现代意义上的林荫大道,行道树选择的就是“法桐”。在时任总理陵园管委会园林组主任傅焕光的主持下,经上海口岸引进了大批二球悬铃木树苗。南京的悬铃木既有产自北美的一球悬铃木,也有产自英国的二球悬铃木,但产自法国的三球悬铃木几乎未见。因近代以来法国人最早将悬铃木栽种到上海,从而有了“法桐”之名。其作为行道树而闻名,则是南京独特的城市记忆。
这些梧桐行道树,伴随着南京城百年的变迁,是“土生土长”的“金陵人”,百年的成长,让他变得沉稳高大,斑驳的树皮,随处可见岁月在它身上的印痕。树叶恣肆地生长着,夏日闪亮的阳光下,绿伞如盖,绿荫熠熠;“一叶知秋”,秋天的风里,满金陵城的金叶飞舞,醉了一座城。它不招摇,没有绚丽的花朵,果实如球,小时误以为是荔枝,也是闹了笑话。这些梧桐行道树,存在于每个南京人的日常,日日相见,日渐熟稔,成为南京人的集体记忆与生活志趣之一,成为绿城南京的底色,也成为南京历史文化遗产不可磨灭的一隅。梧桐之于南京,南京之于梧桐,唇齿相依,相互成全。
梧桐和南京一样,诞生在美好的故事里。从秦朝开始,神秘的方术对着王座上最有权势的男人窃窃耳语,言金陵龙脉之地,王气充沛。这似乎是莫大的荣耀,但也是一种诅咒。也许从秦始皇在这南京城埋下万千黄金时,龙脉就可能被压断了,在这片石头上建起的王朝,面对厚重的历史,只能匆匆带过几笔。她令人着迷和堕落,是风情万千的女人,秦淮河上幽幽商女之音,飘飘荡荡过了宋齐梁陈。朱棣匆匆地来,嫌恶又有点理亏地瞥了几眼,又匆匆离去了。怀抱着丰满而又浪漫理想的太平天国,一路浩浩荡荡杀进金陵,宏图伟志又渐渐地埋葬在缓歌慢舞的丝竹声中。
但她的伤痕也是触目惊心的,亲历了日本侵略的耻辱时刻,记下了侵华日军大屠杀的滔天罪行,也抹不去这场屠戮带来的悲伤。随处可见的法国梧桐,见证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南京的快速发展,日新月异。如同一个成熟的女子,不再青春,但美丽的眼眸里充满着故事,变得更加沉稳、丰厚、知性和内涵。
前两日,去了扬州,一片白墙黑瓦、绿水幽幽,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扬州的柳,柔顺、妩媚,像少女的长发倒映在绿水,一圈圈的涟漪轻轻拨动游人的心弦。“一种垂柳万古情”,扬州的垂柳,在古代文人墨客笔下,留下诗词无数。垂柳之于扬州,如梧桐之于金陵,都是城市的名片,城市的格调,城市的历史文化意境。
走在盛夏傍晚南京的街头,“火炉”的威力是名副其实的,刚下一点雨又停了,热气托着水汽飘起来,朦朦胧胧,配着梧桐此时的绿,凝成一片绿烟,若有若无地弥漫着。年轻的我,仰望如长者般的梧桐,总会想着各种各样的可能的活法,最好是前人从未有过的,循规蹈矩的锦堂风月和功成名就姑且不谈,佯狂披发不容于世,魏晋时也不乏其人,在心里升腾起的一股怀古之情。
文化的古韵,金陵的气节,从我儿时,被韵染着。江宁织造府的云锦,“寸锦寸金”,超高的艺术价值,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的盛况。在国防、科学、教育发展和研究的道路上,邓廷桢将军是清末著名将领之一,在鸦片战争中对禁烟有着巨大贡献;吴良镛院士协助梁思成建立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赵仁恺院士作为中国核潜艇副总设计师之一,为中国的核动力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传承的,不是文化的形式,而是内在的精神内核。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创新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形者,气之所聚”,没有暮春之初那曲水流觞的浪漫,哪来千古梦绕魂牵的《兰亭集序》?没有那海纳百川的包容的笑,哪来唐代各类狂才肆意挥洒?我们青年一代可以静下来,于无声处感受精神内核的初心,在一片静穆中,体会那份“千秋一寸心”,才能用心用情书写伟大时代。我和陈子昂相反,我好像看到了无数的古人,也看到了无数的来者,念天地之悠悠,奇峭绝拔,超脱于世,四海之大,任而遨游。把渺小的自我投身到古今的长河,一下便只有震撼和浸润,从宏观的大中,寻求微观的小,感悟生活的意义和历史的使命。
看着眼前的梧桐,平凡地静默在道旁,高大苍翠。人不用刻舟求剑一样去追求过去的辉煌,生活就在眼前,万物的兴盛荣枯,皆在于脚下的土壤,梧桐向金陵人传递着生生不息、历久弥坚的力量,在生活里感受着生命的意义。
绿烟灭尽,梧桐如故,金陵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