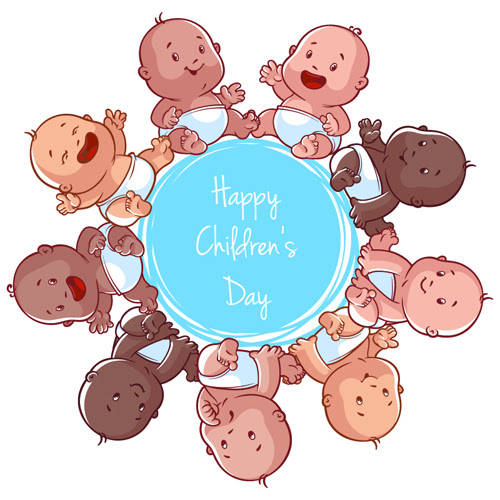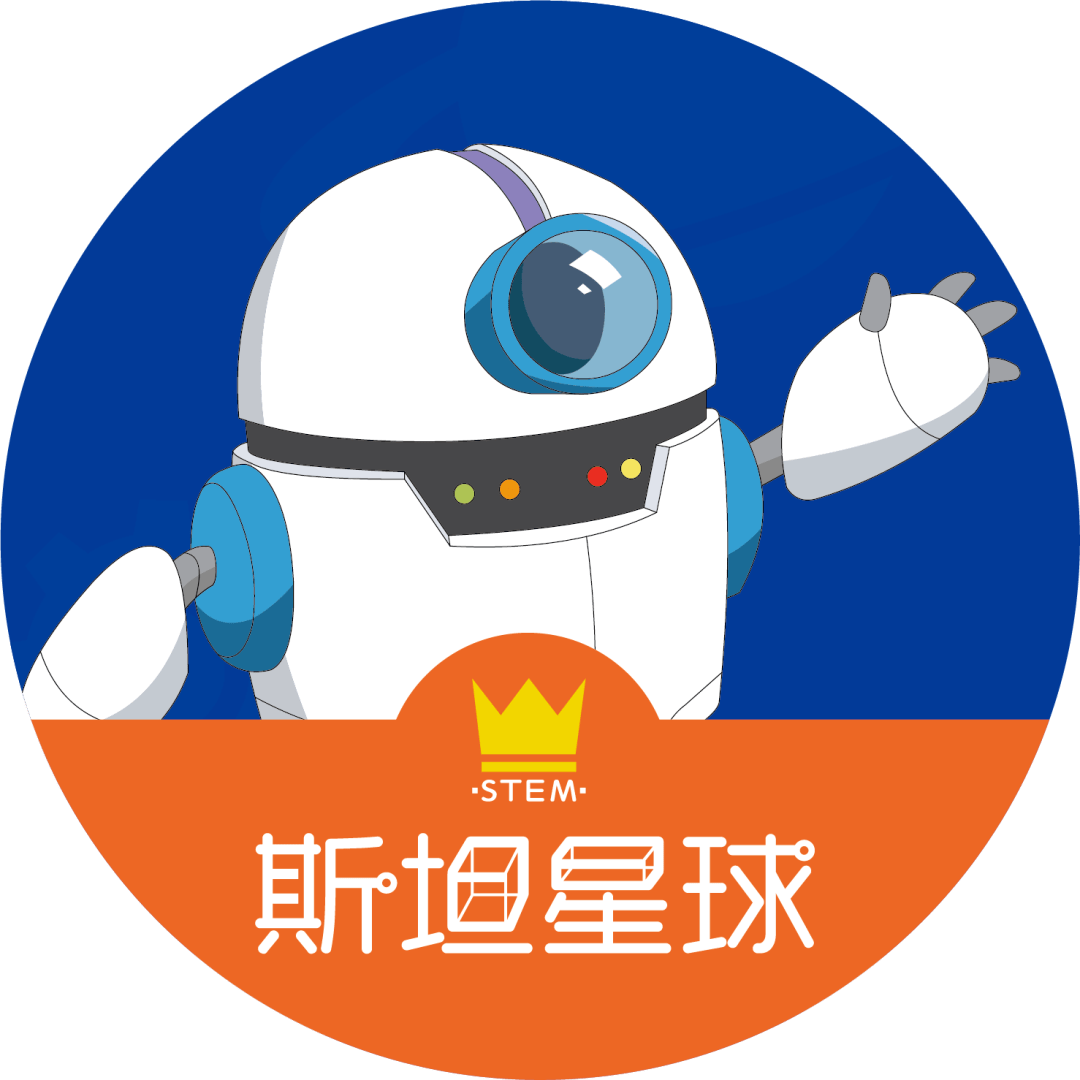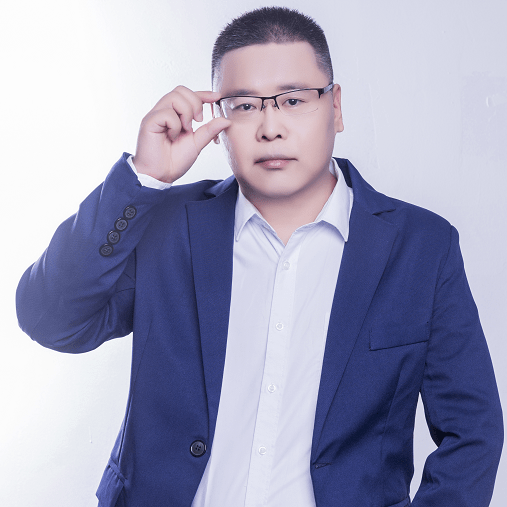参考消息网1月16日报道(文/约翰·哈里斯)
如果说节日往往等同于长时间窝在室内,舒舒服服蜷在沙发上,无休止地刷剧,那么我们在新冠疫情阴影下度过的假期大概会将这些发挥到极致。世界缩小了:生活中尽是谨慎的亲友、取消的行程和就地过节的要求。寒冷和黑暗也来凑热闹。和去年一样,疫情下的节日可能又会成为一个闭门不出的节日。
为了暂时逃离这种困境,会有数千万计的人出门散步,这既是许多人过节时雷打不动的内容,也与我们许多人这两年的生活状态吻合。当我们突然没有了可供选择的休闲方式,自然而然会从最原始的消遣中寻求慰藉。
无论何时何地,随时可以加入。我喜欢散步,也深知自己能这么做有多么幸运,我无法想象不能散步的生活。这种习惯在我孩提时代就扎下了根;等到二三十岁住在伦敦后,我最终成了相当坚定的城市行者。不过直到我离开伦敦,有了自己的孩子,散步才逐渐成为每周必有的活动,让我可以借此恢复元气。
与我的两个孩子一起(我知道,他们迟早会离开,剩我一人散步),大部分的星期天早晨,我都在住的萨默塞特附近闲逛。如果时间更充裕,我们还会参观许多其他地方:达特穆尔、布雷肯比肯斯山、与温切斯特和伊斯特本之间的海岸平行的南部丘陵。但在过去的两年里,由于新冠疫情的限制让我们待在家里,我们的幸福感与探索周边环境和发掘家门口的事物的小乐趣息息相关:古老的墓地、废弃的运河、萨默塞特旧煤田的迷人环境。
乡间漫步是父亲让我养成的习惯,他当年热衷登山,是矿工的儿子。父亲之所以迷上散步,与他的哥哥有关。那时候,去乡下徒步是闪耀着阶级政治光辉的事情。1932年发生在皮克区金德斯考特的大规模侵入事件更是让矛盾激化(工人阶级散步的权力与富人对荒原专属权之间的矛盾——本报注),那场有组织的公民抗命运动给英国带来了多项进步,其中之一就是国家公园的出现。漫步植根于这样的抗争——更别提成千上万工人阶级付出的生命——这与它日后被冠以资产阶级消遣方式的名号背道而驰,而这些激进的暗流从未真正消失。在本地的散步小径保护协会和漫步者协会分会开展的日常活动中,经常能感受到当年让金德斯考特侵入者共同行动起来的力量。
散步也是日益壮大的多元政治叙事的关注点,而要让它真正成为大众休闲方式,仍然需要促进参与者的多样性。就在圣诞节前,我和居住在考文垂的年轻社工切蕾尔·哈丁聊了半个小时,她最近成立了一个名叫“英国步行者”的组织,目的是帮助“黑人、亚裔以及少数族群与户外活动建立积极关系”。
至于为什么散步——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会触及漫步者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有一个简单到动人的答案。正如作家兼虔诚的行走者伊恩·辛克莱所言,用脚去丈量需要“你向全世界打开你自己,让皮肤变得通透,接纳外界给你带来的种种感受”。我们都知道前行路上有什么障碍:偏见、车流、紧锁的大门、写着“私人领地,禁止入内”的警示牌。
我还想到最近两年流传的一些故事,据说热心过度的警察阻止人们外出散步,尽管这样的做法根本不会给公共卫生带来威胁,这是困守家中的人们与外界保持联系的为数不多的渠道之一。新鲜的空气,固有的社交距离,还有从一个点移动到下一个点所带来的不大不小的惊喜:作为让人免于愁眉苦脸、与世隔绝的方式,谁会对此有异议呢?(李凤芹译自2021年12月26日英国《卫报》网站,原题为《散步是一种绝佳而原始的消遣——远比你以为的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