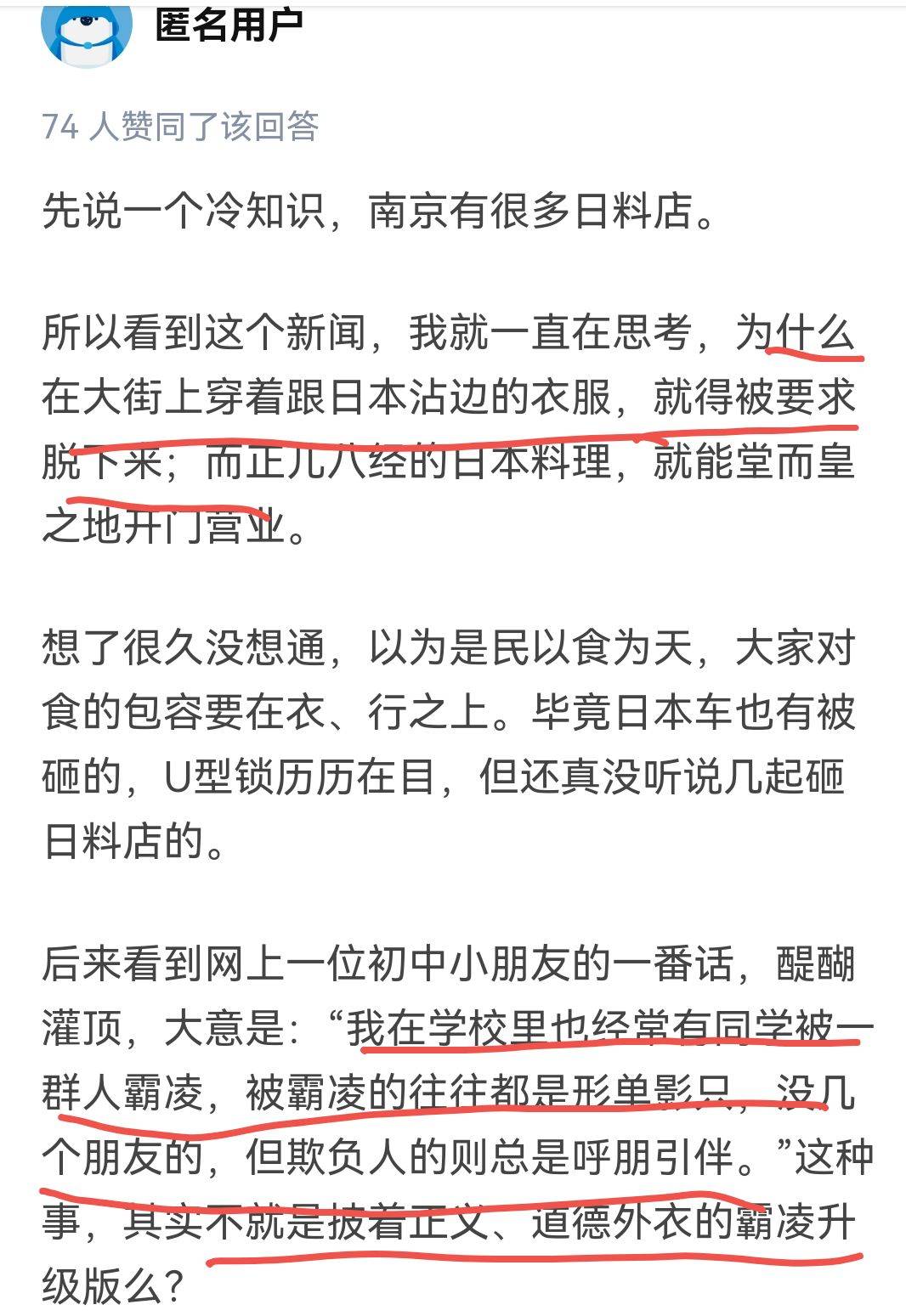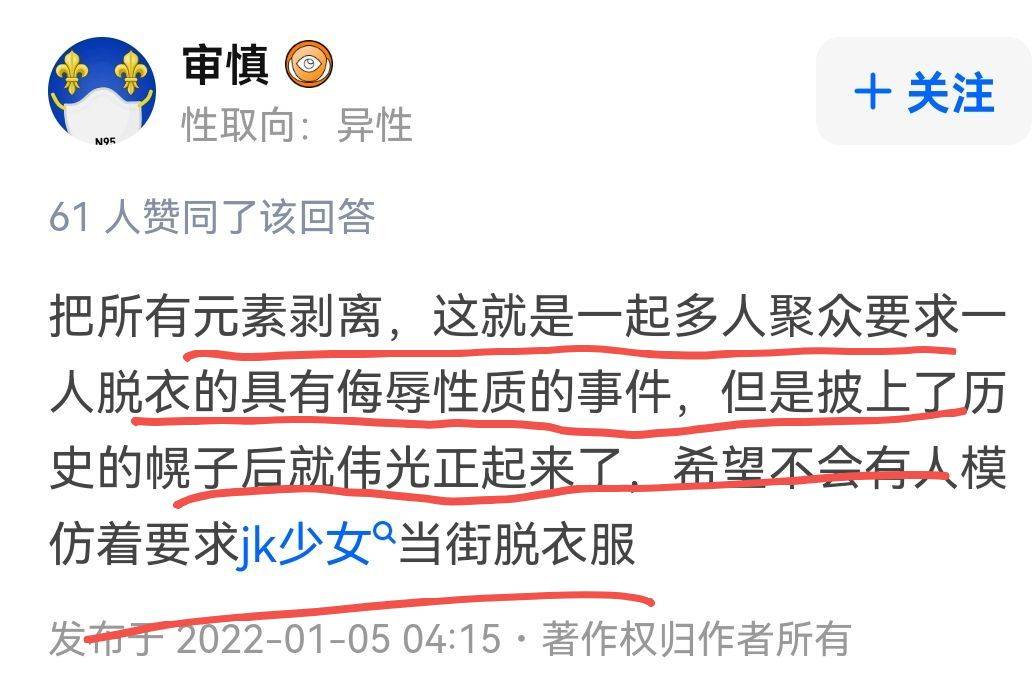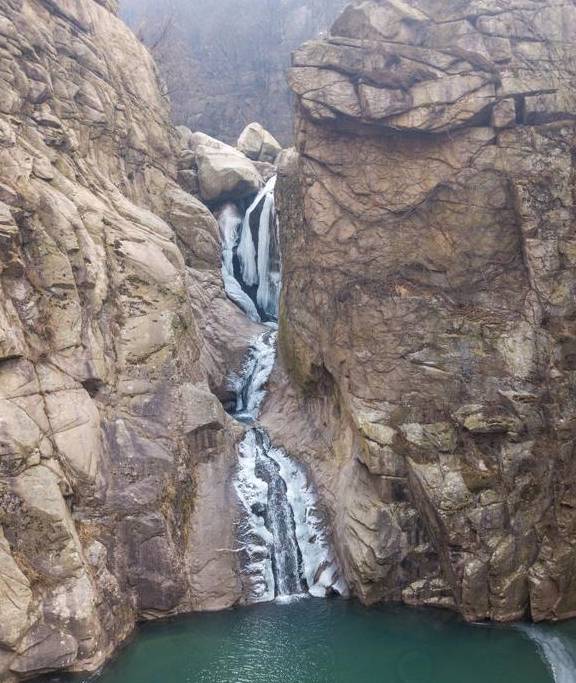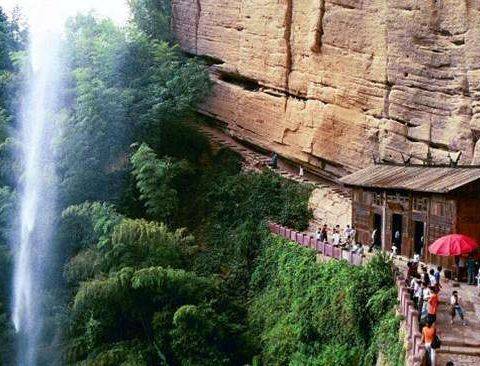流浪
阿梅记得,蒋勋老师在台北游学的时候,曾说:《春江花月夜》所展现的,是一种旅途当中的流浪感。然而,在他看来,更宏大的流浪,应像是佛经里所说的“流浪生死”,是生命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流浪之感,是经由生命的无常而产生的那种真正的惆怅与愁绪。
去王洛宾音乐艺术馆并不在阿梅的朋友叶开当时的行程安排内,只是后来在西海镇上闲逛,一条路一条路地走下去,一不小心就走到了馆前,在一个角落里,在王洛宾先生的后半生的某一阶段的描述中,叶开看到了几张照片,他记起以前谁说过的,三毛其实蛮漂亮的,个子高挑,长发飘飘,发里有五湖四海不同国家的味道,这个万水千山走遍的人呵。
阿梅知道,少年时的叶开曾有一个愿望:18岁之前要去一趟敦煌,去看看三毛,去同她告个别,为她在他的青葱岁月里所给予的无数向往而感念她,也为他的青葱岁月和这青葱岁月里曾有过的向往告个别。
叶开攒够了钱,计划了行程,阿梅还记得他当时买的防晒霜是什么牌子的,然而终未成行。
于是叶开就有了第二个愿望:20岁之前要去一次周庄。周庄有一个茶楼,三毛曾去过了的。他甚至都已想好了在茶楼的留言簿上将要写给将要说与三毛听的话:“亲爱又亲爱的三毛,在这人生路上,这茶楼你曾来过,经年之后,我循迹而来。我在此恭候,就请你魂兮归来,我们见一面就好,这一面,你是滴雨也好,是片云也罢,是船娘唱起又唱落的船歌当中的一个调调也好,是陈逸飞油画当中的某一笔油彩也罢。只要当有一滴雨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起了莫名念想就好;只要当我抬头看见片云的时候,看见了异彩就好;只要当我听船娘唱着船歌的时候,脚步开始停留就好;只要当我平视这油画的时候,眼皮有了跳动就好。就好的意思就是,你的魂魄归来过,而我恰恰就在了”。
2009年年初叶开去了江苏,在苏州太仓,2010年7月去往周庄,在河边的水草都忙着结婚生子的时候,他已然不知道该把那些话说与谁听了。
少年郎
阿梅还记得那年三毛从台北到彰化来游学和演讲,爸爸带自己一起去。说起来,爸爸也是年轻过的人呢!
今天,爸爸难得的穿上了西装。阿梅扭过头去问阿哥:“哥,你之前有见过爸穿西装吗?”阿哥正长长出神,没功夫来理会小妹,于是小妹阿梅自问自答:“爸穿西装,还蛮帅的哦!”
阿梅望着安详入睡的爸爸,在心里同道士一起默念:爸,今嘛你的身躯拢总好了,无伤无痕,无病无煞,就像,少年时欲去打拼。
今天,第七天,寅时不行,因为阿哥属马,因为阿梅属猴,犯冲。于是改到了卯时。卯时已到,送葬队伍启动。阿梅听做法事的道士说,爸爸在这一天会回来。于是,一有机会,阿梅就张目寻找。
在哪里,爸爸?阿梅在心里探问。
爸爸,你是我这么多天以来张着黑伞护卫下的亡灵抑或亡魂吗?
爸爸,你是我放下伞后从天而降跌落在我面颊上的第一滴雨吗?
爸爸,你是现在一直在告别式现场上空盘旋的那只纹白蝶吗?
爸爸,你是此刻吹唢呐的乐师调调里面不经意间的那一个滑音吗?
爸爸,你在哪儿?
山中少年今何在?
时间
半夜,为爸爸保鲜的冰库送到,压缩机隆隆作响,电压过大,不停跳闸,阿梅索性点起蜡烛,剪灯花的时候,无端想起吴文英的《祝英台近》,有人添烛西窗,不眠侵晓。
那个有人,现在倒换做了是我。阿梅心想。
残日东风,不放岁华去。阿爸,我也不想放你去啊。
阿爸,还记得吗?以前,每逢你送我去彰化甚至台北上学的时候,临了,总不爱说“再见”,就只是说“回见”,因为阿爸你一直相信没有什么事物会真正消亡,没有。
女儿没有如期归来,见您最后一面,是不是因为这个,在第七天的时候,阿爸你也没有如期归来?你没有如期归来,据说,这正是离别的意义。而当我同你就此说再见而再不说回见的时候,时间也才产生了意义啊!
做了道士的阿义哥哥背包奔赴异乡为乡人收尸,在火车站,阿义哥哥又开始写诗:在钟点坏掉的时间中/在火车迟点的时间中/生命/走到了最终……
阿爸,是不是属于你的时间早早地被安排,出演了一场意外?而后,你悄然走开,化成一缕香,你的模样,就此,随风飘散。
阿爸, 现在只我一人走夜路了,时不时抬头看星,星辰早黯淡了,如此的道路绵延无尽头,空间无尽,时间无尽,我的眼泪就要掉下来,而我也只能不回头地走下去了。
代理
那天,阿梅还在上班,接到哥的电话,告知说阿爸不再了。短时间内交接了工作,请同事苏菲代理,自己尚着一身职业装,就这般风尘仆仆归来了。
那天,哥还在夜市摆摊,接到医院值班医生的电话,告知说病人林国源先生呼吸衰竭,没有生命迹象了。短时间内交接了摊位,请隔壁做牛排的胖子代理,自己着一双人字拖,就这般慌不择路赶来了。
往常,在阿梅的印象当中,总是爸爸载自己上下学的时候多一些,爸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总是吓得阿梅哇哇叫,爸爸反倒是爽朗地笑了。
告别仪式上,祭奠主位要放爸爸的生活照,爸爸在那里爽朗地笑着,老辈人不满意,埋汰爸爸说不够庄重,于是阿梅同哥重新挑选,还要去照相馆冲印。
从照相馆出来,阿梅骑上了爸爸的摩托车,驶上了爸爸惯常接自己上下学会走的这条路,风太大了,于是阿梅将爸爸的遗像背在了身上,向前驶去。以前,爸爸坐在前面,阿梅坐在后面,现在,阿梅坐在前面,爸爸在后面,爸爸不再笑了,遗像代理了爸爸,从后面看过去,骑摩托车的阿梅骑得摇摇晃晃的,视线早已模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云的心里全都是雨,滴滴,全都是你,阿爸。
目送
从台北到彰化老家,五百里。
每次搭乘上离家的那一趟列车,阿梅总能看到月台上站着的阿爸,一百里又一百里,列车载着我远去,一百里又一百里,阿爸目送我远去。
现在,该是我目送你离开了,阿爸。阿梅心想。
阿义哥哥教我们说:爸,今嘛你的身躯拢总好了,无伤无痕,无病无煞,就像,年轻时欲去打拼。爸,你又要远行了。这一趟远行,比你往常的行走都要远,就好似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一样,我目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黑白照片里,无声无息的你,阿爸。
一千里,两千里,三千里……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阿爸,放心好了,我会牢牢记得你的脸的。你的身终于不可追,而我仍在不停地目送,不停地回头,而终于,我的头也不必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