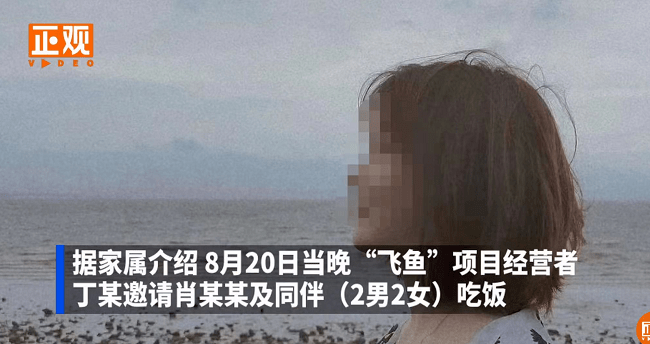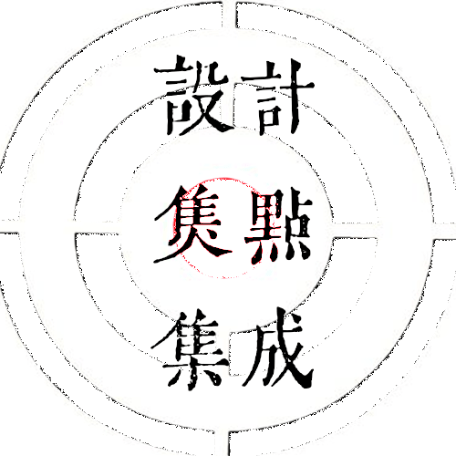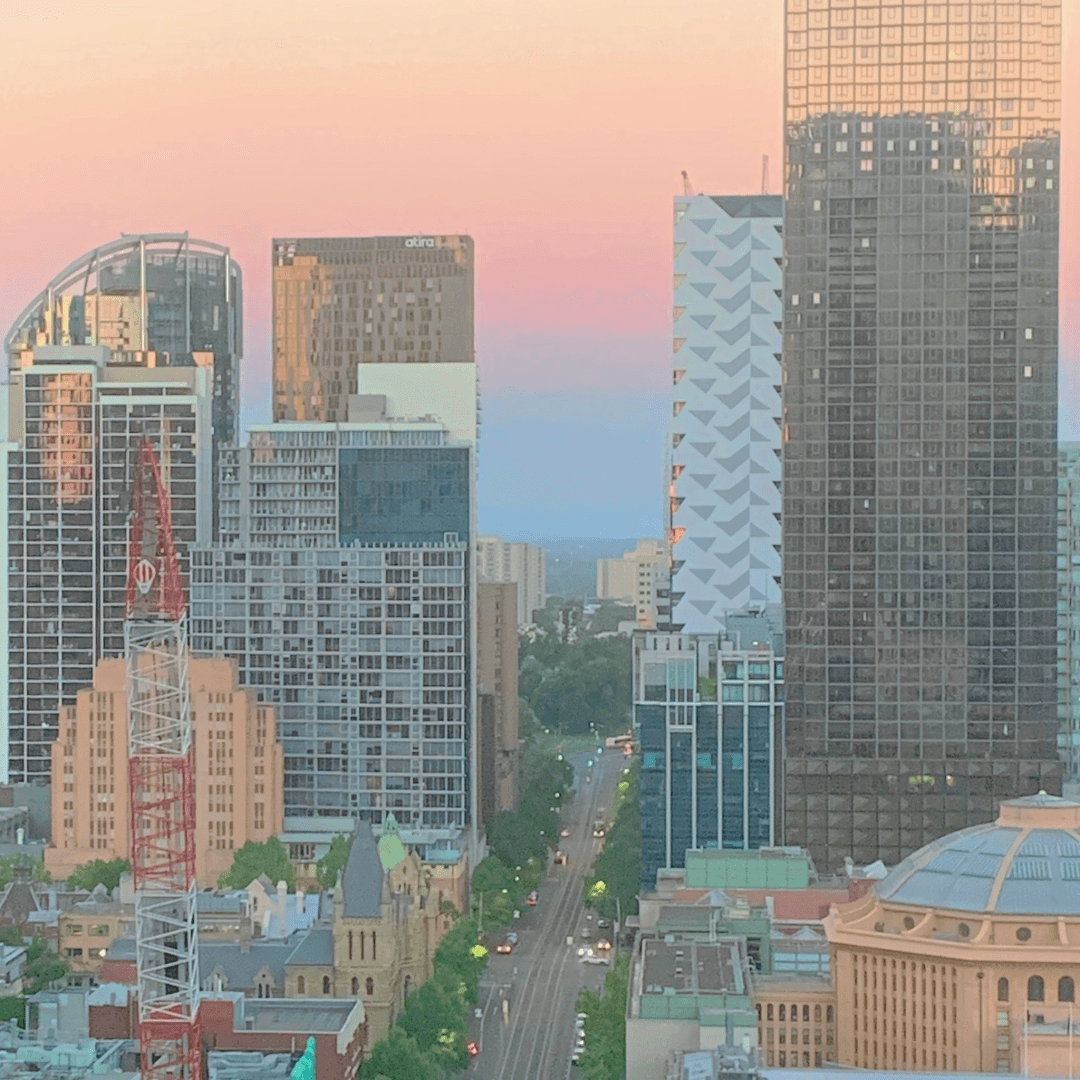在黎巴嫩首都,物质和政治空虚无处不在,而人民却设法凑合着过日子。

看哪,贝鲁特,我们的首都,也是最后一个仍在被围困的东岸城市。漫步在它的街道和广场上,我惊叹于我们空空如也的首都。在左边,我看到了两座高耸的怪物:一座教堂和一座清真寺,更多的笼子,我们把自己困在cliché里,现在只是建造或改造它们的人的陵墓。在右边,我看到一个所谓的历史街区,看起来就像一个吸毒的建筑一年级学生的流行幻想曲。转过身来,我穿过贝鲁特剩下的空荡荡的心脏:el-bourj, al-balad, centreville, Solidere, downtown——这个地方的地名揭示了我们的不和谐,这是一个团结的地方,或者至少是融合的地方。
这里的教堂里没有基督徒。在那里,清真寺里没有穆斯林。再往前走,就是一个没有犹太人的犹太教堂。到处都是没有人居住的办公室,没有商店或店主的店面,没有商人或消费者的市场。路障后面是一个没有立法者的议会。墙外是一座没有首相或大臣的宫殿——前者无疑是在飞往或离开某个地方的飞机上,后者则安坐在他们的官僚领地的其他地方。这里,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今天和以前的那些日子:烈士广场,一个公共场所和空间,没有公共话题……没有家人,没有夫妇,没有婴儿车,没有读者,没有乞丐,没有警察。
最后,我看到了一把椅子。我四处寻找它的主人或居住者。没有人声称它。没有人来认领它。我坐了下来,向后翘起,倾斜到一个舒适的位置。现在我很喜欢独处,但我自私地欣赏了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常常被宏大的计划、意外、事件和预先安排好的对我们过去的重新设计所包围。我开始做那些几十年来一直坚持要占椅子的愤世嫉俗的人很久以前就应该做的事情:思考。

2019年,黎巴嫩各地的市民走上街头和广场。他们是沮丧。他们受够了。他们生气。他们要求改变,在此过程中重新点燃彼此的希望。无论他们的籍贯、政治倾向、社会关系或社会背景如何,成千上万的人要求改变政府,或至少改变政策;领导人的改变,或者至少是行为的改变;战后体制,或者至少是体制内的政治实践;国家结构的行政、治理和司法,或者至少是那些在这些结构中生活并使其充满活力的人的表现。
在这一时刻,黎巴嫩人民拒绝了愤世嫉俗、自私自利的精英们在这个独立的新时代向他们提供的错误选择:占领还是战争、自由还是安全、正义还是和平、面包还是尊严。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走到一起,要求一些不同于他们已经被允许和允许他们自己拥有的政治的东西,甚至比这些东西还要多。
这只是一瞬间,就像之前所有的瞬间一样:神奇而短暂,部分神奇是因为它转瞬即逝。
一时不是造反,不是革命,也不是共和国。黎巴嫩人不可能,也不打算永远抗议下去。他们需要,而且需要生存。他们需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或者在这个存在的黎巴嫩生存下来——即使他们寻求改变它。他们需要养活他们的家庭,无论是他们计划抚养的孩子还是这些灾难造成的父母,即使他们寻求建立一个更多人能够养活自己的政体。他们需要弄清楚如何让自己的女儿进入学校,这些学校也可能受到各派的控制或影响,即使他们在考虑如何改善公共教育——这是我们可以在所有层面建立自由秩序和机会的真正基础——时也是如此。
现在,以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黎巴嫩人民注定要等待冷漠、傲慢和阴险的人去做一件不可能的事:结束他们自己的存在。黎巴嫩领导人不会这样做。相反,黎巴嫩领导人将一如既往地行事。他们会屈服,而不是崩溃:他们会在方便时利用自己的族群间流动性,并在必要时巩固自己的地位,从而避免全面镇压和积极变革。他们将继续试图用不属于他们的钱来争取时间,狭隘地分配利益,同时广泛地转嫁负担,在每个新的关键时刻挽救这个体系,无论有多大可能无论是一场政治叛乱还是债务违约,一场国际谈判或援助会议,还是一系列国内选举,(有些人)仍短视地将其视为变革进程的结束,而非开始。

除了失败和拒绝组建政府之外,黎巴嫩领导人也没有积极参与较小的具体问题倡议或过去时代的大对话。他们当然没有准备放弃自己的权力,改革体制,或者以其他方式改变他们的行为——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攻击他们影响力的基础。”
如果他们被迫改变某件事,他们会做得越少越好,越慢越好——甚至到那时,他们还会编造出形式和文字的胜利,而不是实质和精神的胜利。其他人可能也会这么做。例如,国家和央行并没有突然停止对公共部门的支持,通过这种支持,它们在短期内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但在长期内却失去了资源和灵活性:部分盯住汇率、官方汇率和银行汇率;基本商品和服务补贴;为食品、燃料和药品进口商提供优惠汇率的货币担保;严重的过度就业和公共管理的僵化;在每个部门都存在浪费的,实际上是犯罪的裙带资本主义安排;他们对其他政策进行了偷工减料,以在压力下保留系统的一部分。
为什么?
好吧,他们早就知道他们面临着一个有问题的选择——这个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他们的思想和政治直觉。如果国家和中央银行突然终止他们的政策,他们可能会引发他们的一位顾问所说的“一场即刻的灾难”。如果国家和央行维持他们的政策,他们可能会赢得更多的时间——虽然不需要维持秩序,也不一定需要逃避,但至少可以避免他们给人民留下的危机加剧的灾难。因此,黎巴嫩领导人继续做着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通过反应性、适得其反和扭曲的政策来关注眼前的需求,同时以黎巴嫩几代人的未来为抵押。
更糟糕的是,黎巴嫩领导人刚刚从一个厚颜无耻、令人尴尬的计划转向另一个。这里只是一个:
随着时间的推移,黎巴嫩领导人和世界银行同意两个不同的措施来帮助弱势人群和管理正在进行的大流行在黎巴嫩:2.46亿美元贷款,帮助800000名贫困黎巴嫩也援助和3400万美元的项目基金,导入和监控COVID-19疫苗在黎巴嫩的分布。在2021年1月的同一天,黎巴嫩领导人举行会议,考虑立法批准更大的贷款,同时私下利用较小的流行病计划。事实上,许多黎巴嫩领导人和他们的顾问在轮到他们之前就接种了疫苗,超过了登记接种疫苗的70万人。
他们默默帮助自己,甚至不假装这样做,作为一些运动的一部分,为公众树立榜样。在有关议会委员会、专家小组、医疗集团和国际机构的代表警告有“许多违规行为”后,议会副议长在电视上发表长篇大论,嘲笑国际机构的代表,并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全面的哗众取众。与此同时,公共卫生部长也出现在电视上,把他的投降描述为果断,把他的阿谀奉承描述为谨慎。对这些黎巴嫩领导人来说,这只是一天的工作。

在他们最初帮助创作的废墟上,黎巴嫩领导人打破了他们曾宣布要重建的共和国,现在他们花了数年时间强迫公民每天读一些反常的诗歌和黑暗的讽刺。他们让火烧灭黎巴嫩山;他们在贝鲁特镇压抗议者。他们让首都停水;他们让街道上满是垃圾。他们让走私者每个月从黎巴嫩抽走数亿美元;他们削减了基本补贴,撇开对公共政策的争论不谈,这些补贴的成本只是由于他们的低效、腐败和软弱造成的损失的一小部分。他们培养和资助一个傀儡媒体,充斥着“黄色记者”、雇佣的笔、倾斜的大嘴巴和小小册子作者;然后,他们审查、恐吓、骚扰或以其他方式攻击或未能保护大众的权利——特别是勤奋的记者和感兴趣的公民——努力维持贝鲁特作为言论自由的灯塔。他们教孩子们“监狱是给男人的”,以新法西斯主义的游行方式游行,在私人保安的陪同下在公共大厅里闲逛;然后,他们担心那些冲动的、不受控制的分子、喜欢开枪的年轻人、不知名的袭击者——所有常见的、无所不在的、不知名的嫌疑人——正在街头沸腾。他们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出入境口岸走私鸦片、合成毒品、大麻树脂等,让毒贩或他们的洗钱金融家出现在电视上,为他们的运动捐款,谋求高官;然后,他们把某位继承了半英亩大麻的农民的大麻作物夷为平地,在贝鲁特逮捕了一些基本的瘾君子,并在逮捕了一些太傲慢或太愚蠢而不愿按预期分货的骗子后四处游行。
啊,是的。他们让2750吨硝酸铵在仓库里放了7年,把自己的资本炸成碎片,让一场又一场的大火把剩下的烧成灰烬,然后分发Captagon药丸,就像给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准备糖果一样;他们装载着药品和物资,要求列出装运书籍的清单,像你的祖母一直带着喀秋茶一样检查随身行李。因此,他们扔了一个腐烂的樱桃,贝鲁特爆炸,在那层大便蛋糕上面,他们已经烤了,多年来送给每个人。
作为艺术家,诗人和歌手打造幻想黎巴嫩的“地球上的天堂,”,在黎巴嫩的总统——透视一切,除了他自己的政治选择,预示着通往地狱,黎巴嫩一直暂停了天堂人民希望和地狱之间,人们的恐惧。
黎巴嫩在过去30年一直是炼狱。它现在是,也一直是一片部分自由的土地,由既不是民主人士也不是暴君的人统治,人们生活和工作在允许和禁止之间的灰色地带。不是在和平时期,也不是在战争时期,派系——邪恶的少数群体、武装分子、其他暴徒和他们的皮条客金融家,他们努力塑造社会,而其他人则屈服、逃避、出卖或只是继续生活——世交和战斗在两者之间的空间。
黎巴嫩人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他们的行为方式却破坏了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为自己和家人而奋斗,同时把客户特权和伪社会主义特权视为权利,让领导人把基本权利视为派系特权和集体礼物;害怕他们会释放出恶魔——他们自己的,还有别人的——以至于他们向已知的已经在他们身上横行的恶魔投降了。
现在,黎巴嫩人终于落入了一个非常可怕和非常预测的地狱。想象的天堂地狱或可能是害怕他们的领导人谴责他们的经验,黎巴嫩是双重谴责委托在可预见的未来,邪恶的人了,在和失败,过去的罪行和罪恶。
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漫步时,我发现自己在想世界上还有哪些城市已经倒塌了,或者已经消失了。威尼斯、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港、阿勒颇等地的人们,在无力阻止之后,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一定感到了一种莫名的痛苦。我们认识的所有贝鲁特人一定也感到忧郁,即使是在让他们想起可能发生的事情的阳光下;孤独,甚至在其他人的陪伴下,那些人提醒他们为什么厌恶自己;生气时,即使独自一人也会因此暴露自己的失败。

我们的衰落是自己造成的,是不雅的。所以,我现在也感到一种莫名的羞愧。
但随后我开始大笑,让自己感到惊讶,因为笑声是真诚的,而不是某种应对机制或自我保护反射。毕竟,黎巴嫩仍然是荒谬可笑的。我还记得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荒谬——尽管它从未停止让每个人吃惊。
我想起了今天早些时候问我为什么走路的那个警察。走!
我想起了那些在我的车周围搭脚手架的建筑工人——为了保护它,他们体贴又巧妙地做了这件事——而不是拨打我留在仪表盘上的电话号码。当我为自己建造一个蝙蝠洞的时候,我也在想他们移动的速度有多快,我非常清楚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移动得这么快过。
我想到我是如何与这些警察,建筑工人和其他普通的混蛋发生冲突的,只是为了在人为的冲突和社会期望中建立友谊,相互保证缓和局势。我想起我们在街角互相点头致意,一起嘲笑贝鲁特将永远继承和摧毁的温顺。
我想到了一个又一个的荒谬,一直追溯到1992年,当我第一次降落在黎巴嫩。那年夏天,当我想要一台任天堂游戏机时,祖父给了我一把猎枪——他认为这个牌子类似于贝雷塔手枪。在那之后,当局没收了一块巧克力,并让我带着一把锋利的匕首(这把匕首是我从祖父的收藏中偷来的装饰性但还能用的匕首)登上了回美国的航班(经意大利)。
巧克力吗?不。刀吗?我们想知道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作为一个忘恩负义的学生,我想到了我们学校里严厉的黎巴嫩老师。我想到黎巴嫩的贵族们,他们的将军们现在称他们“残忍、可耻、无耻”;他们自己的顾问形容他们“太愚蠢而不懂,或太自私而不关心,或两者兼而有之”;他们自己的情报人员认为他们是只会解放黎巴嫩的骗子,即使那样,也不一定是在他们死后。
我想到了我们的总统:米歇尔·奥恩(Michel Aoun),这位年过八九十的前将军、自封的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他真的是个偏执狂,忙着争当总统,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一旦当上总统会做些什么(2016年,经过几十年的追求,他确实做到了)。
我想到了我们的总理,他们是数学原理的活生生的例子:整数乘以0等于0。我们的临时政府总理哈桑·迪亚布(Hassan Diab)是另一个可能会在résumé的文章中宣称自己出生的人:“开创了环境间的快速转变,包括但不限于从胎盘到地球大气层。适应大气和环境,更普遍。表现出快速的进步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至少有一位高级主管认为这是一种自然和本能的自我保护天赋。”我们的候任总理——曾经和未来的总理萨阿德·哈里里——是如此的早熟,以至于他在第二代的时候就做到了伊本·赫勒敦自己认为需要三代才能做到的事:挥霍家族遗产。(哈里里后来辞职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被任命为某种形式的总理。)

我想到了我们的议会议长:Nabih Berri,一个为了给伊甸园开绿灯而从上帝身上砍了3%的人他的帮派暴徒仍然到处骚扰私人企业主,制造问题让其他暴徒来解决,并自豪地威胁要“操人们的姐妹”,因为她们和平抗议的正是使我们如此多的人处于依赖地位的条件。
我想起了我们的前外交部长:格布兰•巴希尔,他是贝里的基督教模仿者——缺乏魅力、影响力和暗示,而他用令人毛骨悚然的自以为是、不断的介入和笨拙的姿态来过度弥补。“可怜这个国家,”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黎巴嫩人说,“这个国家的Gebran曾经是哈利勒,现在是巴希尔。”
我想到哈桑·纳斯鲁拉。然后我马上道歉!后来我意识到,我应该向下一个内阁要两个投资组合,把我的谄媚和懦弱当作审慎和务实来卖掉。
我想到银行家、法官、律师、承包商和其他人,他们吃下了有毒的水果,却事后警告世界,他们已经对其他人做了些卑鄙的事。
我想到的是公务员,他们歪曲了自己的工作描述,以牺牲公众为代价为自己服务。
我认为人们应该感觉如果共和国的更体面的将军,警察、法官、活动人士和其他人一起很难抓住它,眼泪在他们的眼睛,脸上的担忧——说话人在他们上面的人shit-taking的层次结构。
我想到了凶残的普通人,野蛮的自然状态,以及我们,甚至在现在,如何把正派的人描绘成哑巴,礼貌的人描绘成软弱,恭敬的人描绘成优柔寡断,执着的人描绘成误入歧途。
我想到体面、礼貌、恭敬、敬业的人们默默无闻地辛勤工作,而那些拥有更多财富的人却做得更少,他们追求的是永远也挣不到的胜利之花。
当我们如此急切地用这些谚语来评论别人时,我想到了我们的谚语以及这些谚语所揭示的我们自己。当我思考某些黎巴嫩领导人和太多想要取代他们的人的行为时,我立刻想到一个问题:他们“不操,不被操,也不让开让别人操。”
我想到,我们最伟大的诗人,一个用骨子里感受到了别人几十年来声称观察这个地方所没有学到的东西的人,是如何对他所有的老师忘恩负义的。我记得他和我们一样,在黎巴嫩受过教育。
安东尼·埃尔戈赛因,是中东研究所的律师、作家和非常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