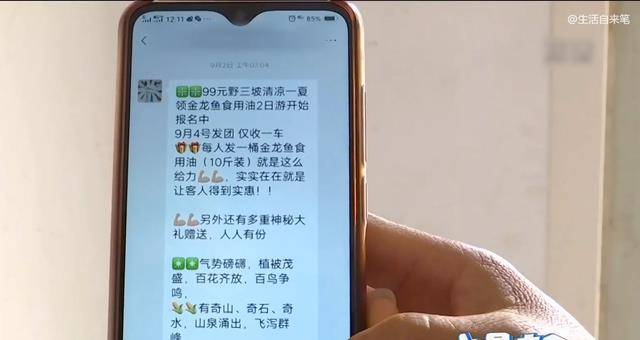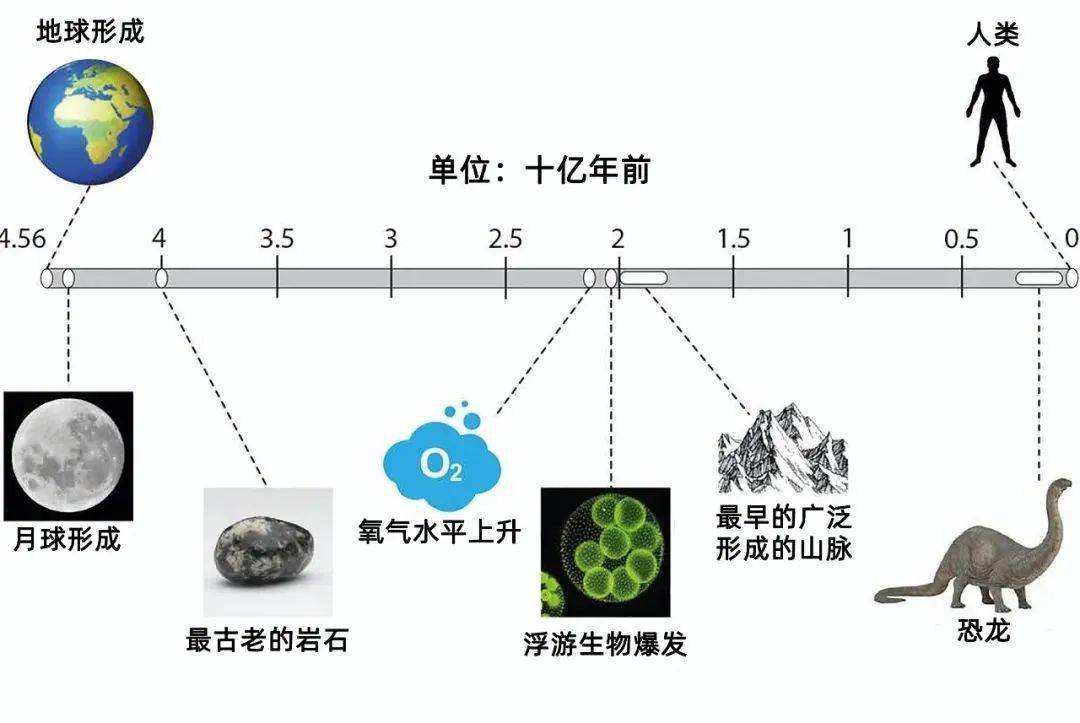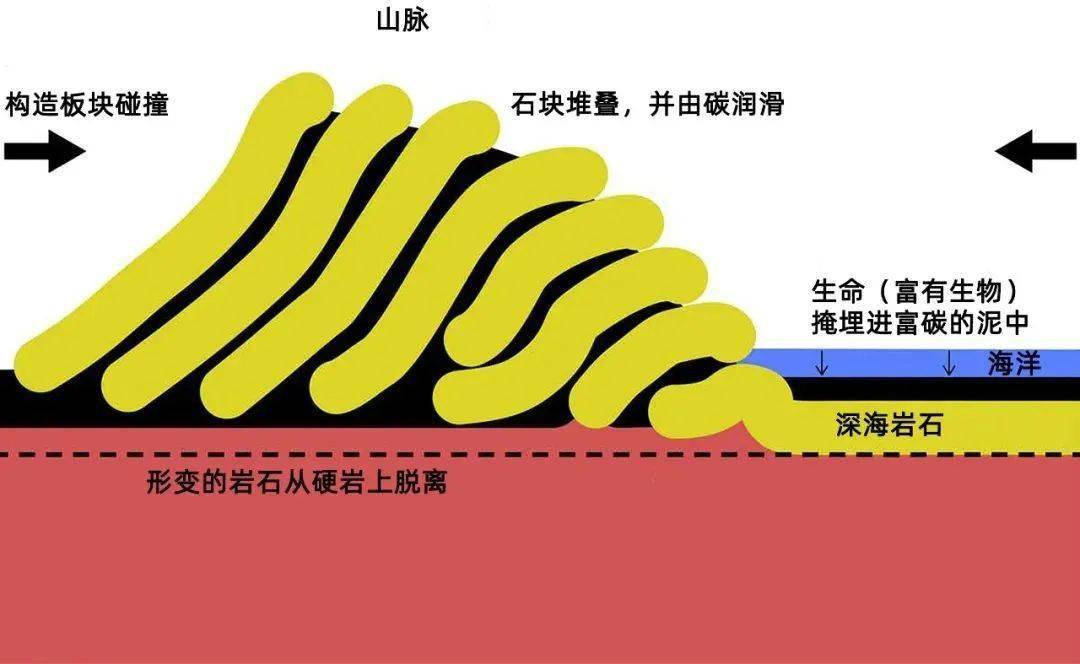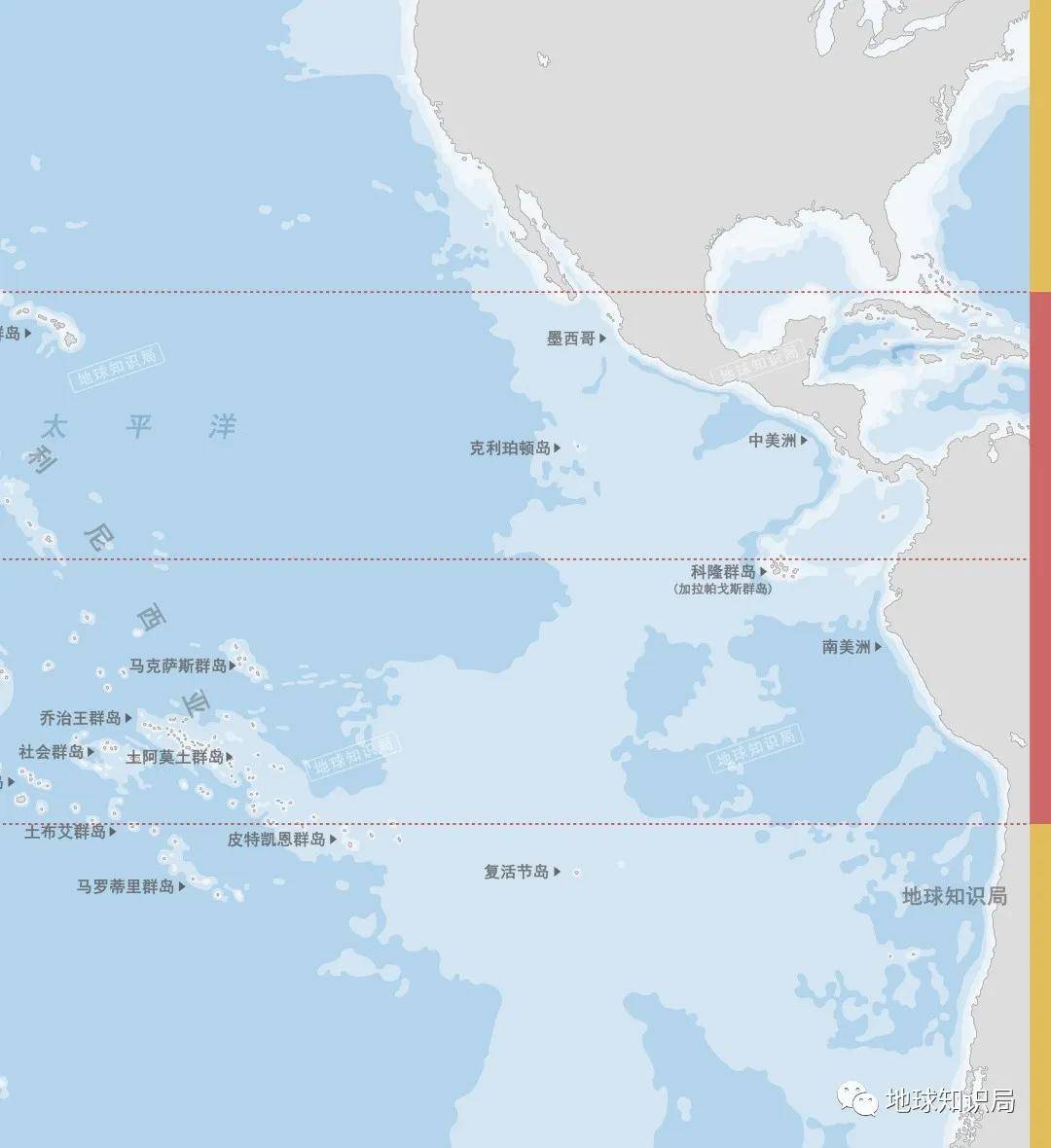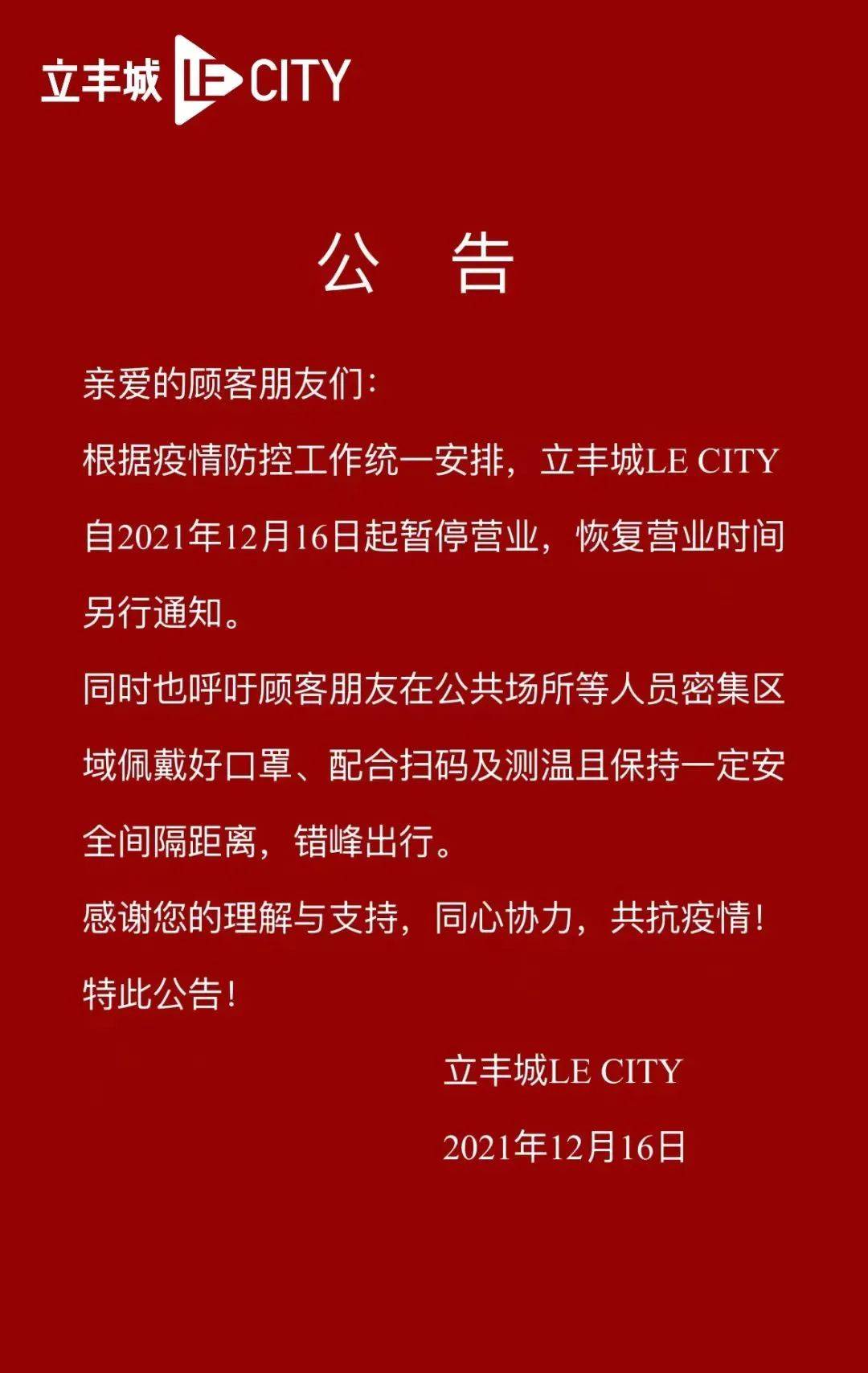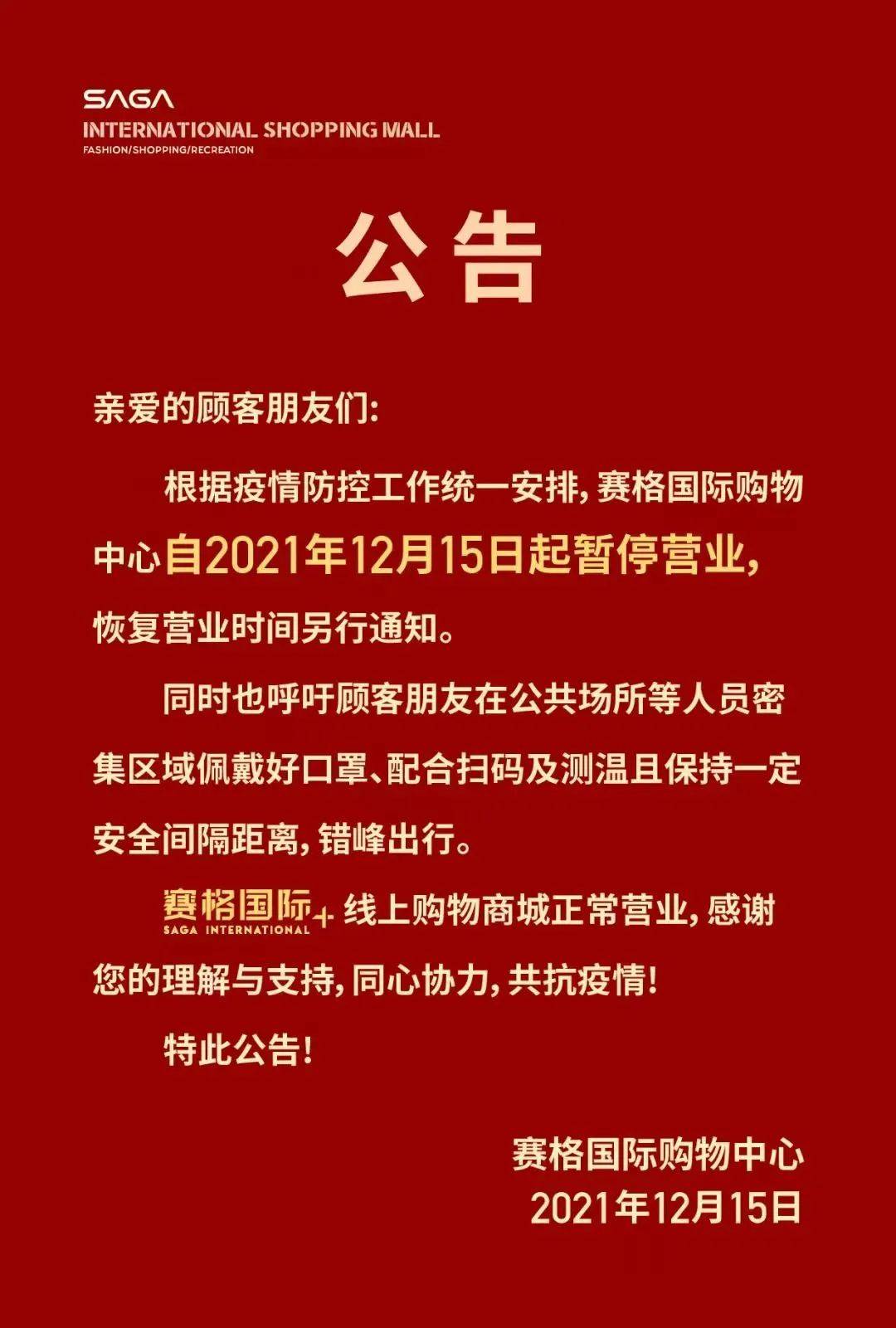红山泓 红山魂
□毛显荣
某个晴朗的早晨,邀约上两个好友,直奔红山窑而去。
红山窑,地方不大,名气不小。因红山窑镇政府门前红山广场的背面红山上有曾经烧制黑釉粗陶的窑炉而得名。那时,腌菜缸、水缸、面盆、油盐罐、酱、醋、茶的容器一应俱全。甚至有钱人家把大小不同的缸摆在库房盛放粮食,并按装粮食的多少分为一斗缸、两斗缸、三斗缸、四斗缸、五斗缸。现在到红山窑镇转一圈,还有好多人家的猪圈、厕所都是用缸垒起来的。“红山窑地方小,三座铺子五座窑”的景致早已不见,但关于红山窑的盛景与人文历史,历代文人雅士早已用心镌刻在了石碑或跃染纸上成了永久的诗和远方。
而我只能说说段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永昌流传着一个家喻户晓的笑话:曾经有武威的姑娘相中了红山窑的后生,双方举行完订婚仪式择日完婚时,按照当地习俗,男方家要给即将过门的新媳妇准备好春夏秋冬四套衣服。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化纤面料少之又少,大多数都是走后门或凭票供应的。当时武威人把这些高级面料叫“一抖干”,意思是洗完后一抖就干了。武威方言里“干”的发音是“缸”。姑娘的家人要求小伙在结婚时必须要有一套“一抖干”。小伙和媒人一听要“一斗缸”,两人窃喜,回家后小伙把女方家的要求陈述给父母,父亲拍着大腿站起来起说:别说一斗缸,五斗缸我们都有的是,我们的猪圈都是用缸砌起来的。第二天小伙的父亲便用驴车当载体,大缸套小缸,小缸套盆子,行走七八天把一车缸送到了亲家门上。
段子仅仅是个笑话,从这个段子里就能看出红山窑制陶的发达与繁荣。从第一个炉开窑到现在,红山窑究竟生产过多少陶器,有统计吗?繁盛时期,这里的陶器最远卖到了哪里,有记载否?这些都不是我们探讨的问题。任何形式的黑釉陶器,到了永昌人家里,就充当了所有能装的下物件的容器。河西走廊谁家门口、屋檐下、灶火旁没有几口不同年代从红山窑卖缸人的驴车上搬下来的菜缸、水缸、浆水缸、面盆、药罐子呢。兄弟们分家时,每个儿子两口缸是父亲准备给儿子们的生活必需品之一。
走在封门多年的王家窑前,恰遇干活回来的王家窑最后一个制陶烧窑人,六十多岁的王永礼老汉。在攀谈与聊天中老汉长吁道:随着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轻巧便捷的塑料制品彻底替代了笨重的陶制品。失去了市场又没有了马营沟煤矿2000℃热卡的烟煤,用啥烧,烧出来卖给谁?我问老汉:马营沟煤矿也封窑了?老汉答:为了保护祁连山,马营沟煤矿按照国家的要求早就封了。
告别烧窑人,从老汉的感慨中沿着一条还没完工的水泥路到红山头上的孔庙里面对孔子塑像静默肃立。读完侧墙上的《论语》选段,出门站在圣人脚下放眼现代气息浓郁的红山广场,几座摇摇欲坠的旧窑炉像一幅幅陈旧的写意画,三三两两镶嵌在崭新画面的最靓丽处随风飘荡。看着曾经辉煌的几座炉窑令人沉思也让人黯然。在岁月的剥蚀和人口的流失中这些文物级的炉窑还能挺立多久?
走下山坡,在红山文化广场新建的制陶车间,最里面支起一个电炉,四周散落着细泥和釉料,门口的模具旁,一身泥巴的李海生正在制胚。五十多岁的李海生是红山窑制陶“非遗”的最后一个传承人。他说,为了不让这门古老的手艺失传,红山窑镇政府做了大量抢救性保护工作,把烧窑工艺列入公共文化体系。出资盖起了300多平方米的厂房,布置了一个展览厅,展示原汁原味的陶制品。组织窑工,带上陶土去景德镇“取经”,让红山窑的土也要做出精细的陶器。遗憾的是,经鉴定,这里的土质量不高,只能做些粗陶。李海生感慨道:要是能做细陶,几百年前先人们早做了,还能留到现在。如今的我也只能用电炉做一些花盆来维护这门手艺了。
出了制陶车间,前走几步就是红山文化重中之重的红山泓酒厂了。此时,碰巧遇上了酒厂的张经理。因为早几年打过交道,寒暄几句后。张经理带我们参观了翻曲、淋酒的全过程,品尝了从大缸里舀出来的不同度数的红山泓,在微熏中站在广场功德墙上“毛忠”两个字旁矗立静思。回顾和瞻仰了毛氏祖先的传奇故事和丰功伟绩后,转身再看看红山广场,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下午回来的路上,歌曲伴着酒香在车里萦绕,思绪依旧停留在那几座窑口。说实话要不是有一口红山泓的醇香在舌尖上缭绕与诱惑,往后的日子,在记忆深处还能搜寻出红山窑的影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