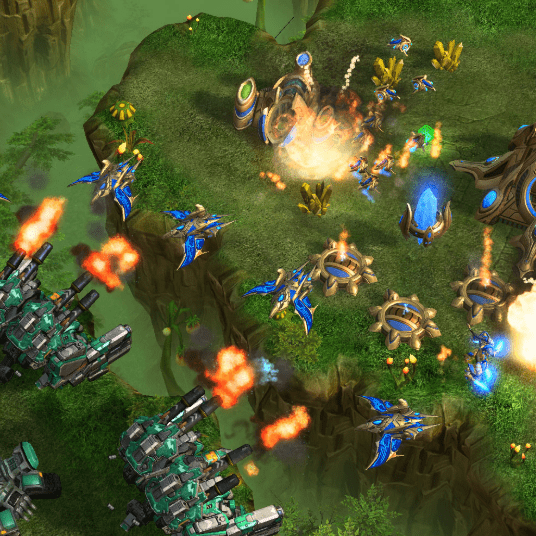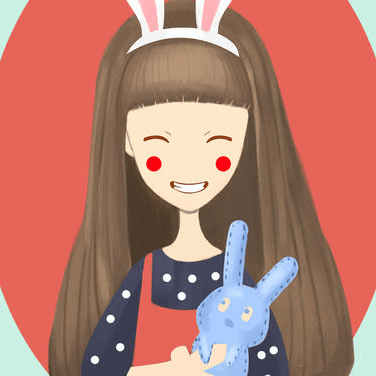旧日太平湖畔,“青睐”寻访团与嘉宾傅光明合影 50年代,老舍在自家的鱼缸旁 胡同里的孩子也来听讲 傅光明给“青睐”会员讲解
众所周知,北京城留存有数不胜数、积淀悠远的文化遗迹。为帮助居京或来京的朋友更切实、更深入、更系统地了解这座“文化中心”的深厚内涵,本报推出“北青版”京城文化路线。我们将以实地寻访的方式,带领读者用脚步丈量这座古老又崭新的城市,去阅读、品味、感受并触摸它的肌理。我们期待,这样一条线一条线地交织起来,将呈现出一幅既有温度又有时代感的京城文化地图。
一个作家的诞生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老舍先生自然也是如此。今年是老舍去世55周年,8月10日,我们邀请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傅光明教授,和“青睐”会员一起,在京城中寻踪老舍旧迹,以此纪念、缅怀这位以“文牛”和“写家”自喻的“人民艺术家”。
丰富胡同19号
老舍纪念馆,老舍迷熟悉的“丹柿小院”
老舍故居在疫情期间限流,参观需要预约。院内人少,两棵柿树静静伫立,安静的氛围使大家说话的声音都为之减低。
柿树下的说明牌介绍详细:1953年春天,老舍夫妇亲自种下两棵柿树。每逢深秋时节,柿树金红,别有一番画意。为此,胡絜青将小院定名为“丹柿小院”。这是老舍迷们喜爱和熟悉的小院。
老舍在此住了16年,很多人都知道他喜欢在院子里种花种草种树。他最喜欢菊花,住在这儿的时候,每年秋天都要搞菊展,把自己养的菊花摆在院子里,请朋友来欣赏。这或许与他的母亲关系密切。他的母亲也是个热爱生活、喜爱花草的人,老舍曾说:“将来我有了自己的小院子,我会在小院里种满花草树。”所以,当老舍在北京拥有这样一个家的时候,他实现了这个愿望。
在傅光明的理解中,老舍的性格柔中带刚,表面幽默,易于交友,实则内在有一条坚强硬实的底线。“他最后在那样一种情况下选择投湖自尽,与他外圆内方、刚硬坚毅的性格底线密切相关。”
老舍在《我的母亲》中,曾写下饱含至情、催人泪下的文字:“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我的。”
昔日居室改装的展厅中,老舍先生的生平记述得清晰有序。“青睐”会员松散地围绕在傅光明周围,聆听这位老舍研究者的讲述。
老舍之有一番成就有其幸运之处。虽然他出身平民家庭,社会层次不高,也没有高学历,但他在1924年得到教会推荐远赴英国伦敦,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讲师。他作为小说家的生涯,即从伦敦开始,伦敦催生出中国现代一位大作家。
老舍在伦敦的住处,2017年傅光明专门去拜谒过。房子的外墙上挂着“英国遗产文化委员会”专门授予的蓝牌子,那是曾在英国居住过,在艺术、文化、历史、科学等领域有过杰出贡献的英国人或外国人所能获得的极高荣誉。傅光明解说:“老舍是第一个挂上蓝牌子的中国作家,是第二个中国人。第一位是孙中山。老舍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就诞生在这间房子里。”
一大面展板专门介绍抗战时期的老舍。抗战中老舍抛下小家,“妻子儿女全不顾,赴汤蹈火为抗战”,在大后方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击协会”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付出巨大,其中不乏人们所无法理解的艰辛和酸苦。为宣传抗战,他在这段时间写过不少话剧,但并不擅长,他的本领仍在说故事。抗战结束后,他和另一位文坛骄子曹禺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应邀访美,访期一年。
一年期满曹禺回国,老舍留在美国。这段时间他和美国朋友合作,将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同时开始写作《四世同堂》第三部。三年半后,新中国成立,应周总理邀请,那年12月9日,老舍从香港坐船在天津码头上岸,回到祖国。回国后老舍暂住北京饭店,家人还都在重庆北碚。1950年初,他买下丰富胡同的这个小院。
在丹柿小院,老舍的勤苦有目共睹,他写下大量讴歌新中国、赞美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题材异常广泛,最著名的莫过于《龙须沟》和《茶馆》。傅光明感叹:“《龙须沟》初稿老舍只花了大半天实地采访便写了出来,而且写得非常快,由此可见他当时的政治热情之高。”经典话剧《茶馆》也诞生在这里,这部戏北京人大都耳熟能详,很多老舍迷甚至能大段背出其中京味儿十足的对白。
老舍这位“京味儿”作家,笔下流出过多少北京的风物和人情。其实“京味”两个字远不足以涵盖老舍。但有一个地方很有意思,傅光明认为非常值得研究:“老舍的小说发生地几乎都在北平,但写作地都在北平之外,伦敦、济南、青岛、重庆北碚,主要在这四个地方。可见,老舍虽然身不在北平,但北平始终在他心底。他在散文名篇《想北平》里说:‘我的血液是和北平黏合在一起的。’所以,从老舍的创作轨迹可以看出,故乡始终存于他的灵魂、他的心血,同时也成为他灵魂和生命的一部分。”
傅光明还告诉大家,学术界对老舍有一种共识的评价,即老舍的创作可以1949年为分界线,简单分作前期和后期。有一种观点认为,老舍后期创作也有一个高峰,这是老舍非常幸运、并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很多大作家,在后期基本上没有与其前期艺术水准相匹配的作品,老舍似乎是个例外,当然,这主要体现在《茶馆》上。”
丹柿小院每到金秋时节,有红色的大枣和金色的柿子,果实饱满丰硕,这仿佛和老舍的创作息息相关。傅光明觉得,自己研究老舍许多年,作为一个北京人,某种时候竟常有一种失语的感觉。“可能因为太爱老舍了,或者是对他比较熟悉,有时反而突然间觉得,似乎并不太能走近他,不太能了解他。我想这也说明了一个作家的丰富性。老舍的丰富有很多层面,并非轻易能解透。”
“老舍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难得的艺术天才,他是一个多面手,现代作家中似乎少有能与之比肩者。他几乎尝试了所有的文学体裁,但他却以‘文牛’和‘写家’自喻,他不说自己是作家,而是在文学土壤上勤苦耕作的牛。”这也正是为什么阅读老舍,不仅是现在进行时,对他的理解和研究更是将来时的重要原因。
老舍能给人一种励志感。他特别喜欢“勤苦”这两个字。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6年时间里,他作品丰厚,为了配合宣传,有些作品一改再改,全是手写。从这点上来说,老舍在丹柿小院的那间小屋里,真的是一名异常勤苦的园丁。
护国寺小杨家胡同8号
老舍先生名篇《四世同堂》的故事发生地
第二个打卡地,我们来到小杨家胡同8号,即小羊圈胡同5号。这里是老舍先生的出生地,同时也是老舍最著名、篇幅最长、有抗战文学扛鼎之作称谓的小说《四世同堂》的故事发生地。
让我们回忆一下,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对此地的描述:“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略微有一两个弯,而且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葫芦的嘴儿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进了葫芦脖子,看见了墙根堆着的垃圾,你才敢放胆往里面走。”
现如今的小杨家胡同仍葆有着细而窄的葫芦嘴,祁老太爷口中阔大且长有一棵大槐树的葫芦肚上,加盖了一座二层小楼。胡同改造后,这里变化不小,傅光明第一次到这里寻访是在1993年,记忆中的破旧建筑中还留存着老北京胡同的感觉。
老舍1936年在济南写下散文名篇《想北平》。他想念北平的点点滴滴:“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每一个城楼,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况且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在小羊圈的葫芦肚儿,“青睐”团员们突然发现,阅读老舍原来还可以怀念想念中的老北京啊!
这时,跑来两个近旁院落的孩子,七八岁的阳光模样。他们刚刚在开心地打着羽毛球,现在一头一脸的汗。见我们一队人马出现在自己的领地,好奇地凑过来听讲。傅光明又读起老舍的《我的母亲》,让大家感受大作家文句的简短和有力,老舍文字的感人处每每在诵读中更能够体现出来。傅光明说自己特别爱读老舍,很大原因在于其文字的内在张力。
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第一章,开篇第一句:“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傅光明请大家体会大作家的起笔:“我们常常说万事开头难,长篇小说也一样。《四世同堂》是一部鸿篇巨制,100万字,头开得如此随意,老舍当初是怎么构思的?”
大家议论纷纷之时,傅光明接着说:“实际上,老舍对于小说的整体布局,起笔时应已有了比较成熟的酝酿。要把祁老太爷写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把祁家写成一个什么样的家族?我们国民的性格有多少层面附着在祁老太爷这样的中国人身上?他都有了打算。老舍的深刻在于,他从来不做明面上的批判,而是在看似日常琐碎、简单随意的描写中,自然而然形成一种犀利的剖析和批判。”
看过《四世同堂》85版电视剧的朋友可能还记得,邵华扮演的祁老太爷在胡同里葫芦肚子处说的那番话:“不碍事,咱们小羊圈有一个葫芦嘴,严实。”他平生的经验告诉他,不出三个月,乱子就会过去。他嘱咐家人囤足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自家小院门关起,大缸顶住,就“不碍事”。单这一段,傅光明做起了人物分析:“祁老太爷觉得国跟我没有关系,抗战跟我也没有关系,我只要关起门来过自家的小日子。在这样的描写中,那种深入骨髓的国民性批判,是不是自然呈现了出来?”当然,他强调说,文学中这样的描述、批判常需要我们去领会。
老舍的《四世同堂》故事精彩深刻,而实际上,他所写的事并非亲历,而是来自夫人胡絜青的讲述。那时老舍在重庆北碚,胡絜青带着孩子千里迢迢从北平赶来。家人团聚后,胡絜青经常跟他讲起日治下的北平。这些讲述无疑调动起老舍的创作热情,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
傅光明说:“这里我们不妨替老舍设想一下,他构思这样一部长篇小说,首先会想让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他最熟悉的地方是不是最合常情?我们知道,北京城西北角这一块儿,就是这里及附近一片区域,正是老舍青少年时期成长的地方,是他父亲和母亲的旗籍属地。他的父母是满洲正红、正黄旗人。这是他最熟悉的地方,让故事发生在了这里,再自然不过。”
《四世同堂》是一部篇幅浩大的小说,在鲜明的抗战主题之下,描写了方方面面的人物、人情、人性,从很多描写的人物身上都能体会到老舍文学和艺术的深度及广度,尽管有些人物出场次数很少。“老舍是一位幽默作家,我们常常将他定义为语言大师、幽默大师,但对于他怎样把自己深刻的批判融在作品里,很多读者体会得不深,所以今天这样一个老舍之旅,可以说也是一种有意的引领,因为这种批判对于今天的我们,并没过时。”傅光明道出这一次寻访的深意。
傅光明建议:
“成立一个老舍读书会吧”
老舍确实是幽默的,他的幽默体现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中,也体现在他的作品里。在《我的理想家庭》那篇散文中,他曾自我调侃说:“我刚想出一个像样的句子来,小济就来捣乱,耽误了我的构思和写作,所以我到现在也没有成为莎士比亚。”傅光明也是一位莎士比亚译者,对于老舍谈莎翁,他也有发言权:“老舍没写过像样的文章谈莎士比亚,但他谈过莎士比亚写了很多戏,只是写得太快,原本他可以写得更好。”我想,老舍对莎士比亚的这一评价也反映着他自己的创作观吧。
前往下一处打卡地的路途上,傅光明讲起老舍轶事。谈到老舍曾经很得意地说过,他的《骆驼祥子》是可以朗诵的。语言常常跟着声音走,在阅读中能够得到不一样的体会。对此,傅光明深以为然,他说:“阅读老舍不需要很高的学历,他的文字非常口语化,顶顶俗白。单纯从阅读作品来说,读鲁迅,中学水准大概读不太懂,说不准还会逆反,跟鲁迅产生距离。但老舍不会,老舍那些最好的作品,随时随地抽出一章,随手就可以读,对于语境的前后关联不用太过考虑。”傅光明自己爱读老舍,那是他的一个享受。
接着,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日本有个老舍读书会,成立于1955年。读书会每周日上午活动,内容就是读老舍作品。傅光明与读书会的创始者们大都是忘年交。2004年,他应日本老舍读书会邀请,专门去讲老舍。读书会邀请嘉宾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主讲人不会说日语,以保证随时随地用中国话与会员们交流。说什么样的中国话?那就是第二个条件,必须是北京人!说北京话!傅光明能从读书会成员那里感受到,他们特别享受这样一种倾听。
“由此我想,‘青睐’也可以成立一个老舍读书会。我们来读老舍,甚至可以表演,比如《茶馆》;还可以做老舍文学寻踪,我们都是北京人嘛!《骆驼祥子》里写的很多地名都是真实的,并非文学想象,我们大可拿着一本《骆驼祥子》,去寻觅祥子在北京的行踪。”这是不是一个诱人的提议?反正在场的“青睐”会员们都跃跃欲试了。
有网友借机提问:如何提高孩子的写作水平?
这方面傅光明可谓经验丰富,妻子和他的“引诱”式阅读,使他们的女儿早早深谙文学之道。而他也记得老舍先生曾经反复讲到:文学写作要遵循文学内在的规律。
这个规律是什么?说起来有点玄奥,但有过创作体验的人都懂得,规律不是简单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写作之路异常艰辛,它需要勤奋,需要广泛阅读,也需要一定的才华。傅光明感慨:“我们总说老舍是一位天才作家,但他也不是坐在那儿就文思泉涌,他的每部作品都有构思的艰难。我们有没有想过,老舍以如此的天才,竟付出如此的勤苦,这才是他的成功之法?”
新街口豁口太平湖
老舍的生命在这儿画上句点,走向永生
小杨家胡同距离老舍生命结束的地方——太平湖,只有大约两站路。“太平湖”,紧挨着新街口外大街西侧的护城河。这是我们的第三处打卡地。
说是太平湖,湖其实早已不存在。大概在上世纪70年代修建地铁时,这个不大的湖被填平,上面修建起厂房,如今成了积水潭地铁车辆修理厂。
老舍投湖的地点在西边的后湖,疫情期间,进入要扫码测温。傅光明没有带我们深入去找寻旧地,据说那里曾经立有一个说明牌子,大家倒也不甚关心,只专心地听着傅教授分析,老舍为什么选择此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实际上,这个题目老舍之子舒乙先生曾做过研究,他曾经写过:“太平湖悲剧发生十二年后,有一次,我偶然打开一张解放前的北京老地图,竟一下子找到了父亲去太平湖的答案。太平湖正好位于北京旧城墙的西北角,和城内的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很近很近,两者几乎是隔着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而遥遥相对。从地图上看,两者简直就是近在咫尺。观音庵是我祖母晚年的住地,她在这里住了近十年,房子是父亲为她买的,共有十间大北房。她老人家是1942年夏天在这里去世的。我恍然大悟:父亲去找自己可爱的老母了。”
傅光明的分析中,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很重要的一点,这里是老舍作品中很多人物故事悲欢离合的发生地。
从老舍故居走到太平湖,距离不近,而他当时已经是67岁的老人。他家附近也有水,什刹海、后海、积水潭,都比太平湖距离要近。那一天,这位67岁的老人在湖边坐了多久,没有人知晓。而傅光明肯定,他一定坐了很久,想了很多,想来想去,最终没给自己找到一个眷恋生命的理由。
在了解了老舍这番经历之后,傅光明特别提议大家再来领会一下《茶馆》结尾王掌柜的自杀,是否能跟老舍最后的自尽形成艺术与真实的对应和吻合?都是那么的悲、惨、痛!傅光明说:“或许老舍先生坐在这儿,脑海中有了一个艺术时空,扔着想象的纸钱,凭吊着自己的生命。”
同行的“青睐”会员们静静地听着,仿佛跟随着傅教授的思路,更多更深地理解了老舍,走近了老舍。傅光明说:“从地理空间上来说,老舍的生命终点距离起点很近,但他生命和艺术的丰富性远远超出。老舍自身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时空,是一个博大的艺术世界。对于老舍,到今天,还是读不完的,尤其作为北京人,我觉得,我们要无限地深爱老舍,爱他写过的北京。”文/本报记者 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