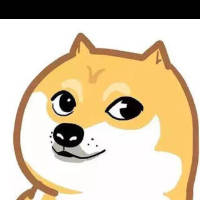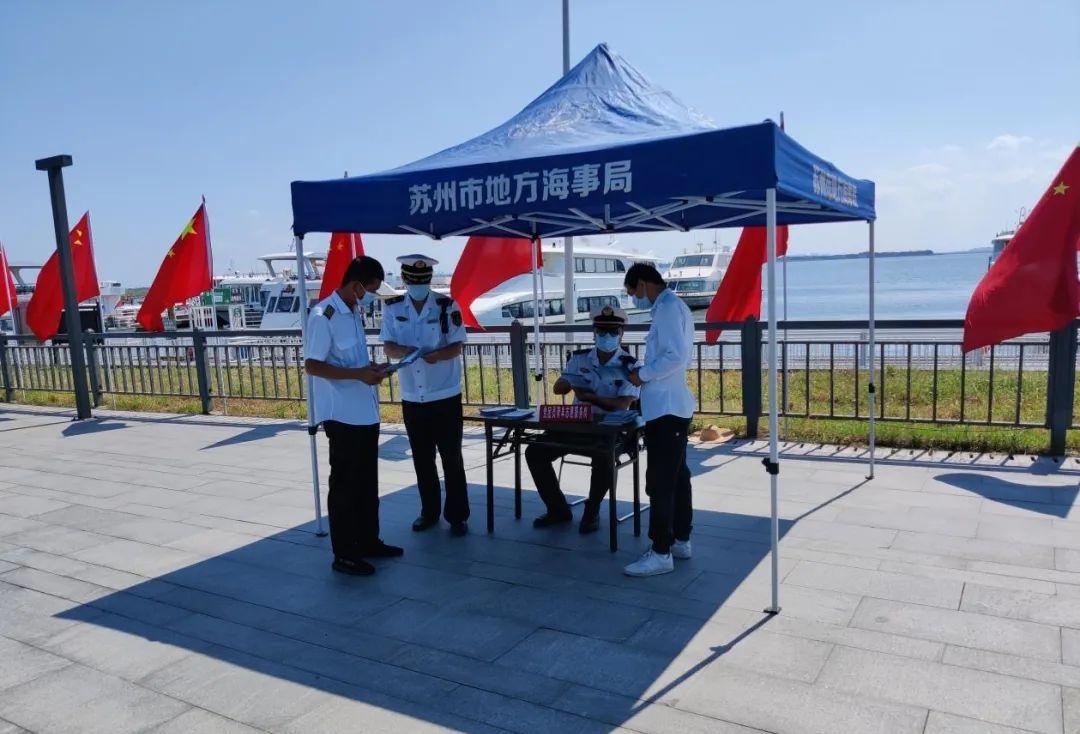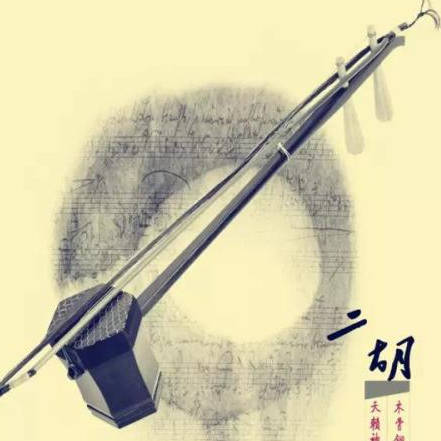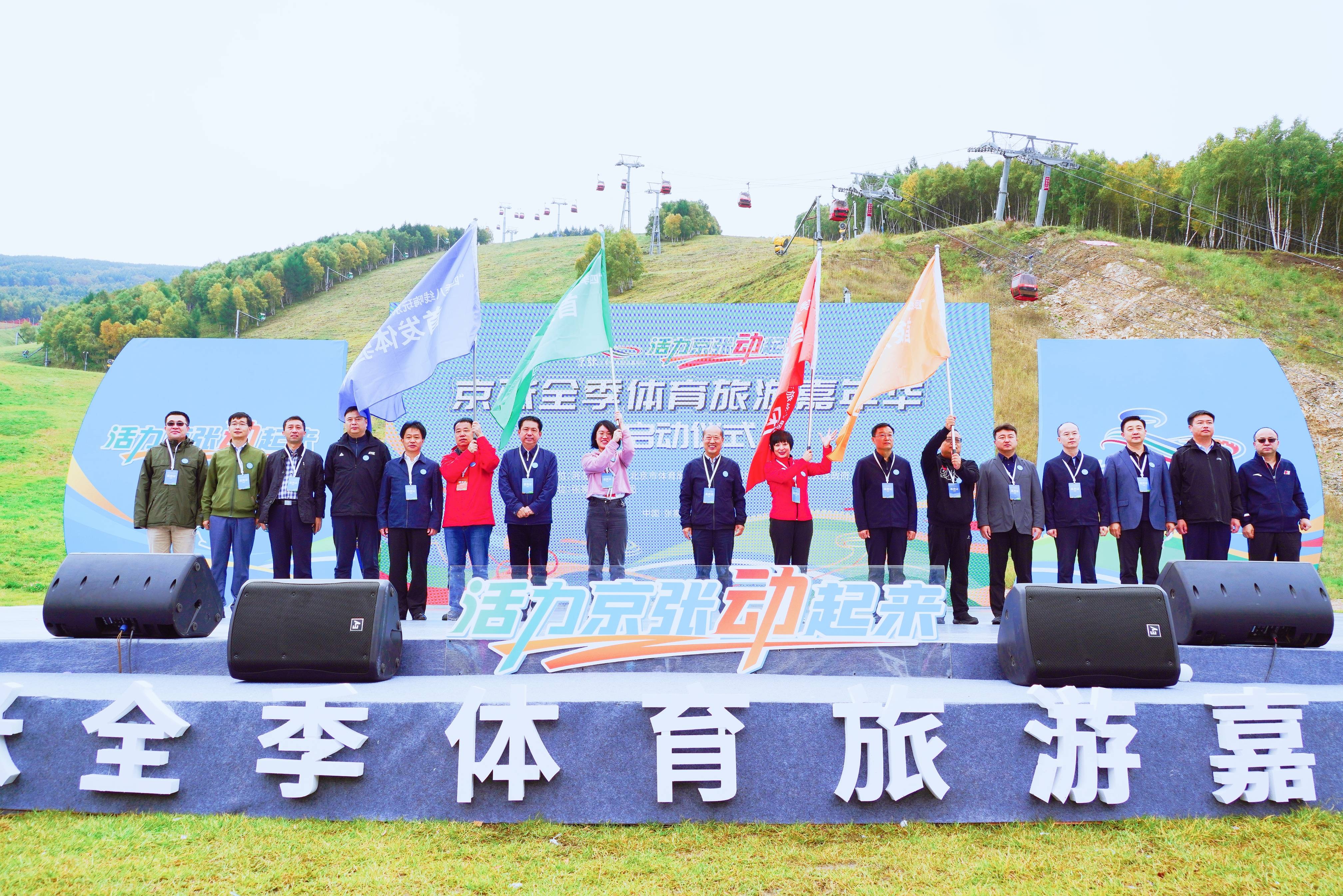(马尔克斯故居餐厅 作者/摄)
【行走南美】
杜欣欣/文
一
卡塔赫纳,清晨的气温已经相当高了。我们在阴凉下用餐,旁边是一对儿巴黎人。聊起旅行计划,那男人说:“你们还不知道啊?泰罗那(Tayrona)国家公园因原住民节日关闭一个月!”“啊?!我去圣玛尔塔(Santa Marta)就是为了泰罗那。”他说:“谁又不是呢?”旅行中总有不确定的因素,但已定的行程却不能随之而变。
卡特赫纳与圣玛尔塔之间没有航班,车程近四小时。虽然两城之间有公车,票价仅8美元,但语言不通,天又极热。权衡之下,我们宁愿付20美元搭乘中巴。同车的人都是游客,来自法国、英国或德国。出发前,检票员将一对母女送上车。她们穿着正式,小姑娘很好奇,时不时会从椅缝里偷偷瞧我。
车子沿着加勒比海滨向东北而行,地广人稀。大概1小时后,车停路边。这一带相当荒凉,那对母女下了车,沿着土路向坡上的村庄走去。看起来是乡下人到大城市谋生,搭车回乡。那对母女下车后,不久又停在加油站。一个人上车点数乘客,似乎在查验司机是否私自载客。高速公路直而平,隔离带很宽,车辆掉头就在隔离带上。公路修得好,收费也不少,沿途共收费六次,不知跑在高速公路上的马车是否也要缴费?
车过巴兰基亚(Barranquilla),该市的规模在加勒比地区仅次于卡塔赫那。此时正值嘉年华会前夕,城里城外车水马龙。嘉年华会起源于威尼斯,然后传到巴西的里约,美国的新奥尔良和哥伦比亚的巴兰基亚。目前世界上共有4处举行嘉年华会,一般于复活节前40天开始,持续4天4夜,据称此地嘉年华会的规模仅次于里约。
马尔克斯与卡塔赫那、巴兰基亚和圣玛尔塔都有不解之缘,作家的母亲在圣玛尔塔念书,马尔克斯不仅少年时曾多次来往于巴兰基亚和圣玛尔塔,后来还为巴兰基亚的报纸撰写专栏。那时作家还未满23岁,笔耕所得仅聊胜于无。他回忆说:“已过服兵役的年龄,却是两次淋病的老将。每天抽16只烟……”
马尔克斯的文学生涯多以与水有关。他以海滨城市卡塔赫纳为背景,创作了《霍乱时期的爱情》。他在马达莱纳河上航行过11次,自称熟悉河上的每个村庄和树林,而巴兰基亚位于马格达莱纳河口。他的《迷宫中的将军》又是以古朴迷人的马达莱纳河上之城蒙帕克斯(Mompox)为背景,不朽之作《百年孤独》的故事则发生在阿拉卡塔卡河畔。
驶过巴兰基亚之后不久,湿地、泻湖和大海交替在车窗旁闪过。90号公路变得极窄,车的左边几乎是贴着加勒比海行驶,而右边就是圣玛尔塔大沼泽湖。这片沼泽位于马格达莱纳河与内华达山脉圣玛尔塔之间,面积近5000平方公里。湖水颜色多变,蓝、黄、浅灰、乳白带绿。早年沼泽湖与加勒比海相通,1950年代沿海修建了一条狭窄的沙质堤坝,我们正行驶在堤坝之后的修筑的公路上。然而,湿地生态系统主要依赖的海水和淡水的自然交换却被隔阻了,盐度水平失衡,导致近29000公顷的红树林消失。在地球上,为了交通方便,破坏生态和自然风景已成常态。
汽车行驶着,湖中散落着船屋,船屋前插着很多木杆。鱼鹰、鹭鸶站在木杆顶上,目光如炬地盯视着湖面。那些船屋多是稻草木板搭成,铁皮屋顶。稍微讲究的房子周围还有一圈走廊。这里鱼产丰富,一条条的鱼晾晒在走廊上,绳子上的衣物随风飘动,一只狗站在衣服下。这是塞纳加(Cienaga)城水面的那部分,而“Cienaga”在西语中就是沼泽的意思。印度喀什米尔的达尔湖和秘鲁的提提卡卡湖也有类似的湖上人家,但此地的红树林风景却迥然不同。
这个哥伦比亚唯一的高脚屋镇,街道就是湖,通行靠船,只有一座桥通往教堂。马尔克斯在回忆中说:“从巴兰基亚到阿拉卡塔卡,只能乘坐破烂不堪的汽艇驶出殖民时期奴隶挖成的航道,穿过一大片浑浊荒凉的沼泽,来到神秘的塞纳加,最后转乘普通列车。……”有一年,作家乘夜船经过大沼泽:“只见渔火点点,如水面繁星。水面上住着无数渔民,却只闻其声未见其人,他们的呼唤在沼泽上留下幽灵般的回声。突然间一缕乡愁涌上心头。”
经过沼泽水上城之后,路面稍宽。路旁,草棚一字排开,鲜鱼吊在棚子上,草篮里摆满晒干的虾仁。此地为生艰难,但那简单淳朴的美让我想到很久以前的中国江南。也许只有坐在空调车上远距离观看,才能欣赏艰苦岁月之美吧?“怀旧总会无视苦难,放大幸福,谁也免不了受它的侵袭。”(马尔克斯)
公路再次拓宽,此时已行车3小时。沿途风景从茂密的热带树林逐渐变得树木稀疏,盐碱地或红土地丘陵。我们看到山了,那就是圣玛尔塔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 de Santa Marta)。这道山脉与安第斯山并不相连,最高峰为5700米,距离加勒比海岸仅42公里。
公路开始分叉,一边是去圣玛尔塔,另一边去波哥大。此去波哥大近1000公里。正逢旱季,绿色难觅。12月雨季来时,天气会凉下来,“黄昏时分,当12月的雨后,空气如钻石般晶莹剔透。圣玛尔塔内华达地山脉白色之巅仿佛就在河对岸的香蕉种植园里。在山脉悬崖上,阿鲁阿科族印第安人背着满满的一袋姜,像蚂蚁般地沿着蜿蜒的山脊前行。他们嚼着可卡叶以减轻生命之重负。“(《活着为了讲述》马尔克斯)
公路上,车辆多了起来。货运卡车在超车,速度极快,年轻人站在卡车箱里向我们微笑打手势。风越来越大,光秃秃的山坡上长着仙人掌类植物。虽然此地距离卡塔赫纳只有200多公里,但已是大地焦渴的半干旱区。
二
清晨,我们从圣玛尔塔前往阿拉卡塔卡(Aracataca)。阿拉卡塔卡是马尔克斯的外祖父的家,也是他的出生地。很多年前,二月的一天,马尔克斯陪母亲搭船回阿拉卡塔卡变卖祖产。那艘夜行船上钉着高低不同吊床吊钩,甲板上放了木凳。乘客推推搡搡,提着大包小包上船,不一会儿,货物和鸡笼甚至活猪抢占了木凳,而下等妓女永远霸占着客舱里的两张上下铺。这一画面让我想起十多年前搭夜船离开达卡,在甲板上与山羊鸡笼挤在一起。我还想起从巴西玛瑙斯出发的亚马逊河船上的吊床,床上的睡客鼾声如雷。如今这一带已通公路,既不要坐船也不用坐火车了。
出了圣玛尔塔,车向东南行。不久就驶离海岸,深入腹地。沿途可见大片香蕉种植园,成熟的香蕉套着塑料袋。这里的香蕉园与瓜地马拉类似,以前都属于美国联合果品公司,该公司不仅控制南美一些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还参与颠覆政权。在马尔克斯记忆中,此地的香蕉园犹如独立王国:“围着通电的铁丝网,像硕大无比的鸡笼,夏日凉爽的清晨,被烧焦的燕子黑压压一片……透过铁丝网,有时能看见戴着宽檐薄纱帽、穿着麦斯林纱裙,弱不禁风的美人拿着金剪刀在花园里修剪花枝。”
公路穿过香蕉园,时不时地还穿过河,“每条河边都有一座村庄,火车怪叫着驶过铁桥,在冰冷的河水中洗澡的女孩如鲱鱼般跳了起来,乳房一闪,让乘客不知所措。”(马尔克斯)如今那些河中仍有洗衣和洗澡的人,但铁路早已不再载客。阿拉卡塔卡河的河水扔然清澈,河边的铁皮房顶仍然生着锈,屋顶上仍然落着候鸟或迷途的鸥燕。
阿拉卡塔卡小镇沿河而建,“阿拉”的意思是河,“卡塔卡“是族人对首领的称呼,因此当地人只称此地为“卡塔卡”。小镇口摆着一串竹木搭成的小摊,所售都是极为便宜的日用品,穷困显而易见。小小的火车站位于城之东南,距离马尔克斯故居步行仅10分钟。当年马尔克斯回故乡,就在这里下火车。“火车在时,我们没有感到全然孤独,但当它突然撕心裂肺地鸣着笛开走后,妈妈和我相对无言,无助地站在大太阳底下。镇子沉甸甸的凄凉扑面而来,锌皮顶、木结构、长廊形阳台的老车站,像挪到了热带的西部片场景。”作家童年时乘坐的火车也分为三等,“政府高官和香蕉公司高级职员坐一等座,过道里铺着地毯,包着红色天鹅绒的扶手椅可以转向。要是香蕉公司老总、老总的家人和贵宾乘坐,车尾会加挂一节豪华车厢,镀金窗檐,遮阳玻璃,外加露天茶座,可以在旅途中坐在小桌边喝茶。”
我们的车继续向西行驶,驶过一座座白色或其他颜色的矮小平房。一些街道仍然是土路,街边人家都装了铁栏门窗。车子经过玻利瓦尔广场,白色勾红边的教堂,一家漆成大红色的超市,两家咖啡店……在马尔克斯回忆中,此地曾有电影院和红灯区,街上的房子仿佛来自童话世界。那时,香蕉公司的老总开着豪华敞篷车,同车的德国牧师端坐如国王。此时此地,到处都是冷冷清清,布满了灰尘,完全不像一座4万人口的城市。
虽然镇子上有好几幅马尔克斯的画像,但却无任何有关作家的纪念品,既无钥匙链、体恤衫和冰箱贴,作家的故居也不收费。1961年以后,马尔克斯主要居于墨西哥城。2014年,作家去世时,阿拉卡塔卡曾力争作家叶落归根,但马尔克斯的骨灰被葬于卡塔赫那——那个连他的故居都没有保留、让他爱恨交加的城市。
从市中心向南,马尔克斯的故居在一条窄街上。这是马尔克斯外祖父母的老宅,也是马尔克斯成名前,他的家族唯一的产业。白木屋的屋顶很陡,如伞般地张开,那把“大伞”下接出宽回廊以遮挡阳光或雨水。据说早年当地的房屋都有雪松板高顶,这所房子重建时也保留了雪松板,但如今的民居大多是低矮的水泥盒子。
木屋内的房间一字排开,中有走廊。第一间是会客室兼私人办公室。屋内摆了书桌和摇椅,马尔克斯外祖父的照片最为醒目。照片上的老人着浅色西服深色领带,神态安详又骄傲。在马尔克斯记忆中,他的外公身材矮胖,气血旺盛,光亮的头皮上有些许白发,髭须硬朗,戴着一副金框圆片眼镜。“天下太平时,外公说话不紧不慢,善解人意,秉持息事宁人之道,但他的保守派朋友们回忆说,他在战场上却步步紧逼,很难对付。”
马尔克斯在外祖父母卧室里出生,这间屋里挂着两位老人的合影。作家出生前,其父母搬来与外祖父母同住。马尔克斯出生不久,其父母又迁往巴兰基亚谋生。马尔克斯被留在卡塔卡,由外祖父母照料长到8岁,而外祖父尼古拉斯对其影响深远。
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家有薄产,年轻时为自由党作战,解甲归田后,回到祖籍巴兰卡斯。后来他为了捍卫荣誉在决斗中杀了人,为免祸漂流在外多年,最终接受阿拉卡塔卡的税务官一职,于是举家迁此定居。阿拉卡塔卡位于腹地,极其闭塞,海风不至,非常炎热,绝非梦想中的乐土。然而,尼古拉斯一家人迁来不久,香蕉种植园开始造就当地的繁荣。当时,属于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种植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外地人纷沓而至。他们来自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甚至远至意大利和叙利亚。来到此地并非都是劳工,还有监狱的逃犯,法国记者,可谓芸芸众生,形形色色。那时行走镇中,既能听到午后单簧管吹奏着忧伤的华尔兹舞曲,也能看到傍晚下工的黑人高歌狂舞。尼古拉斯的一个棋友来自比利时,此人打过仗航过海,还是涉猎甚广的艺术家,马尔克斯看到外面的世界,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
故居内,外祖父尼古拉斯的金银作坊紧邻着办公室,那里放了一些简单的工具,地板上插着铁制金鱼。据马尔克斯回忆,外祖父的手艺来自祖传,他会制作身子会动、镶着绿宝石眼睛的小金鱼。看到那些金鱼,读过《百年孤独》的人立刻就能想到奥雷里亚诺。他年老归家后每天做两条小金鱼,做到25条时便放入坩埚里熔化,然后再从头开始。据说《百年孤独》中的乌尔苏拉之原型,就是马尔克斯的母亲露易莎·马尔克斯。露易莎出生于普通人家,成长于香蕉公司昙花一现的繁荣时期,曾在圣马尔塔学校受过富家小姐般的良好教育。在现实生活中,露易莎生育时间长达20多年,生有11个子女,而马尔克斯的父亲还有4个私生子。在马尔克斯成长的日子里,这个家庭食指浩繁,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但露易莎似乎并不怎么发愁。2002年,她在卡塔赫纳逝世,享年97岁。那时她已经有了67个孙子、73个重孙子和5个重孙女,据说其葬礼隆重如民族英雄去世。
在这个故居里,外祖父尼古拉斯接待过一些大人物。虽然他无权无势,但因其作战资历,处事公平而备受尊重,还做过香蕉种植园劳资双方谈判的调停人。然而那次调停并未成功,暴动的香蕉工人遭军队屠杀,据说死者三千。成年后,马尔克斯作为记者曾经采访过屠杀事件的幸存者和目击者。他还梳理了报刊和官方文件,最终却发现被害人数的真相始终无迹可寻。
故居走廊拓宽的一段便是餐厅,这是整栋房子中最明亮宽敞的一间。一张长方型的饭桌,一盏玻璃吊灯,马尔克斯回忆道:“这座老宅不仅是一个家,更是一个镇子。”这“镇子”里的人一直在思乡,如果没听说老家巴兰斯卡的闲言碎语,这一天就过得不完整。这家人每天都接待下火车来此的老家人,那些人来自极为偏远的地方,多半与马尔克斯家族沾亲带故。老家来人总会留下吃饭,一个流水席总要吃上好几轮。关门就寝时,客人自选地方挂上吊床。那些吊床高高低低,一直挂到院子的树上。
除了客人,这一家“总共15个孩子,只要有吃的,随便一坐,吃起来就像有30个孩子。”当马尔克斯的父亲追求其母时,对这个有私生子的未来女婿,外公竟然在道德上有所忧虑,而外公自己除了3个婚生子,还有9个私生子!作者回忆道:“那些年里,有一天最神奇:家里来了一群着装统一、打着绑腿、靴后跟绑着马刺的男人。他们的额头上都涂有圣灰十字,他们都是‘千日战争’时期上校在‘省’内各地留下的私生子。他们从各自家乡赶来为外公庆生,但晚到了一个月。”有一次马尔克斯在某地火车站的饭店吃饭,多年后得知那个女店主竟然是他的一个姨母——又一个外公的私生女。最有趣的是,马尔克斯在波哥大路遇一位老人,那人长得太像外公乃至他几乎脱口喊出“外公”。老人问道:“你那著名的外公叫什么名字?”听了回答后,那人说:“我就是你外公的长子啊!”马尔克斯解释是因家庭不愿女儿下嫁,乃至满街都是私生子。无论何种原因,我的感觉是那个时代的哥伦比亚人根本不在意私生子。
故居餐厅的角落里挂着一捆香蕉,看板上写着香蕉种植园的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香蕉出口带来该地区的繁荣。1929年,哥伦比亚成为世界第三大香蕉出口国。”阿拉卡塔卡因香蕉经济而盛而衰,《百年孤独》中的布恩迪亚家族定居地“马孔多”的名字就取自附近的香蕉种植园。
事实上,自马尔克斯父母结婚后,此地就开始衰落。20年前,因躲避准军事武装的暴力,此地人口又再次暴增,但这里几无工作机会,却有毒品问题。直到2014年,当地还只有一家小旅舍,住客主要是马尔克斯的铁粉。
故居的厨房位于餐厅之后,马尔克斯家女眷从这里端出面包甜点,加入里奥阿查甘薯的浓汤,早餐的鸡蛋黄油玉米饼、炖小山羊、烹好的甲鱼和虾子。这个家族的女性坚强宽容,贫贱不移。捉襟见肘时,外婆米娜带着她那帮稀里糊涂的女人做了家里的顶梁柱。正是家族里众多的女性和儿时众多的女佣,涵养了马尔克斯的性格和思维方式。
马尔克斯童年的睡房很小,内有吊床。墙上的那张照片就是《活着为了讲述》的封面照,我猜那恐怕是作家童年唯一的单人照。这里的一个房间做过病房,马尔克斯6岁时就在老宅里见过生死。在回忆录中,他还提到卧室里有个祭坛,摆放着真人大小的圣徒像,比教堂里的更逼真、更阴森。不要说孩子,我住在有圣像的房子里都觉得阴森可怖。
故居的后院曾经花团锦簇,有时茉莉花香浓郁得让人无法呼吸。后院还曾有精心打理的菜园,山羊、母鸡和猪在牲口圈里和平共处。如今参天的大树仍在,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作家提到的栗树。后院的两面墙上都有马尔克斯的画像,一幅严肃一幅亲切,画像旁都写着他的爱称“Gabo”。
马尔克斯离开此地后,随父母先后居于巴兰基亚和苏克雷,然后就去波哥大上法学院。家境贫寒,父母供他上大学不容易,而他的父亲更是将自己未圆的大学梦交给儿子去完成。大学二年级时,马尔克斯打算为写作而辍学。就在那个暑假,他陪母亲露易莎回来卖这栋老宅。回乡下后,母亲带他拜访老友巴尔沃萨。巴尔沃萨医生仁心仁术,在当地很有名望,也曾拥有香蕉时代最好的药房。但彼时的阿拉卡塔卡几近穷途末路,青天白日里,秃鹫就在医生房顶上跳跃,医生说:“夜晚更糟,能听见死人在街上走。”
露易莎指望着医生能说服儿子重返校园,但医生却对露易莎说:“个人志向与生俱来,背道而行有碍健康,顺势而行妙药灵丹。“故乡之行后,马尔克斯像战场上的战士一样视死如归地发下誓言:“要么写作,要么死去。”
在码头上,作家挥别母亲后即飞奔至《先驱报》的办公室。他灵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连气都没喘,就用他妈妈的话作为第二部小说的开头:“我想请你陪我去卖房子。”
我们的车子再次驶过破败萧条的镇中心。蕉林葱郁,河流蜿蜒,阿拉卡塔卡消失在苍茫之中。鸦雀归林,为这片孤独的土地带来些许喧闹。
(记于2020年2月12-13日。文中所引《活着为了讲述》摘自南海出版公司,译者李静,作者亦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