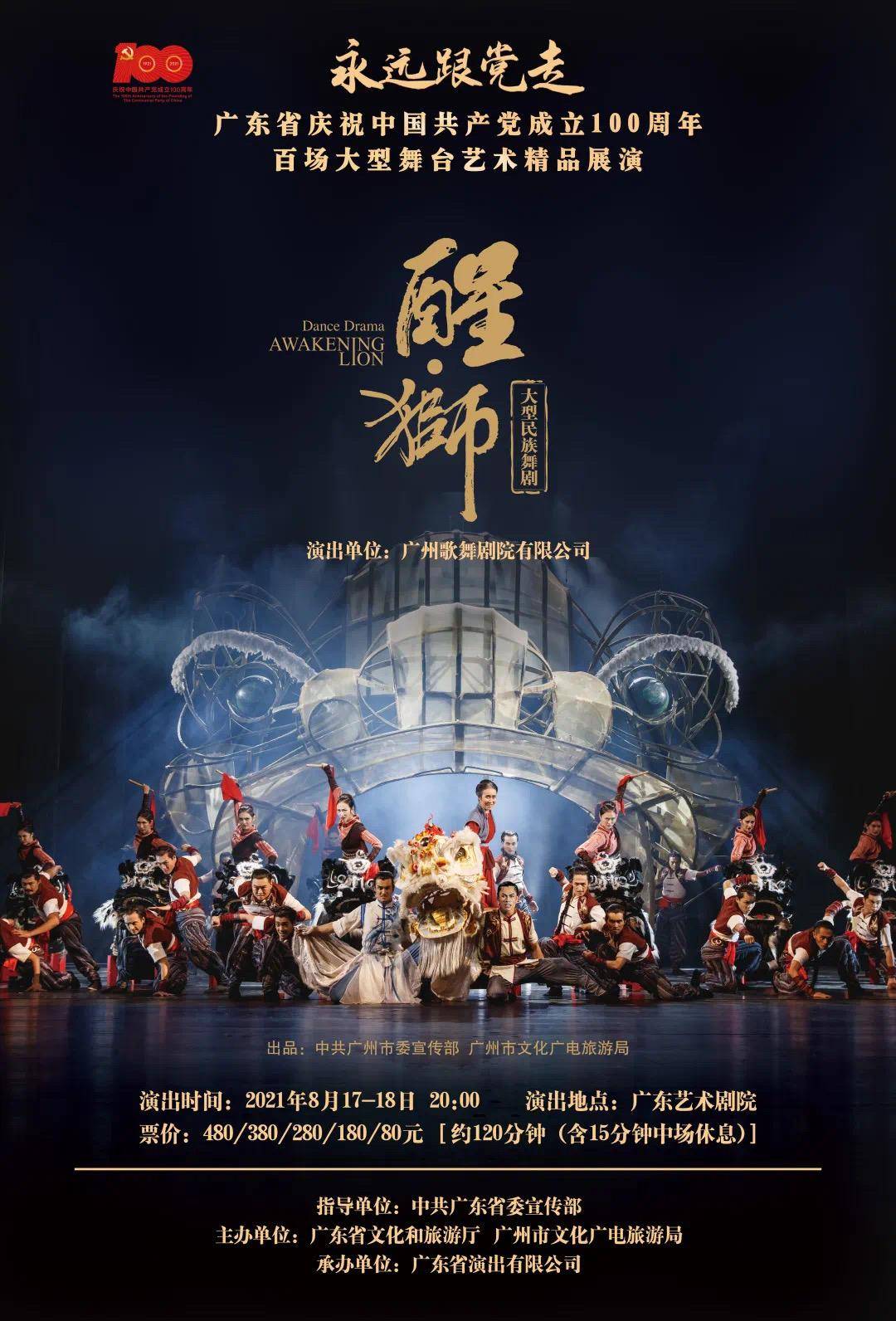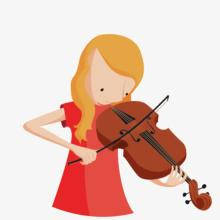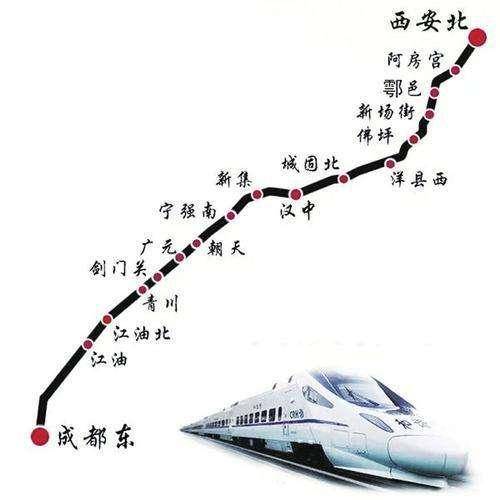一栋红楼,我在其中委身了十七年。红楼不大,小小的,矮矮的,坐落于一片杂乱无章的民居中,显得灰头灰脸。小楼所处的位置叫莲湖巷,巷子窄窄的,刚好能容纳一辆轿车通过。可在巷子里穿梭的,更多的是三轮车和架子车。三轮车是小商贩的谋生工具,架子车则是收废品者的仓储。三轮车和架子车上,常常垒得层层叠叠、晃晃悠悠,人在它的旁边经过,不由得心跳加快,唯恐它上面的某个物件坠落而下,砸伤自己的脚面。
巷子是条断头路,长不过百米。巷子的开端与一条名为大莲花池街的街道相连,终端是一栋横着身子的民居,它拦住了这条小巷的去路。小巷的北侧是几户民居,民居背后则是莲湖公园;小巷的南侧是一个派出所,往里就是我所委身的红楼,在派出所和红楼之间狭小的空隙里,拥挤着一堆杂乱的房舍。红楼再往里,又是一群更加密集却没有章法的民房。派出所的大门朝大莲花池街开着,它只是把自己的后背,甩向了小巷。而在小巷里,唯一能称得上国家单位的,就是这栋红楼。红楼高不过三层,原为简易建筑,一度墙体裂缝,摇摇欲坠,后来经过修葺,又经过粉饰,它终于有了新的容貌,呈现出少妇脸庞般的羞涩与红晕。
有六户居民的房舍直面着小巷,其他的则是民居与民居交错纠缠,遁入幽幽之中,被杂乱所遮掩和覆盖。六户面临小巷的住户,一户人家是两层小楼,楼的墙面上贴着白色的瓷片。从那户人家的装束来看,他们应该是一个回民家庭。那户人家的楼外,横着一道黑色的铁栏杆。栏杆也好,楼门也好,总是紧闭着。偶尔会看到那家的女主人拎着笤帚在打扫卫生,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洁净的追求和护卫。墙面不时出现用墨汁刷写的留言:“乱倒垃圾者全家×××。”从中可以解读出不讲卫生者对他们生活造成的烦恼,也足以看出这户人家对乱倒垃圾者的极度恼怒。
另一户直面小巷的户主是谁,我不知道。我所看到的是,那栋房子尽管缩进了小巷,但因为距离大莲花池街比较近,因此它成了门面房。租用它的人似乎经常性地变换,一个面孔刚刚熟悉,没过多久就消失了,代之的是另一张陌生的面孔。我记得在十多年前吧,它的门额上写着某某工贸公司的招牌,里面在批发白鹭电池。那个年代刚好兴起传呼机,几乎人人的腰间都挂有一个“铁鸟”。传呼机要用电池,一个月就得换一节。于是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我都持续地到他们那里买电池。那里的电池是正牌货,比市场上便宜五毛钱。公司里的老板三十七八岁,个子很高,脸像喝过酒似的,呈现西红柿的颜色。他性格比较张扬,似乎对自己的生意无比满意。有一天我在一家面馆吃面,碰到这个老板,他在向面馆老板吹嘘自己的生意如何红火,数钱都把手数得酸疼云云。对我留下好印象的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人,他和老板是兄弟关系还是合伙关系,我并不清楚。我所观察到的结论是,在这个公司,以职位论大小,老板下来就数他了。也就是说,他是公司的二把手。他个子不高,但五官清晰,脸上的表情浮现着隐隐的忧郁,又潜藏着隐隐的高傲。我去他那里买电池,他会冲着我一笑。路上相遇,他朝我点点头,我亦朝他点点头;他朝我一笑,我亦朝他一笑。我们俨然已经是老熟人了,但却几乎没有真正交谈过,以至于他大概不知道我姓甚名啥,我也不清楚他的尊姓大名。忽然间他消失了,像一屡微风不见了踪影,却让我不由得滋生这样的慨叹:此生曾经与多少人相逢,但相遇者却甚为寂寥;对于那些整天和我们擦肩而过的人,有几个人能在我们的心里留下印痕,又有多少人不过是我们行路途中随意瞥了一眼的风景?
批发电池的公司撤离后,这个门面房不停地转换着自己的角色。它有时候大门紧锁,有时候大门开启一条细缝。现在它是一个裁缝部,里面端坐着一个中年妇女。裁缝部并不做完整的衣服,它只是承揽一些修修补补的活儿,比如为裤子锁边、为棉袄加拉链、缝合衣服咧开的伤口等等。裁缝部没有招牌,门外横着的那条竹竿上悬挂的那几条旧裤子,仿佛就是裁缝部的经幡,随风招摇飘荡,惹人眼目。
莲湖巷里还有一个门面,大概算得上几个门面中最热闹的一个了。它几经变化,现在门额上悬挂的牌子叫“文化娱乐中心”。看到这个名字,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挂羊头卖狗肉”的民间俗语。它既不文化,也不娱乐,更谈不上中心。说白了,它就是个麻将馆。早上从它门口经过,它似乎是一个早餐摊点。巷口那对卖豆腐脑的夫妇,他们把摊子扎在路人经过的人行道上,但若有食客喜欢坐着就餐,他们就引领食客步入活动中心,让他们把麻将桌当餐桌。麻将桌上扔着散乱的麻将,有红的,有绿的,有蓝的,有白的。陪着麻将狼吞虎咽,也算得上早餐的特别之处。十点钟过后,活动中心就响起了唏唏啦啦噼噼啪啪的响声。透过宽阔的玻璃门,可以看到好多麻将桌旁,坐满了搓麻将的男女,年老者居多,但也不乏青丝飘飘的年少者。四个人在打,却有五六个人在围观。于是摸到好牌的兴奋和老不和牌的沮丧,交织成一片杂乱的叫声喊声和叹息声,让活动中心里人声鼎沸。偶尔,活动中心里吵得天翻地覆,那肯定是在付账或算账上出了差错。五毛钱或一元钱,足以让那些怒不可遏的麻友将麻将桌掀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