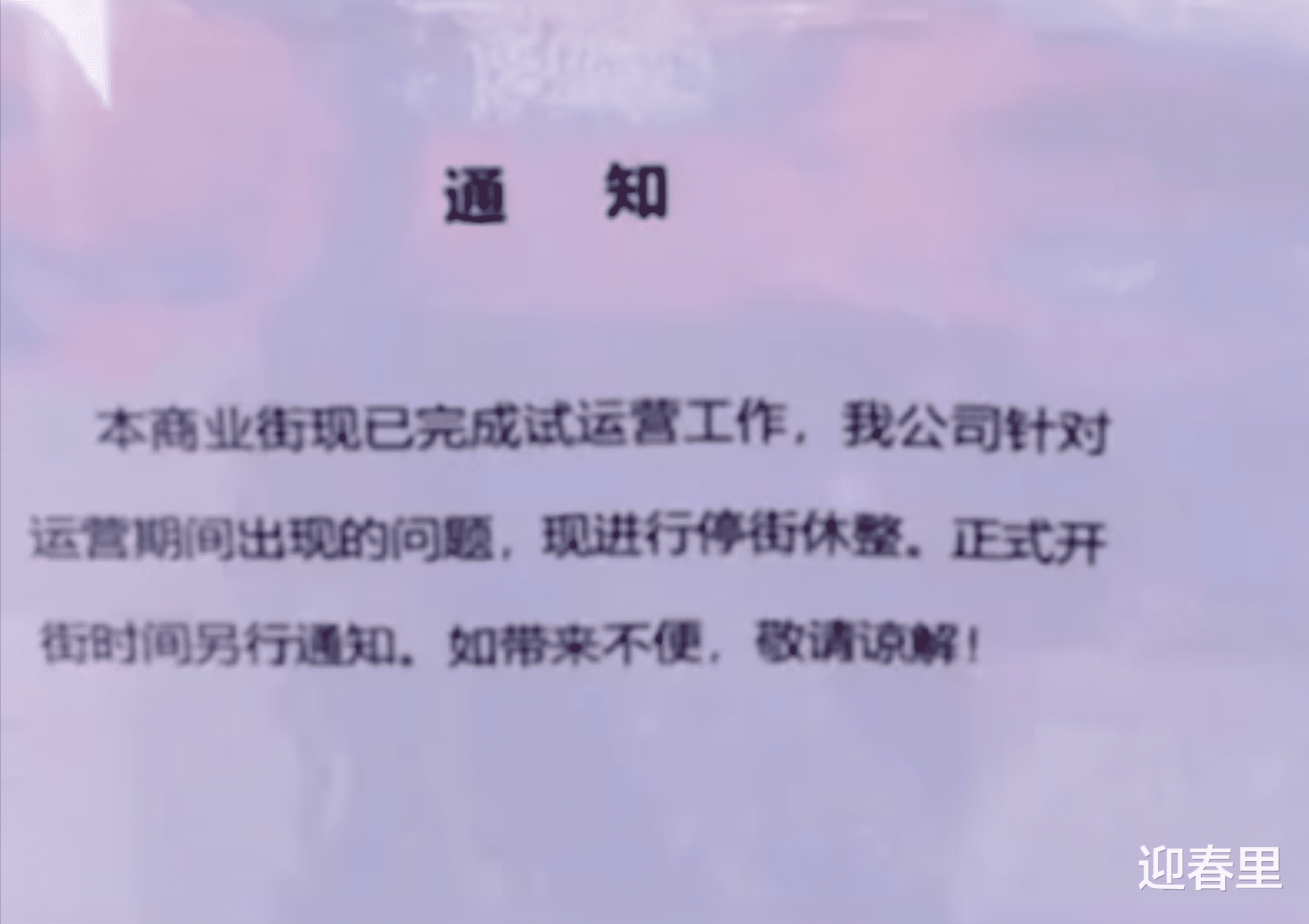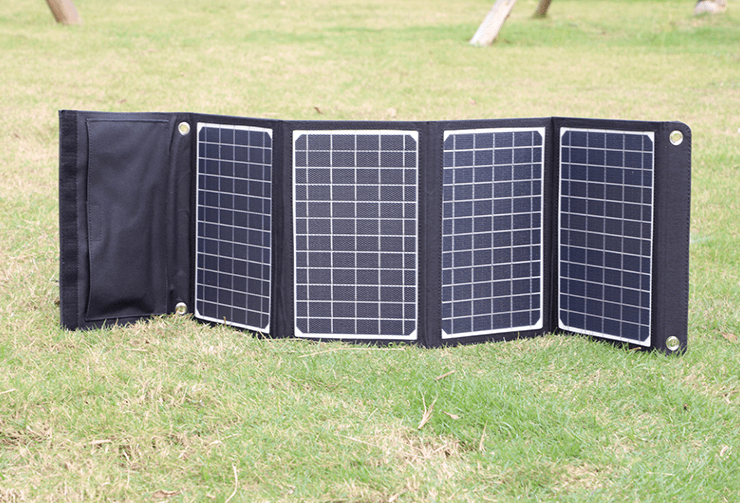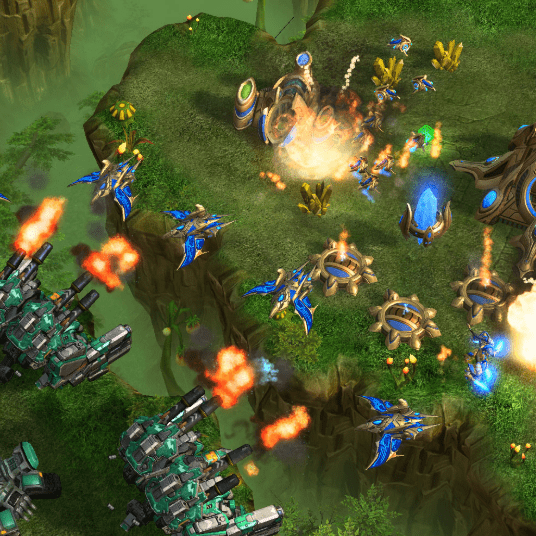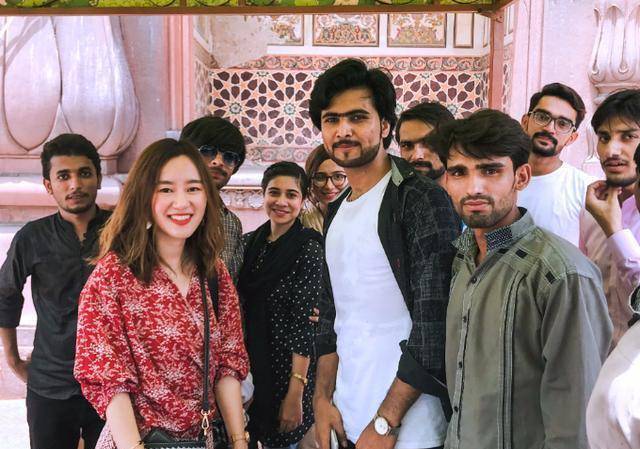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脉
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脉
阿富汗再一次成为了世界关注的中心。而这不过是这个山地国家自1979年以来悲剧命运的再一次回旋,甚至不需要休止。
8月16日,阿富汗原总统加尼(《如何修复失败国家》一书的作者)从喀布尔机场消失,并将首都和政府留给塔利班接收人员时,瓦尔达克省(普什图人占该省七成人口)省会迈丹城的女市长扎丽法·加法里只能对媒体说:“我正坐在这里等待他们(塔利班)到来,没有人帮助我和家人,我和丈夫只能与他们坐在一起。”
其实,无论是阿富汗的末代王室、前总统卡尔扎伊、加尼还是塔利班,都可谓是普什图族内部的产物。而普什图人并不占阿富汗人口的绝对多数,其在阿富汗历史舞台上崛起,也是相对晚近的事。
阿富汗的波斯文化底色
位处欧亚大陆心脏的地理位置,以及横贯其间的几条连接东西、南北方向的干道,使得阿富汗民族间的通婚混血普遍存在。
兴都库什山脉以北的居民,由于过去突厥—蒙古民族政治的强势,大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蒙古利亚人种体质特征。而在阿富汗北部讲“达里波斯语”的地区,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的融合,则使得居民兼有红或金发、浅色眼睛和单眼皮、高颧骨的特征。早在明代,通过和来访使节的接触,汉文史家就已经用“半鞑半回”一词来形容当地原住民。
 兴都库什山脉附近的旅行者
兴都库什山脉附近的旅行者
而在阿富汗南方,俾路支人、努里斯坦人和普什图人聚居区内,所谓的“地中海—印度型”体质特征开始变得明显。他们多表现为淡金色的头发,以及蓝绿混合色的眼睛。
这些民族中一部分是当地的原住民,但由于近代国家边界的分割而成为跨境民族。如普什图人在阿富汗境内和定居巴基斯坦斯瓦巴坦山区的人口,几乎一样多;而塔吉克人除了塔吉克斯坦外,也广泛分布于阿富汗北部。
而移入当地的人群中,哈扎拉族、艾马克族是蒙古征服时期镇戍军人和本地人群通婚的后裔;乌兹别克人的踪迹,则始于“月即别汗”南下入侵帖木儿汗国时期。
因此,阿富汗的民族是多元的,任何一个民族相对其他都不占据绝对人口优势。而跨境民族的普遍存在,更是加剧了外部国家对内政事务的影响。
人群的多样性,反映了阿富汗往昔的历史。属于东部伊朗语族的大夏(贵霜)人、跟随亚历山大东来的古希腊人,还有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由内亚草原西迁至此的突厥和蒙古人,先后建立起强大帝国,又随即瓦解于后来的征服者之手。
不过非常明确的一点是,10世纪之前在今日阿富汗疆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是波斯文化和具有波斯血统的统治者;10世纪之后,则是突厥—蒙古文化占据上风。然而,即便是在突厥—蒙古人成为政治上的统治者时,阿富汗当地的主体居民仍然是把自己上溯至波斯神话人物佐哈克(?a??āk)的古儿人(Ghur)。
同样出身于古儿人的迦儿惕家族(āl-Kart),则以高超的政治手段费心周旋于蒙古人和地方军阀之间。在蒙古征服蹂躏中亚之际,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元代称“也里”)成为一个稍稍平静的绿洲,从而庇护了不少流亡至此的文人和圣徒。
 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的普什图人
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的普什图人
迟到的“普什图人”
作为山地之国,阿富汗的地形也决定了其境内只有有限的几个地方,才可能发展出较大规模的定居社会。
兴都库什山脉的主轴线,从东北向西南在该国中部展开,东北部则是覆盖着冰川的巴达克山山脉,东部是以喀布尔山谷、努尔斯坦为主的四个山谷地区,北部则有昌格尔山。
于是,仅有阿姆河流经的突厥斯坦平原、赫拉特河谷,以及赫尔曼德河谷—锡斯坦盆地等少数由内陆河流经的平原地区,适合较大规模的人口定居和经济生产。
因此,在16世纪之前,阿富汗境内的历史名城,也主要分布在上述三个地方,各地之间由固定的商队道路连接。
帖木儿兴起之前,穿越中亚的路线往往会选择偏向北方的路线,即从巴达克山经过塔卢坎到达巴尔赫(马扎里沙里夫西北20公里),再南下赫拉特或喀布尔。这样可以避开中亚各蒙古汗国混战造成的危险。
而帖木儿之后,直接穿越突厥斯坦,从河中地区渡过阿姆河南下赫拉特,成了主要的路线。沿着哈烈河谷前往赫拉特的路线,从15–16世纪至今从未发生大的改变。
直到这个时期,普什图人仍然主要活动在阿富汗南部。少数旅行家如伊本·白图泰偶然记录过这些南部的“山民”,但更多时候他们是透过为商队提供保护,来参与国家的经济生活。
所以,今日在阿富汗占据统治地位的普什图人,在该国历史舞台上是一个明显的迟到者。普什图人得名于他们的语言“普什图语”(Pashtō),这是东部伊朗语的一支,人种为高加索人。他们是阿富汗南部山区的游牧人口,而在历史上阿富汗的政治文化重心一直位于北部。
普什图人分为杜兰尼、吉里齐等多个分支。每支均以共同的父系祖先作为谱系的起点,而各个普什图分支,则以传说中的“Qays 'Abd al-Rashīd”作为共同的始祖。
16世纪,伊朗萨法维王朝的阿拔斯一世,曾委任Pōpalzay部落的首领作为普什图联盟的指挥官。众多普什图部落开始组成更大的政治联盟,参与周边政权的权力游戏。

1709年,由忽塔齐部落首领Mīr Ways领导的吉里才(Ghilzay)起义,将阿富汗南部地区从伊朗萨法维王朝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而在“波斯之剑”纳迪尔沙统治伊朗时期,他通过拉拢杜兰尼部落分支“阿布达里人”,换取后者的军事支持,自此也开启了普什图人(以杜兰尼部落为主)由南向北扩张的步伐。
普什图人在纳迪尔沙时期被大量吸收进军队,并开始学习如何管理国家。在波斯和莫卧儿帝国衰落并走向解体的过程中,普什图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阿合马沙推行的扩张政策,使这个国家一度扩张成“从呼罗珊直到恒河平原”的强大政治势力,并在此后成为阿富汗地区的主导力量。
 阿富汗瓦尔达克省迈丹城街
阿富汗瓦尔达克省迈丹城街
普什图人的“政治晚熟”
18世纪下半叶,普什图人开始向北征服哈扎拉人的领土,而第二波向北方的殖民迁移,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普什图人渐渐占据了长期由突厥—蒙古系人群游牧的巴德吉斯草原和阿富汗突厥斯坦地区。
由于普什图人武力强盛,少量的普什图迁居人口(每次约数千户)在上述地区,均成功地压制了原居的哈扎拉人和艾马克人的势力,并获得了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政治和经济领导权。然而,这也开启了之后普什图人和哈扎拉人群之间长期的冲突和纷争。
哈扎拉人应该是蒙古西征之后戍守当地的各个千户(古代蒙古族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后裔,他们与当地的居民通婚并世守于此。13–16世纪文献中,活跃于阿富汗—伊朗—北印度地区的一支蒙古混血军人组成的力量“哈剌兀纳思”(Qaraunas,哈剌意为“黑色”,是指他们的肤色较纯种蒙古人更黑,兀纳思可能与“匈人”有关,印度人把一切来自北方的游牧力量都称作“匈”),应该与哈扎拉人祖先有关。
 阿富汗瓦尔达克省迈丹城街
阿富汗瓦尔达克省迈丹城街
当代哈扎拉人,主要聚居在阿富汗中部的巴米扬、哈扎拉札特和阿富汗突厥斯坦。他们以农耕生活为主,并改宗什叶派,因此在文化亲缘性上更靠近伊朗。但直到19世纪,哈扎拉人日常使用的波斯语中,仍然包含有大量的蒙古语词汇。
因为宗教和民族的差别,哈扎拉人长期以来受到以普什图人为主的阿富汗主流社会的系统性歧视和迫害。在第一次塔利班运动时期,塔利班鼓吹“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应该回自己母国,而哈扎拉人只能去坟墓”的极端民族政策,导致许多哈扎拉人被杀。
作为阿富汗历史舞台上的迟到者,普什图人在国家构建和运作国家机器方面,并没有太多的经验。在这场权力游戏中,他们甚至要通过学习突厥波斯人的政治经验,来建构并完善自己的国家。
直到现在,普什图语中的大多数与政治、政治机构相关的术语中,还保留有大量突厥语(甚至蒙古语)词汇。由此也可以看出普什图人治国知识和政治传统的来源。例如表达主仆(并引申为领导者—追随者)关系的术语“naukarān”,就来自蒙古语“那可儿”(n?k?r,伴当),而这个反映私人之间隶属关系的术语,同样也被用来形容政府机构中的管理者与雇员关系。
普什图人日常的政治生活,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传统部落习惯的支配。
 喀布尔山谷
喀布尔山谷
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s)是研究阿富汗部落政治习惯和组织方式的权威。他认为在普什图人的社会中,每一个人在空间结构中的位置取决于他的居住地,在社会等级结构中的位置取决于父母的身份,因而呈现出相当强力的固化倾向。
而普什图人的政治联盟,则建立在领导者与个人之间缔结的契约上。这种契约受到部落习惯、传统而非成文法的约束,并完全以现实目的为基础。因此,阿富汗各个政治派别之间的变节、重组,常常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发生。除了现实目的外,对抽象原则的效忠,以及法条的约束,在阿富汗的政治传统中即便不是毫无意义,其可靠程度也是值得怀疑的。
政治联盟的易变性又带来另一个结果:以家族为单位的政治团体,并非建立在内部合作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亲属之间的普遍竞争中。因此,来自兄弟之间的竞争,构成了政治生活中最基本、也往往是最激烈的冲突。这也是那句普什图谚语所展示的图景—“我和我的兄弟联手对抗我的堂兄弟,我和我的堂兄弟联手对抗陌生人。当没有外人时,我对付我的兄弟。”
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中写道:“命运和人类在玩着棍子击球的游戏。”如今新的一局已然开启。或许,阿富汗问题的渊源应该归因于普什图人政治的晚熟。对于其未来命运,恐怕只能等马球触碰底线的那一刻才能解答。
作者 | 米兰沙
看世界杂志新媒体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