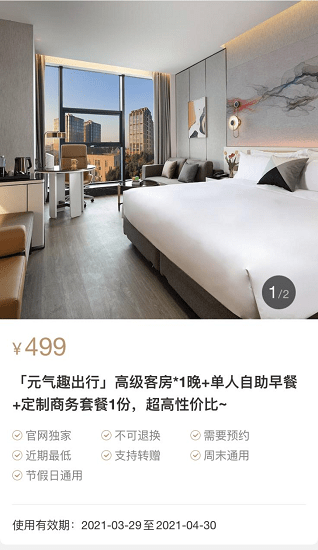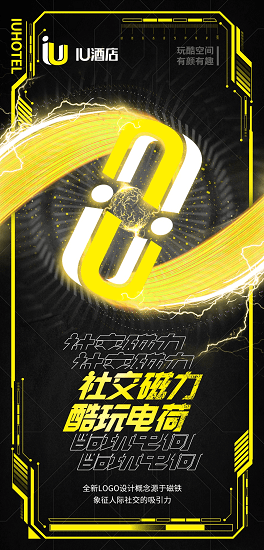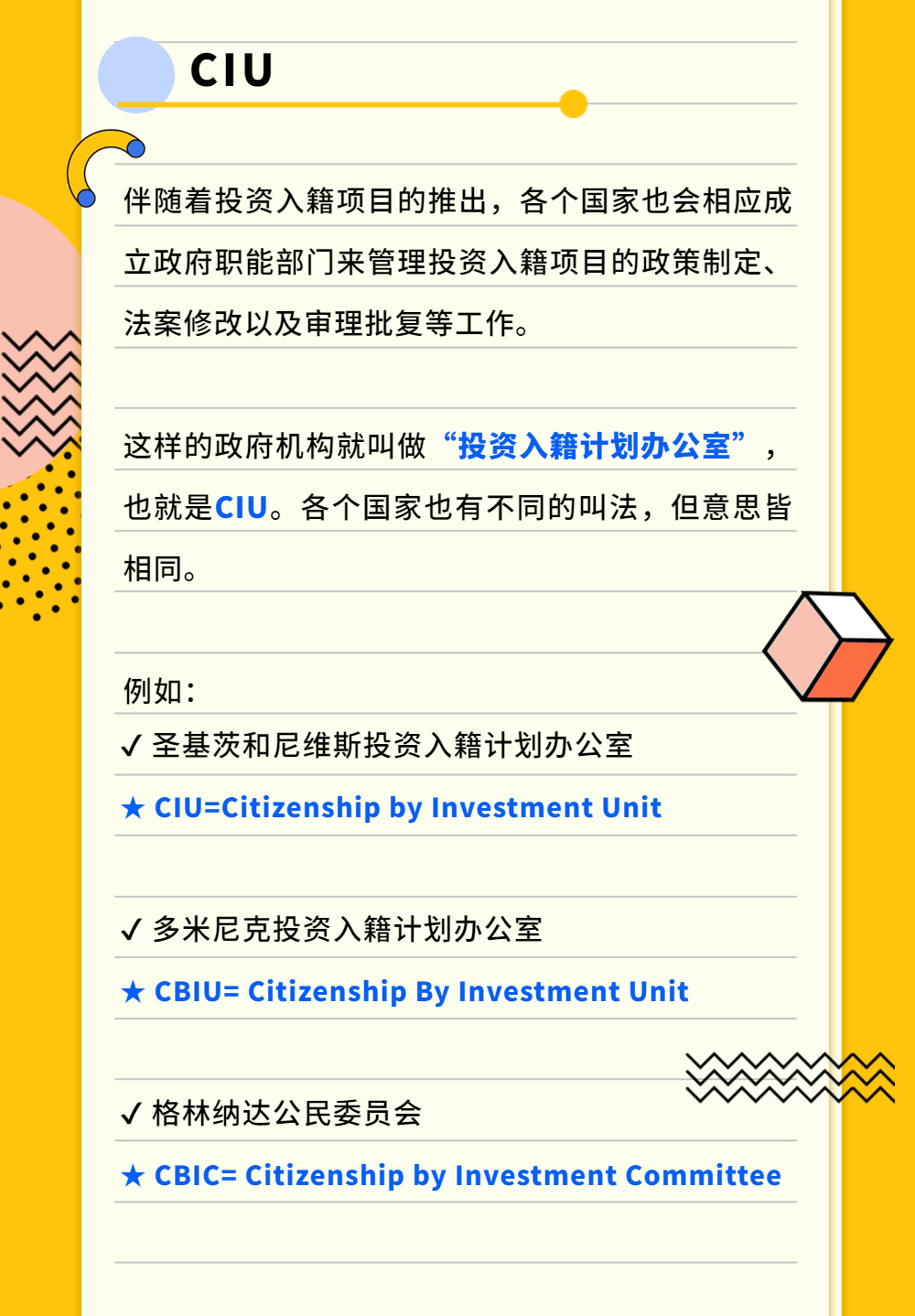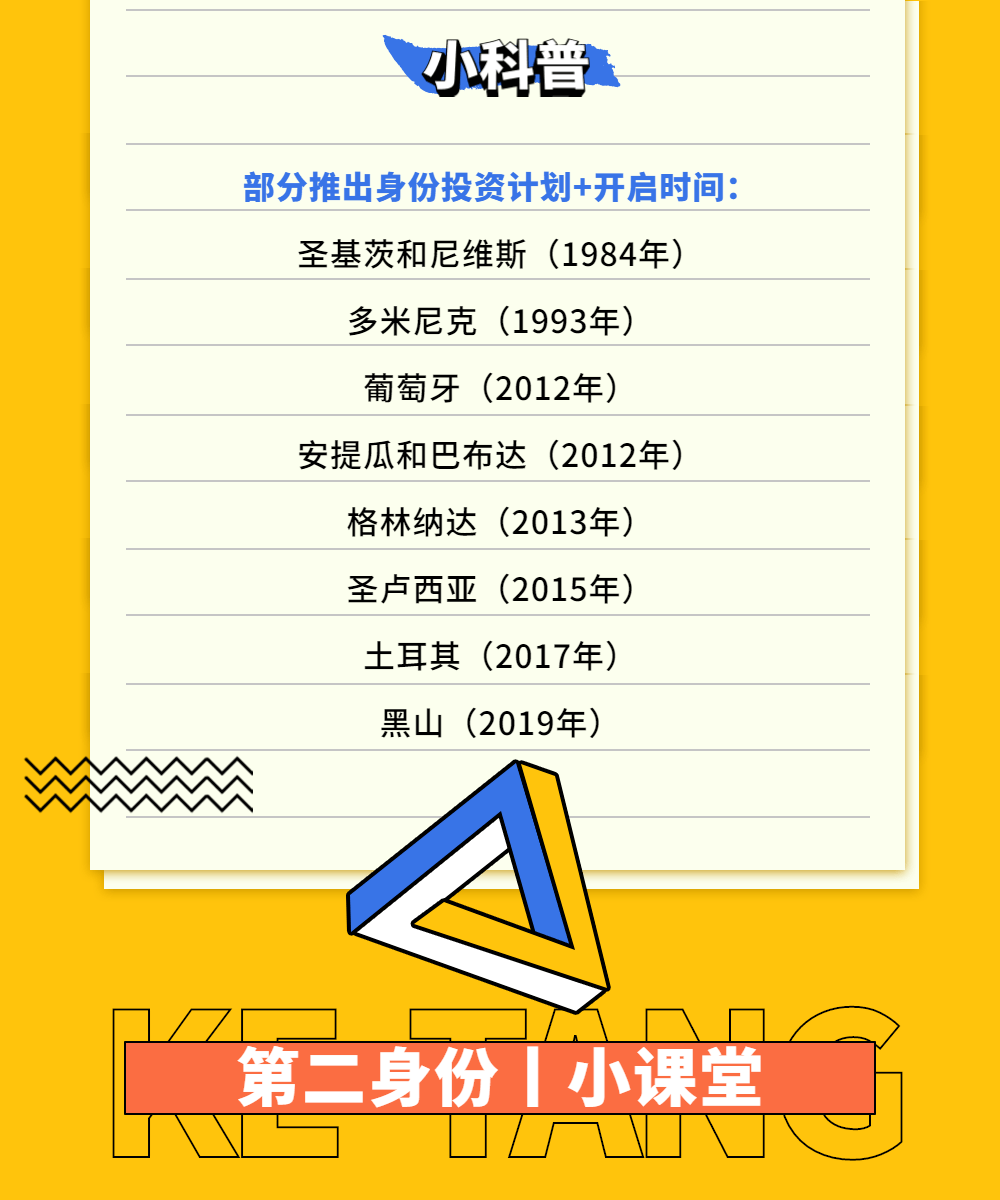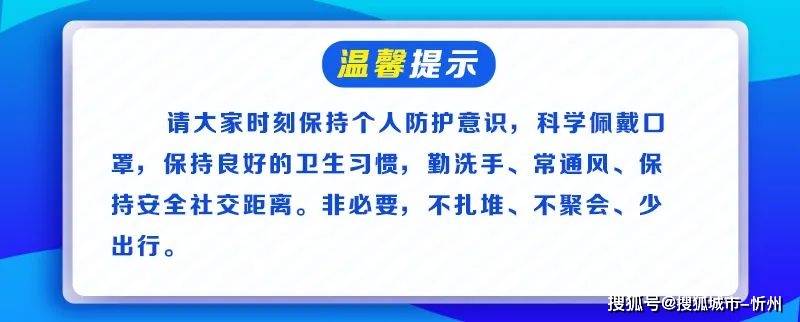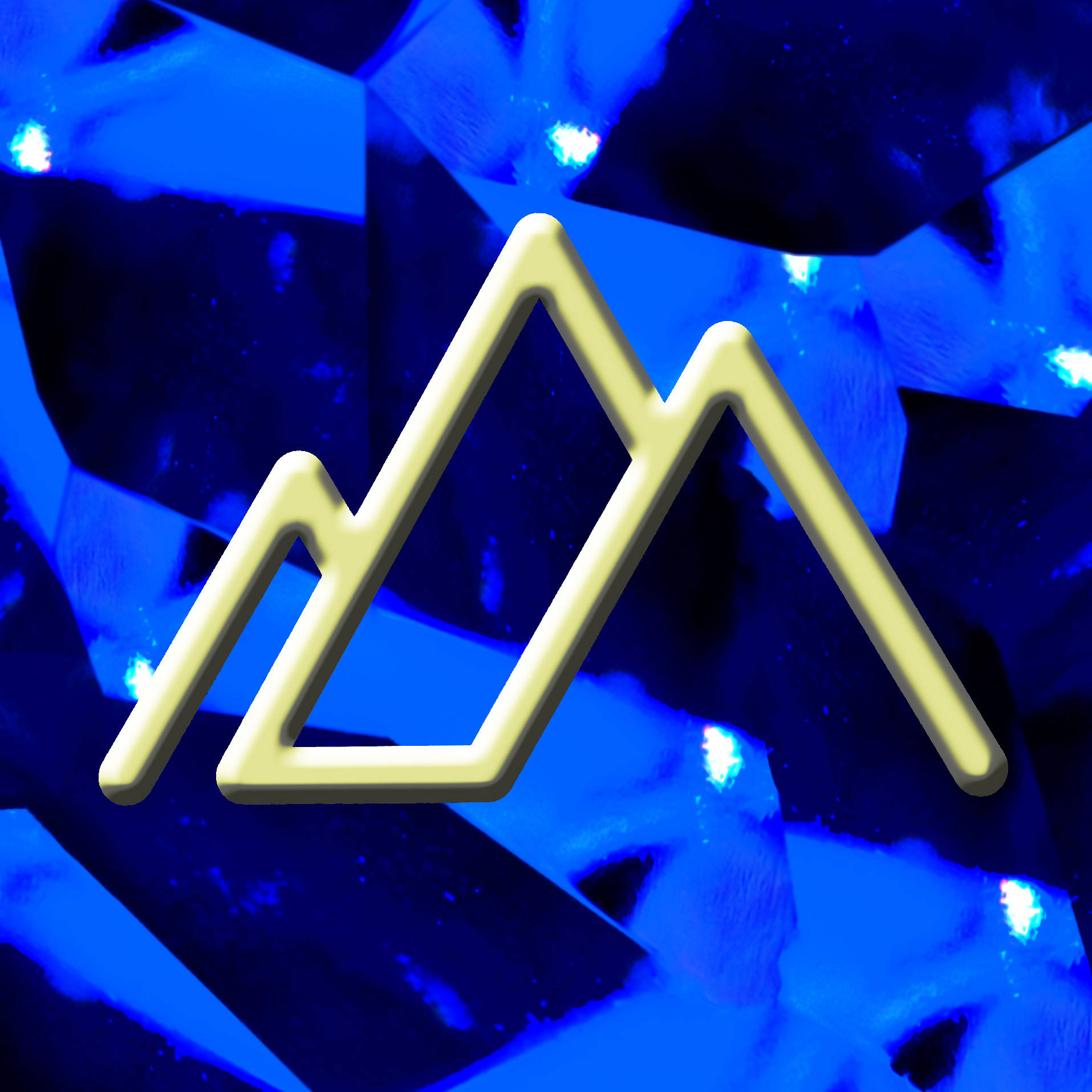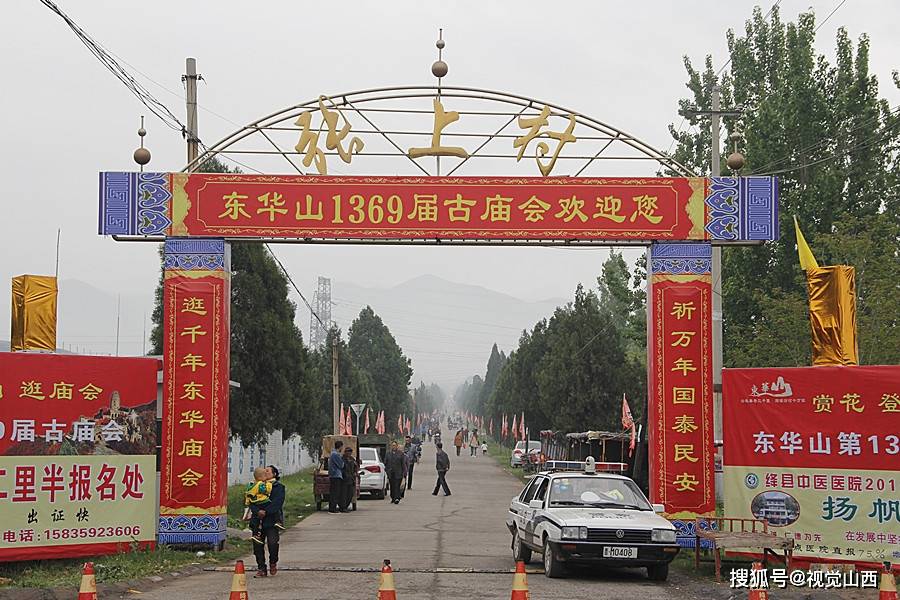■ 谭文德
这是靠近城市的一个河滩,闲暇时喜欢一个人去那里走走看看……
大多时候,河滩空旷、安静,几乎很少见到人影,是一个可以自由安放灵魂的轻松之所。河滩的景致,不同季节之间变换着。春、夏两季休闲的人很多,河滩是城里人走进大自然的好去处。秋、冬季游人少了很多,隐约可见远处有人在耕地,吆喝耕牛的声音,在空旷的河滩上不时顺风传了过来。
河滩修建了青砖铺就的便道,雨后的便道湿漉漉,道旁成片的紫穗槐叶子快落光了。见到那一簇簇匀称而细长的枝干,让我忆起早年用它编筐的情景。教科书上说,紫穗槐是种很好的固土护堤的植物,一般种在河提护坡上。
冬天的河滩里风很大,吹到人脸上愈加冰冷。莲池里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在落日的余晖里,暗黑色的断茎枯叶,把残荷的影子映在冰面上,真乃“浮影残妆,临水斜阳”。远处除了挖莲菜的人,穿着水衣在水池里干活,几乎无人到这里来。
河道淤积到河滩上的那些金色的沙粒,是当地不可缺少的建筑材料,这些年忽然变得更金贵了。过去经常见到,停靠在水边的采沙船。如今环保治理抓得紧,都被拖走了。但是,城市里的楼房依然在建造着,离了那些沙粒怎么能行?金钱的诱惑总是巨大的,所以偷采沙子的营生,禁而不绝就是很自然的了。
河滩靠近水的湿地里,生长着大片的芦苇。信步走在水边上,苇荡在秋风里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这些野生的植物,在河道里顽强地生长着,年复一年,生生不绝。
行走在河滩上,脚踩着被河水冲刷过的河床,绵软的沙土很舒服。夏日里咆哮着的洪水已褪去,但水流过的痕迹,仍提醒着我这里曾有的危险和恐怖。
冬日寂寥的河滩上,总是要热闹一阵子的,成群结队的天鹅来了,很远就能听到鸟儿的鸣叫声。这个时节会吸引好多人,冒着严寒前来观鸟。
到了初春时节,我常去河滩里寻找春天。河提上的柳枝才吐出嫩黄,风干了一个冬天的滩地里,已经长出了稀疏的绿草。河滩上枯萎的草丛里,突然间飞起一只斑鸠,把正在行走的我吓一大跳。原来,那里有鸟儿的巢穴,河滩里藏着它们的爱巢。
这是一个落后的城市,目前还无力一下子消灭原生态的河滩,才使她依然随着四季变化着,也留给我亲近她的机会。自从我来到这个城市,就和这条河结下了不解之缘,无数次徜徉在她的侧旁,无数次目睹过河水涨落。流淌了千万年的这条河,已渐渐注入了我的心田。
河滩的存废,是人力与自然力间一场旷日持久的博弈。千百年来,世代居住在河道岸边的人们,在河水里捉过鱼,在河滩里耕种庄稼,遇上夏季洪水下来,还能打捞些浮财。昔日的庄稼地、莲菜池,变成了今日供人们观赏、栖息的水面,一条条休闲的便道,伸向远方。河滩地变身成了休闲公园,高高的防洪堤,迎水坡修了台阶,人们可以拾阶上下。
快速发展的城市,会不住地侵蚀着大自然的馈赠。在人的欲求和改造自然力面前,河滩必然选择退缩,生长在那里的一切,也会逐渐消失。河流、平川甚或山岭,都会被改变模样。人们喜爱原生态的无奈,其实大多源于自身的莽撞,只是常常不自知而已。
这条河是城市的唯一存在,将来城市一定会朝河对面扩展。那时,这河将成为城中河,河的两岸会被重新整治,河滩也许就彻底消失了,但其更大的价值定会被发掘出来,就像兰州的黄河、上海的黄浦江、伦敦的泰晤士河那样……
眼下的河滩,将成为人人艳羡的黄金水岸。世间的事物,总会这样不停地变化着。